走向现代企业制度
(大型调查报告) 文/吴戈
【编者按】 国有企业向何处去?这已是掌握现代国有企业命运的厂长、经理以及他们的职工们目前十分关切的话题,他们迫切地在寻求一条光明的改革大道。大型调查报告《走向现代企业制度》多层次有条理地介绍了我国国有企业近十余年中改革的探索之路,对当前国有企业的改革确有可借鉴可参考之处,不能不读。参照《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一经典文件的学习,结合本企业的具体情况,以取得相当成绩的兄弟企业为楷模,努力探索前进。那么,不久之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之路,相信可即将接轨运行了。
现代企业制度是企业改革的必由之路
七十年代末,一位前来我国考察的国际著名经济学家曾断言:中国没有企业!此语一出,环座震惊。的确,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是唯一的经济主体。全国尤如一个大企业,各个企业实际上是全国这个大企业的分厂或车间。虽然有国有企业10多万个,其中预算内企业4万多个,大中型企业1.6万多个,特大型企业500多个,但对照国际惯例,中国确实没有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拥有主体地位的真正意义上的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责权不明、活力不足、雄风难振,亏损便十面设伏,鼙鼓动地,弄得“国家队”四面楚歌,不但不能为共和国“输氧造血”,反而要国家投入巨额的资金作为亏损补贴为其“供奶输血”。于是,在亏态毕露、危机四伏中苦苦挣扎的国有企业,不得不寻求一条行之有效的能振兴国有企业的改革之路。
1979年,企业改革在中国刚刚起步时,不少人认为国有企业不活的症结在于缺权少利,来自“婆婆”的“管卡压”过多、过死。因而改革呼声最高的是对企业进行“扩权让利”。但这种在不触动企业财产关系的前提下设法对企业进行行政性分权让利的改革方式,并没有使企业活力明显增强。
针对这种现状,经济界的权威人士们不得不另辟蹊径,从企业利益再分配的角度出发,以充分借鉴农村经营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成功经验为基础,从1987年开始,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进行了第一轮承包试点,这种探索方式,虽然在其试点的初期显示出了其优于“放权让利”的一些特点,但从1991年实施的第二轮承包状况来看,承包制又渐露弊端,尤其是企业行为短期化问题日趋严重。令一些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如果不触动企业产权,承包制所设想的“交够国家的、留足企业的、剩下归自己”的模式又只能是一个美好的充饥画饼。
在这种形势下,有利于企业产权各归其主、明确清晰及可望实现政企分开、使企业真正成为拥有财产支配权的独立法人的股份制改革被推到了企业改革的前台。但不久,人们又从股份制试点工作中发现,企业往往把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股票上市,而忽视了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重组,大大小小的“翻牌公司”应运而生。为此,严厉的经济学家们不得不再一次举起黄牌:如果没有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必然走入歧途。
就在一派“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改革潮中,也有一些精明的企业家们想通过“多枝嫁接”,从与外商合资中拿来一个机制的;想通过“仿洋皮”,从三资企业中仿制一个机制的;想通过“国有民营”,从“老乡”那里换来一个机制的,凡此种种的探索与尝试不胜枚举,但其中传递出的信息却再也明白不过——国有企业活力不足、亏损严重的深层次原因是产权关系不明晰、组织制度不合理、管理制度不科学。
1979年以来的企业改革所有的成败得失都在说明:中国的企业改革要进一步深化,就不能回避产权,就必须完成对企业改革观念的嬗变,由以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政策调整转为企业制度的创新。
一句话,中国企业必须走向现代企业制度,以公司制为其主要组成形式,以公司法人制度为其主要核心,建立具有典型意义的有限责任公司,并逐步完成向股份有限公司的过渡与改造。
沧海横流谁驭舟楫竞千帆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决定》以及继之而来的《公司法》的导航指向下,一大批勇于超越、敢于拓进的企业家们,怀着舍我其谁的神圣使命感,甘作走向现代企业制度的马前卒,在企业改革的前哨阵地上,导演出一幕又一幕探索与实践的活剧:
(沧海拾粟一:深圳风)
远在1980年,共和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行政管理形式——经济特区在深圳似春笋破土时,一种全新的企业制度——公司制、股份制便在这片充满希望与代表希望的土地上得到了最广泛的认同和运用。经过近14年的实践,深圳人已经能够为全国企业界勾勒出一个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的轮廓。其所积极推广的“公司制”、“员工制”、“非官本位制”、“产权流通制”等改革,把企业投入了公司化改造的熔炉。
深圳人认为,国有企业之所以活力不够,其根源就在于企业产权模糊,谁都可以支配企业资产,谁都可以不对企业负责。明晰产权的最佳办法,就是采用公司制,即把非公司类的企业改组成公司。现行企业一律不以所有制形式划分“成份”,只以组成形式和法律责任分为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无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合作公司四类。到目前为止,已有157家企业完成体制改造,其中已获准股票上市的35家。为此,有立法权的深圳市人大常委会还先于国家《公司法》审议并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和《深圳经济特区有限责任公司条例》。
打破企业内部干部与工人的界限,实行“员工制”,把过去企业与员工间的行政依附关系转变为新型的劳动合同关系,彻底改观一次分配定终身的僵化人事格局,赋予劳动者充分的择业自主权,实现员工与企业间的双向选择,活跃了劳动力市场,形成了公平的竞争机制。
取消市属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实行“非官本位制”,按照企业的经营规模和效益水平分类定级,采用国际通用的资产、利税、销售等三项指标体系对企业进行考核。
促成企业兼并、产权转让和依法强制破产,实行“产权流通制”,1993年2月8日,深圳产权交易所正式挂牌,使过去因条块分割而凝固了的产权进入流通领域,让资产转让、兼并、拍卖、破产和重组,按照国际惯例进行市场化、公开化、规模化。至1993年10月,已有45家企业进行产权或股权转让,总额达1点4亿元。
“四制”的改造,尤其是进行公司化的改造,使深圳企业国有资产第一次从“全民”这一含混不清的概念中被科学而具体地界定下来,并有了法律意义上的认证和人格化的代表来维护自身的保值与增值。从这个意义上说,股份制公司这种现代企业制度无疑更符合市场经济所要求的高度灵活性和可操作性。以深圳市通讯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国有股占股本56.16%,法人股占24.9%,员工股占18.92%,1992年公司资产总额2.4亿,1993年升至4.8亿,仅一年时间,国有资产增值一倍,这不能不说是现代企业制度赐予的市场奇迹。
(沧海拾粟二:潍坊潮)
在胶东半岛,素以“忙趁东风放纸鸢”而著称于世的风筝之乡潍坊市,在走向现代企业制度的金光大道上,又率先放飞了一只引人瞩目的成功之筝——以出售国有企业全部资产给企业员工的方式,来从根本上改变国有资产的性质、完成对100户县属以上企业(其中包括一些大型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从而实现生产率提高、效益增长、资产增值三大目标。
1993年岁末,潍坊市百家企业在市政府的统一部署下,进行了资产评估,将企业的资产总额(含固定资产、流动资产、专项资产、无形资产)扣减负债总额后的剩余部分作为一次性出售给职工的净资产,先由企业自清自查,再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文件进行评估确认,然后根据职工的承受能力和入股自愿性,采取配股认购和自愿认购两种方式进行出售。同时健全企业新的领导机制,由全体股东民主选举董事会、监事会,政府不作行政上的干预。
实践证明,这种股份化的方式促成了政府职能和企业经营机制的根本转化,促进了企业内部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它不但使企业求生存求发展的能力、自负盈亏的压力、追求最高利润的动力明显增强,而且使成为资产拥有者的职工内凝力增强、主人翁地位得以真正的体现。如中兴五金股份有限公司改制初期,其董事长按老一套办事,决策不民主,用人不公正。结果股东大会一个提案,便将其罢免。用职工的话来说,这就叫“一砖一瓦有我份,我不管它谁管它。”
职工得到了民主,企业也告别了“婆婆”实现了自主。这些“无主管”企业不但生产什么怎么生产可完全按照市场的需求自行决断,就连抗御“三乱”的能力也得到了明显的增强。据该市10家股份制企业统计,自职工买断企业所有权以来,各种不合理负担比上年同期减少了30多万元。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国有资产在市场流通中实现了循环增值。以前,潍坊市对国有资产实行实物形态的封闭式管理,存量资产尤如死水一潭,兴不起半点波澜。改制后,国有资产以货币形式收回,再以财政贷款形式投放市场,在不断的流通中循环增值。以潍坊电机厂为例,改制后,国家直接收回资产270万元,再投入后,两个月内即获得19万元的财政贷款利息,企业效益亦得到大幅度提高,改制后仅6个月,就完成产值1636万元,实现利税近100万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65.3%和62.7%。
(沧海拾粟三:“八骏图”)
大风起兮云飞扬。当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徐徐撩开它朦胧的面纱时,在中国企业群中举足轻重、闻名遐迩的东风汽车集团、东方电气集团、中国重型汽车集团、第一汽车集团、中国五矿集团、中国纺织机械工业集团、贵州航空工业集团等八家大型企业集团喜获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批准,成为全国首批进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试点企业。在积极推进大型企业集团公司化改革的进程中,勾勒出一幅气势恢弘的“八骏图”。
这八家大型企业集团,过去与其下属工厂及科研机构的联系纽带,主要是行政隶属以及围绕龙头产品形成的生产技术经营关系。而集团内部的产权关系却模糊不清,未能明确建立以资本融合为特征的产权连接纽带。使总公司对成员企业无力驾驭、调控,难以进行统一的规划和经营。
现行的新体制则可望从根本上打破这种格局,并按照市场的要求优化重组,总公司及其子公司将逐步改造为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这样一来,除了总公司对子公司的纵向持股与垂直投资外,成员企业之间亦可交叉持股,从而真正形成资产一体化经营的企业命运共同体。这正如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汤丙午所说的那样:国资部门将企业集团主要成员企业的国有资产统一委托给核心企业(即集团公司)经营和管理,是为了使核心企业成为企业集团的母公司,并通过参股、控股等关系,使成员企业成为子公司,从而增强集团的凝聚力,发挥整体优势。
尤其具有现实意义与改革意义的是,获权经营国有资产的这八家大型集团实际上已成为一种中介性的产权经营机构。它将依法经营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并以资产的保值与最大限度的增值为目标开展经营活动,使资源配置更为合理有效。
此间的一些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这八家试点集团所代表的新体制,必将有助于改变国有企业产权虚化、国有资产在运营过程中无人负责的局面,并催生出一种新的资产经营管理主体。
八骏争途,谁持彩练当空舞?
(沧海拾粟四:牟氏梦)
就在国有企业草拟向产权宣战,向现代企业制度进军的豪迈檄书之际,早把市场经济这个多元魔方玩得生机勃勃的非国有经济成份已经将其机制上的优势向国有企业进行了渗透和互补。一种全新的产权改革方式——“国有民营”,在天津、上海、福建、江苏、黑龙江、吉林、四川等十数个省市区内,已成为国有中小型企业一用就“活”的灵丹妙药。
就在这种引私营“活水”浇国有“旱田”的探索过程中,国有首屈一指的民营企业——南德经济集团总裁牟其中先生又于1993年11月前后构想出一个推动企业快速靠拢现代企业制度的崭新思路:拟以200万美元的雄厚资金,租赁并改造国有重庆479厂、五洲——阿里斯顿制冷设备厂等大中型企业,实行产品结构调整与企业内部各种机制的优化重组。并敢立军令状,保征每年大幅度增加上缴利税、实现资产增值,20年后向国家归还企业资产应缴利税,并按账面价值归还资产。
权威经济人士对此喜上眉梢,评价说:如果牟其中的这一战略想得以实现,那将是国有企业又一条走向现代企业制度的新航线。
……
(画外涛声):
沧海拾粟,仅能挂一而漏万。据传媒报道,自走向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改革目标确立以来,除台港澳地区外的全国各省市已闻风而动,挥鞭催马。成都、重庆、南京、沈阳、齐齐哈尔等市甚至已出台了详细具体的《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方案》,对公司体制的改造、“嫁接”“民营”式的改造、出售产权以进行股份合作制的改造、剥离经营、企业兼并、破产等等问题进行了规范化、程序化、政策化……
极目沧海,正爽风吹拂,舟帆点点,枕戈待旦的中国企业正在海之腹中孕育着一场百舸争流千帆竞的生命律动。
侧耳倾听,正浆歌楫颂,渔舟唱晨,中国企业这条曾风雨飘摇的老船已面向远方的初阳犁开浪花无尽的涛声。
(题图照片:何炳彦 插图照片:缪德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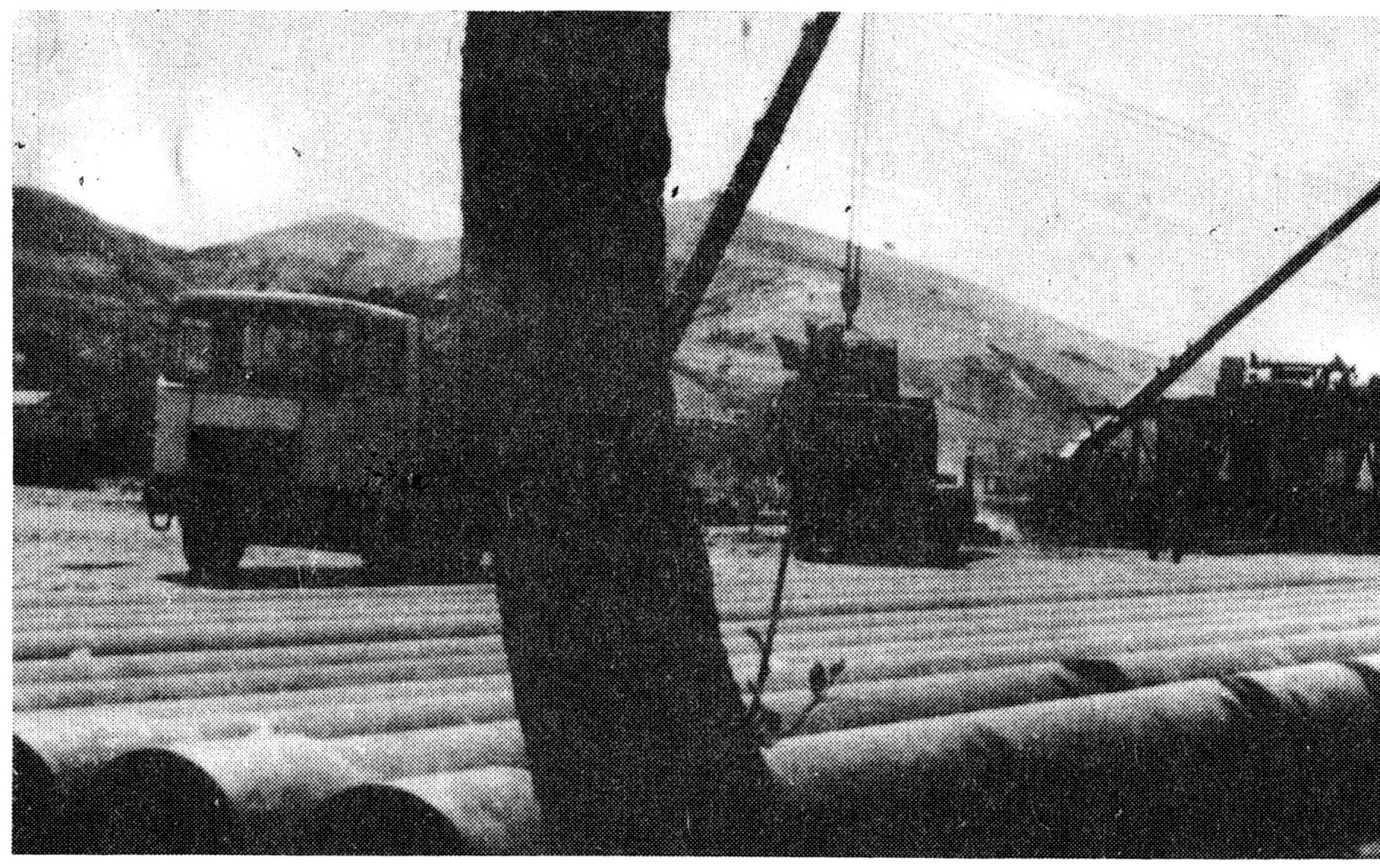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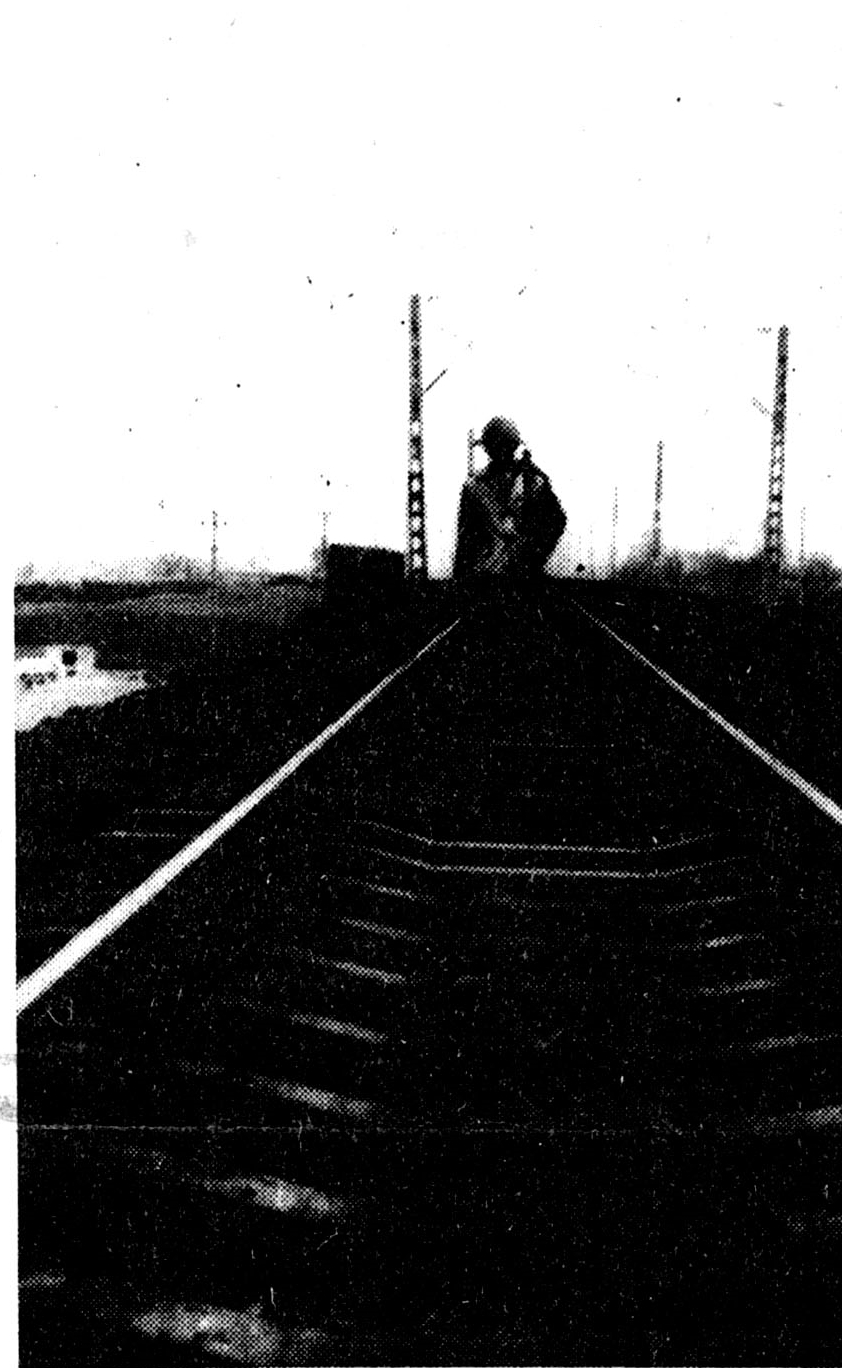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