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丛中最鲜艳
走近丁祖诒和他的西安翻译培训学院
序
人称,他是神州20世纪“民学”的普罗米修斯,他给数以百万计的高考落榜生从天上盗来了“希望之火”!
人称,他是华夏20世纪的新武训,他要无悔地捧出自己后半生的余辉,为数以百万计的高考落榜生描绘一弯通向21世纪的彩虹!
人称,他是“东方哈佛”的构思者,他期待着中国的民办大学在不远的将来能走上世界民学的大舞台!
他有水晶般的心和极富哲理的思维,他掷地有声地说:“高考落榜生犹如烧了七、八十度的水,如果给他们添上一把柴,让他们在民办大学里继续深造,是‘第二个希望工程”’。1997年7月1日,《中国青年报》以通栏大标题“丁祖诒和他的‘第二希望工程’”用一个整版作了鼓呼。
他的故事幻化成“为了中国的‘哈佛’”,立即摘取了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向全国读者特别推荐的优秀作品”的桂冠;
他的故事升华为四集纪实广播剧“希望”和五集电视连续剧“荒原足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的五彩电波为他谱写了飞向大千世界的绚丽乐章;
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先后三次为这位民办教育家打开了金色的大门,“丁氏复合型教育模式值得向全国普通高校推广”成为教育改革的强音和共识。
荣获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的丁祖诒倾诉了对落榜生的“情有独钟”的感念。
日本NHK国家电视台的20分钟专题将他推为继董建华之后的第五位亚洲名人。
中央教育电视台春节晚会,他手捧鲜花向国人大声疾呼:“中国的民学曾有过辉煌于华夏的历史,就一定会有灿烂于世界的明天”。
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他手捧“中华大地之光新闻人物”的金牌光芒四射。
“中华英才”的巨幅封面,将他推上了“英才”的峰巅。
世纪老人冰心久久地拉着他的手,要他将“希望”一代代播种,一代代延伸。
28位驻华使节专程参观了他的“东方哈佛”,题为“世界在这里睁大了眼睛”的整版报道,被全国十多家大报转载,将他和他的“西译”推向了大洋彼岸。
98年慕名蜂涌而至的6800名学子,光荣地成为西译98级新生,创造了全国招生之最。
人称,百花丛中他最鲜艳!最夺目!
他说,最鲜艳的是13000名西译学子!最鲜艳的是中国民学的春天!
一
命运有时总是喜欢捉弄那些热爱生活的人。
1957年,当踌躇满志的丁祖诒,怀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以每门功课90分的成绩,受到清华大学青睐时,生活突然向他泼来了一瓢冷水。因为出身问题及几句关于“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出格的话,他最终被拒之于大学门外。青春年少的金色梦想彻底破灭了。
“这是我人生中受到的第一次伤害,当时这种刻骨铭心的伤害,深深扎进心底的自卑,乃至恐惧,至今还不时地从积淀的岁月里浮上来。”
许多年后,当他的西安翻译培训学院迎来一批批高考落榜生时,他总是这么说。
丁祖诒是那种在命运面前永不服输的人,他总是说,命运就像画家手中的笔,只要你握住了他,总会在自己的人生中描绘出多彩的图画。
那时的他,又开始以惊人的豁达与乐观的态度开始面对生活。他立下誓言:“今天上不了大学,总有一天,我要登上大学讲台”,从那一刻起,他凭着这种坚定的信念,凭着少年的壮志豪情,开始向不公平的命运挑战。在以后短短的两年时间里,他终于以惊人的速度攻下了英、日、德、俄四门外语,并且刊发了近百万字的译著,加上在高中阶段就超前自学了多门大学理工课程,到1964年,竟然用三年时间在一所业余大学里获得了六年制本科学士学位,将生命的时钟拨快了三年。丁祖诒以自己的努力,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二
也许是历经了坎坷艰辛的生活,成功后的丁祖诒,总是把目光关注到那些同样在生活中遭受嘲弄的人们。
1985年仲夏的一天,上完课坐在家里休息的丁祖诒,在翻看当天的报纸时,他突然被报上的一条消息震惊了,一个高考落榜生,由于受到社会、家庭等各方面的压力,最后被逼上了黄泉路。这是何等怵目惊心的消息呀!当时,丁祖诒的心就像被人狠狠捅了一刀似的。二十多年前,当他被命运所抛弃的那一幕一下子又浮上了心头。如果当时自己不是理智一点的话,自己也许会走上这条路的。这之前,丁祖诒曾看到过一份资料:全国每年有200多万考生,而高校仅能录取27%,剩下的73%的落榜生,将不得不被推向社会。同样,这些青年,都处在对生活充满着幻想的年龄,他们对生活的承受能力又是那样脆弱,当他们从理想王国突然跃进现实生活,不知有多少人会承受不住这种打击。
“高考落榜生就像烧了七、八十度的水,如果再给他们添上一把柴,该多好呀!”也就是从这一刻起,丁祖诒突然萌生出了一个念头,自己办一所大学,让更多的落榜生有一个深造的机会。他要想办法重新唤起这些落榜生心中的希望,让他们的青春迸发出五彩的光芒。
这时,丁祖诒因工作出色,已担任了某国办大学外语教研室的主任。同时,他又受西安市科协的重托,开始筹备西安翻译工作者协会,并当选为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这无疑对他实现这个夙愿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
丁祖诒是那种说干就干的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策划和筹备,这年秋天,他终于将一块起名为“西安外国语联合培训部”的招牌,挂在了一间租来的教室的门外。
新生事物,总是会给人们带来一种疑虑和惊讶。当那些抱着试探的心理报了名,坐进这简陋的与高等院校有着天壤之别的“培训部”开始上课时,他们的心里仍然不怎么踏实。
一年以后,第一期兼职导游班的50名学生学完了课程,其中有43人顺利地通过了省旅游局的导游证统考,走上令许多人羡慕不已的导游行业。
就这样,丁祖诒用自己的一腔爱心,一片热诚,一片对社会的责任感及对高考落榜生的关注,写下了他迈步“中国哈佛”故事的开头。
生活总是让懦弱者无路可走;让平庸者有一条路无需选择;让勇敢者时时面对着十字路口。就在丁祖诒为他的“中国哈佛”的梦想写下一个美好开头时,已被借调到西安市译协,年近五十的他,不得不面对现实,对眼前的生活之路做出选择;他所任职的大学不再同意将他长期借调“人在曹营心在汉”。两条路由他选,一条路是,用培训部收入的学费支付自己高额借调费,占住高校的位置,循规蹈矩地按既定的模式去教书。这种选择,意味着他将有可能得到三室一厅的住房,将评上高级职称,还有终身享用的劳保福利以及安逸、舒适的工作环境也对得起自己四十年的工龄,另一条路则是摔掉这半生梦寐以求才拼来的铁饭碗,用今天时髦的词来说“下岗”。
这天晚上,丁祖诒第一次失眠了,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像一只迷了路的羔羊,真不知该何去何从。
一个将近50的男人,上有年迈的双亲,下有三个女儿,再这样折腾下去,他觉得太对不起他们了。然而,当他一想到自己的事业刚起步,一想到还有那么多渴望跨进大学门槛的年轻人时,他心里的天平失衡了。
丁祖诒毅然地作出选择——摔掉这个“铁饭碗”!决心一下,丁祖诒便义无返顾地带着一家三代七口人,搬回到当中学教师时住的那间仅有15个平方米的简陋的小屋。
搬家的那天,许多同事和朋友都来劝他:“祖诒,只要你想通了,好赖留下来,别等将来后悔都来不及了。”
对于朋友和同事的好言相劝,丁祖诒只是感激地笑了笑,他说,我对自己的选择,绝不后悔!
听了这话,他的大女儿再也忍不住了,平生第一次冲着他说:“爸,你这样做,到底图个啥呀?你怎么这样傻呀?”他的父亲老泪终于夺眶而出,在那苍老的脸上纵横着……
“是的,我到底图个啥呀?”
后来,当他那与他患难与共多年的妻子,因他一意孤行,因他太不管不顾这个家而挥泪与他分手时;当他拿着创办民办大学的方案四处奔波,求爷爷告奶奶地寻人说情而屡屡受挫;当他独自一人前往汉中市一个重点中学去游说为他的民办学校招生,而被“请进”当地公安局时,他常常这样扪心自问:“对此选择,你是否后悔?”
当丁祖诒创办的学校终于走出艰难,走向人生的辉煌,一位深知内情的记者这样问他时,他竟毫不犹豫地说:“对此选择,我生不后悔,死而无怨!”
三
套用一句话说,民办教育是一件摸着石头过河的事。它不像名牌大学那样,学生只要一挤进这座中世纪的城堡式的象牙塔,便可一劳永逸坐享其成地等待着生活为他们铺就一条锦绣般的路。
丁祖诒在创办西安翻译培训学院之前,虽然也从事过几十年的教育工作,但那种传统的教学方式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地去攀爬教育这把梯子——考试,考试。从而为社会造就出一批批高文凭、低能力的人。
而作为一个民办学校,从它一诞生的那天起,命运就决定了它必须走向市场,与社会经济相适应。
在学校创办之初,丁祖诒为了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便抱着尝试的态度,在教学过程中对课程的设置做了大胆的改革,他让学生在学习外语专业全部课程的同时,又加开了其它的涉外专业,如国际贸易、国际旅游、国际会计、公关文秘、市场营销、计算机应用等,再加上多项现代化技能。这样,这些学生毕业后就会在社会立于不败之地。
而真正启发丁祖诒,使他坚定不移地实行教育改革(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的是后面发生的两件事。
第一件是这一年新一届毕业生面临择业的关键时刻,新加坡一家银行来西安选录职员,或许是处于一种习惯,也或许是他们对民办学校的不信任,一开始,他们便把选用人才的目光死死盯住那些“皇家”学校的外语、财经类的学生。但是,几经周折,最终却因为那些院校的学生或缺乏专业知识或外语口语能力差均未能如愿。随后,他们不得不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来到了西安翻译学院这所民办高校。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他们根本无法想象,一个民办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竟一专多能,既精通外语,又深知专业,还懂得电脑,还会开小汽车。
仅这一次,他们就以每月高达7000元人民币的薪水,录用了30名。
第二件是,西译院的多名大专毕业生在和国办大学本科生的较量中,竟跨越本科段,一举考上了国办院校的研究生。
就在99年招聘中,西安著名的金花集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批驻外办事机构高级文员。几经考核,剩下30多名“选手”最终录用的九名文员有八名是西译学生,只有一名是国办大学本科生。
这一切皆源于西译的复合实用型教育模式。
事实证明,丁祖诒的这种尝试没错,也更坚定了沿着这种教育模式走下去的信心。
这之后,丁祖诒又经过多方调研,根据市场的需求,制订出了一个“外语十专业十现代化技能”的复合实用型外语教学体系(即把高等自学考试与大学后继续教育融为一体,把专业深造与现代化技能培训合二为一),开始向“皇家”学校那种传统的教学方式挑战。毕业生怀揣两张文凭(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或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西译院颁发的专业证书),既会外语,又懂专业,还掌握有多种现代化技能,自然而然地也就拥有竞争理想职业和早出成就的真正“本钱”。
据1996年“内参”透露,国家权威部门曾在南方“三资”企业对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工作能力作了专项抽样调查,排名第一的竟是民办的西安翻译培训学院。
西安翻译培训学院也因此吸引了大批素质较高的生源。1998年招录的6800名新生中,竟有1200名高考500分以上的四年制本科生。在1999年春季自学考试中,西译参加外语类考试的各门通过率均超出全省平均通过率30个百分点,位居全省之冠。
除此以外,西译毕业的万名学子中,历经几年的拼搏,担任三资企业经理,工资达三、四千元者已比比皆是。出国深造者近两千人。
四
机遇总是垂青那些生活的有心人。1993年下半年的一天,正当丁祖诒为校舍的事急得坐立不安时,担任学院名誉院长的西安市政协主席孙殿奇,给他带来了一个消息,位于西安南郊的国营西安第一钟表机械厂,迁入市内电子城工业园区,老厂的200多亩厂址,6万平方米建筑,以630万人民币标价转让。
这消息,如同久旱的一滴甘露,令丁祖诒激动万分。这块留下唐代诗人王维诗句“太乙近天都”的风水宝地,正是开展封闭式外语教学,加速学生成才的理想之地。“吃”下它,学院便可以从此摆脱靠租赁校舍“寄人篱下”的初级生存格局。其今后的发展更是不可估量。
当时,国家有关政策明确规定,民办院校的一切资产归国家所有。办学者白手起家把学校办起来,租赁校舍没有风险不说,奋斗几年还可心安理得地“赚上一把”。如果置房子买地,这样一大笔资金不但要勒紧自己的裤带,最终产权归属国家。走好了,将一马平川,若失败,后果将不堪设想。
虽然说,这是一步险棋,但丁祖诒吃了秤砣,铁了心,决定走下去。
那一天,他将决定买地建校舍的这个消息向全院职工通报时,他没想到,他短短的几分钟的讲话,竟然几次被那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打断,当会议结束时,全院师生自发起立,齐声高唱:“院长您大胆地往前走哇,往前走,莫回呀头,通天的大道,九千九百九十九呀。”
丁祖诒在人生最最艰难的时候,都未流过泪,但这一次他竟热泪盈眶,激动得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来,他深深地被学生们的热情感动了。
决心已定,筹措资金便成了当务之急。为了组织集资,丁祖诒率先停发了自己的工资,又把学院的全部家当押上。想向银行申请贷款。许多家长知道这件事后,也纷纷赶来将家里的积蓄全数拿来,借给学院。
那些个日日夜夜,丁祖诒几乎使出了浑身解数。他像只陀螺一样总是不停地转着,一旦自己稍有松懈,他便会狠狠抽上自己一鞭。
1993年10月7日,在各级领导和社会贤达的大力支持下,丁祖诒终于如愿以偿,与工厂签订了“国有资产转让合同书。”
事实又一次证明,丁祖诒这一步险棋完全走对了。如今,丁祖诒的西安翻译培训学院,已成为一个拥有占地六百亩,自有校舍13万平方米,全日制学生13000名,两亿元校产的民办学校。他现在又将在西安经济开发区花巨资购买68亩土地和两万平米的豪华校舍,不久,一幢现代化西译大厦将拨地而起。
五
有人说,大学生是用心灵生活的,他们更注重灵魂的充实和自由。
十七八岁,正是花季般的年龄,他们风华正茂,他们青春年少,他们的心底充满着浪漫、幻想、纯真。
丁祖诒却在他的学校里订了许多清规戒律,对他的学生们实行全住校全封闭准军事化严格管理。
每年新生入校,先进行军训,还得严格遵守他的三重封闭式管理制度。即一周五天内禁止出校门,男女生不得互串宿舍,教学区与宿舍区隔离,男生不准抽烟、喝酒,女生不得化妆、戴顶链首饰、染黄头发。男女生不得勾肩搭背,一经发现谈恋爱立即劝退……
可是,学生们对这种“苦行僧”式的管理方式不领情。1995年,在执行上课时间封闭宿舍区的管理制度时,一些学生不理解,半夜里一边高唱国际歌,一边呼喊着“还我一片空间”。“要人权,要自由”的口号。丁祖诒知道孩子们是可爱的。但太幼稚,他也能理解孩子们的心理。但同时,他更深知“教不严,师之过”,对这种取闹,他没有理睬,也不去调查谁在“捣乱”,只是坚持执行管理制度。三天后,学生们不再唱了。这时,丁祖诒召开师生大会,专门为学生做了个报告,讲“学生的人权是什么?”在学校里,丰富知识,提高素质,就是最大的人权,如果学校安排课时不足,教师不负责任,教学设施不完备,对学生管理不力,这才是不尊重或者说侵犯了“学生的人权”。
“如果没有那时‘炼狱’中刻苦修炼,哪有我今天展示才华的‘天堂’呀!丁院长虽然在学校管理上像一位严厉的父亲,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却更像一位慈母。”一位曾经在那个夜晚振臂高呼“要人权,要自由”如今有了令人羡慕的工作的学生这样说,“记得1994年11月份时,我们学校的一位同学,因父亲去世,母亲没有工作,而失去了经济来源。她便去找丁祖诒院长说想退学找份工作养家糊口”。
丁院长听后,便深情地对那个女学生说,你现在退学太可惜了,这样吧,我明天就想办法安排你在学院里打份工,这样既不误学习,又有收入,下学期再减免你的学费,你看行不行?
丁院长又听同学们说,那个学生现在连吃饭的钱都没了,当即拿出200元钱送给她,并说:“这点钱虽然不多,你先用着,希望你能学下去,如果还有什么困难,你就随时找我。只要我有一口饭吃,就不会让你挨饿!”
就这样,这个同学终于挺过了难关,完成了学业,最后还找到了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
这多年来,丁祖诒始终是以亲情为基点来对待学生。几年来,在学校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十多年中还先后为千余名学生减免了数百万元的学费,而他自己掏出的工资就更无从计算了。
六
著名作家琼瑶为“西译”题写道:“生命中永远有数不清的挑战,面对挑战,不论是败是胜,总是在人生的旅途上迈出了一大步”。
丁祖诒在向命运挑战的同时,更敢于向正统、向权威挑战。从而创出了一条非常适合我国国情的民间办学的路子。他的“丁氏复合实用型”教育模式,更是为我国素质教学带来了曙光。
丁祖诒成功了,有人把创立的“西安翻译培训学院”称为中国的“哈佛”;把他称为中国“哈佛”创始人。
“哈佛”为什么有名?就是因为培养出六位总统和十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丁祖诒的“西安翻译培训学院”虽然尚不能和“哈佛”真正相提并论,但他毕竟在中国的教育史上创下奇迹。
1996年11月19日《香港文汇报》上曾刊登过一篇题为《教育改革出成果,民办高校结奇葩》的报道:98%毕业生工作称心,20%大学生出国深造。西安翻译培训学院复合实用型人才成效显著。10月22日,该院又有100名学生陆续启程赴吉尔吉斯国立师范大学留学。开创了西北五省区民办学校大规模出国深造先例。
特别是近年来,当许多国家正牌学校的毕业生都为找不到工作而大发其愁的时候,西安翻译培训学院的毕生却越来越红火,越来越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
1997年,该校千名毕业生,被100多家三资企业全数聘走。
1998年,离毕业还有两个多月,60%的毕业生已被上门索聘的单位领走。
1999年6月近2000名毕业生又被全国三资企业抢聘一空。
丁祖诒“西安翻译培训学院”的现象,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为此,国家人事部人事与人才科学研究所、人民日报社和中国国情调查研究中心,分别于1996年、1998年、1999年先后三次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举行了“西安翻译学院丁祖诒教育模式高层研讨会”、“西译现象高层研讨预备会”和“全国民办高教研讨会”。会上,他受到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家璐、雷洁琼、吴阶平、程思远、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马文瑞和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等有关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扬。这位驰名神洲大地的“98中华新闻人物”,这位涉足政坛的陕西省政协常委。这位被中央电视台和日本NHK国家电视台推为“东方之子”和“亚洲名人”的民办教育家,用他十余年的心血为国家积累了两亿元的固定资产,而他自己依然两袖清风,但他却仍然在奋斗着。
我常想:丁祖诒在民办高等教育这个百花园中已构成了一隅风景,他在构筑“西译”这块风景的时候,自己又成了一个教育景观,在民办高等教育这个大观园中“西译”在百花丛中会更耀眼更鲜艳,千万朵花儿会更红更香,香飘四方…… (大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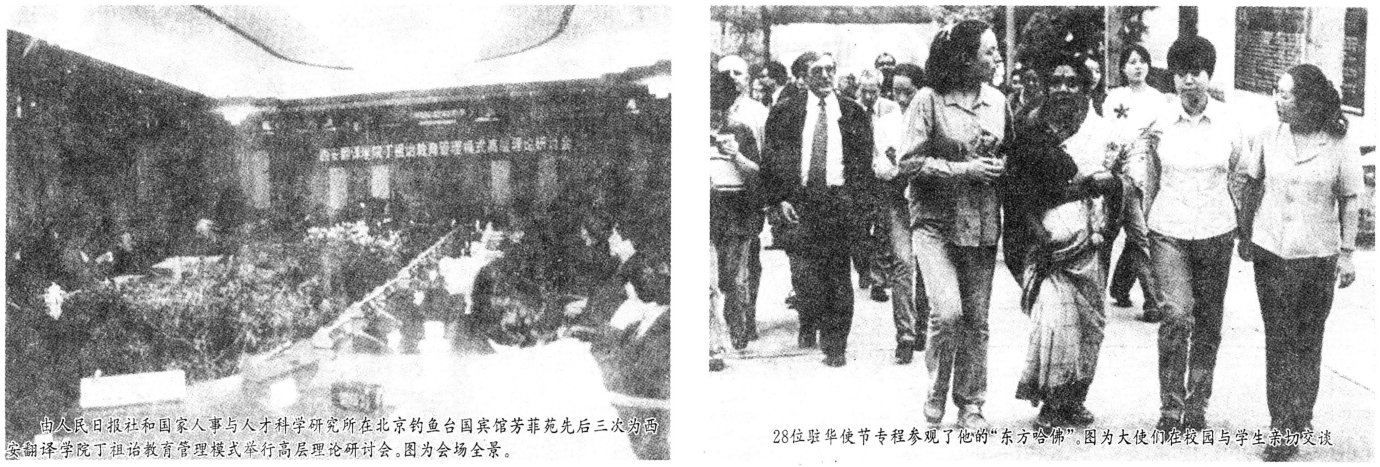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