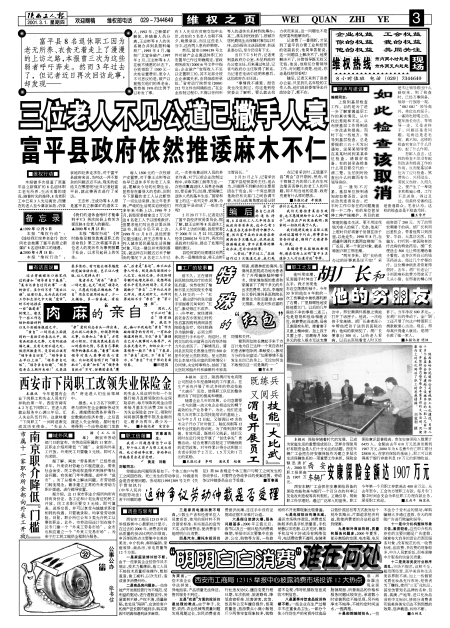
本版导读
富平县8名退休职工因为老无所养、衣食无着走上了漫漫的上访之路,本报曾三次为这些弱者呼吁奔走。然而3年过去了,但记者近日再次回访此事,却发现——
三位老人不见公道已撒手人寰富平县政府依然推诿麻木不仁
本报曾多次报道了原富平县立新煤矿的8名退休职工老无所养、生活无着的境况。随着时光的推移,8名老职工中已有3人先后离世,而健在的老人至今凄凉如故,仍哀哀地四处奔走求告。对于富平县政府来说,为何这一并不复杂的问题迟迟不决,现实的症结又在哪里呢?近日记者赴富平县,就此事再次进行了采访。
王志彬、王成功等8人原是富平县立新煤矿的退休工人。1992年,立新煤矿解体,伴随着人员分离,王志彬等8人的关系被合并到县塑料编织厂。1995年4月,编织厂又宣告破产。1997年2月,王志彬等8人在极不情愿的状态下,分别领取了1500元一次性安置费用。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破产以前拖欠他们的养老金,竟然按19%的比例予以补发了事。
每人1500元的一次性破产安置费,对于像王志彬等这些早已退休多年的老工人来说,要解决今后的长期生活,显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回到乡下原籍的老工人从此断绝了一切生活来源,加之年老多病,严峻的生活现实迫使他们多年来不断上访。1998年5月,县经贸委曾拿出2万元对这8名老工人予以困难救济,但要求他们写出息访罢诉保证书,保证今后不再上访。1999年11月8日,县经贸委又提出建议,将王志彬等8人列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可这一建议并未得到落实。就这样在问题迟迟未予解决的情况下,8名老工人中已有3人先后在贫病交加中去世,尚在的5名老人也朝不保夕,晚景凄凉。而且这些老人当中,还有两人患有矽肺病。
然而,国发(1994)59号文件对破产企业离退休职工的安置早已作过明确规定。省政府陕政发(2000)6号文件中指出:企业破产“变现收入不足以安置职工的,其不足部分按企业隶属关系,由同级政府承担。”省劳动厅陕劳发(2000)212号文件也明确指出:“在企业改制过程中,不得以任何形式,一次性结算退休人员的养老待遇。对于以前企业改制过程中,采取买断工龄等方法,一次性结算离退休人员养老待遇的,要妥善予以处理,要保障已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国家和省上的这一系列文件、政策,为何在富平县却成了一纸空文呢?
2月20日下午,记者走访了富平县经济贸易委员会。据了解,就王志彬等8名退休工人多年上访的问题,县经贸委于2000年11月22日以富政经发[2000]34号文件,再次向县政府打报告,提出了处理问题的建议。
县经贸委的处理建议有两条,其一是筹措资金,将王志彬等人的退休关系转到统筹办;其二,落实到民政部门,按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加以对待。这份报告主送县政府、抄送县委办后,至今仍没有下文。
当日下午5时许,记者来到县政府办公室,未见到政府办公室主任。后来通过电话,记者与政府办主任取得了联系。当记者在电话中说明来意后,这位政府办主任说:
“事情我不清楚,报告我也没见到过,你还是到经贸委去了解吧,要么就去找主管县长。”
2月21日上午,记者采访了富平县经贸委孙主任。他认为,问题得不到解决的主要原因在于资金,另一个突出原因是政府有关部门之间协调不够。无论从政策角度还是从财力状况来说,这一问题也不是经贸委所能解决的。
记者费了一番周折,才见到了富平县分管工业和经贸的张副县长。他简单答复说,这一问题县上解决不了,他更解决不了,分管领导既无权又无钱。他说,他刚任分管领导工作,对问题不清楚,他说,你还是找经贸委吧!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县委办公室,只见到几名年轻的工作人员。他们说县委领导去开政协会了,都不在。
在记者采访时,正值富平县“两会”召开期间。然而,对于管辖之内的那几名在生死边缘苦苦挣扎的老工人的问题,却不知当地的党委、政府究竟有什么样的想法。
■本报记者 辛国强备忘录
1999年12月9日
本报“维权行动”:《谁给我们发养老金?》首次向社会披露了富平县原立新煤矿8名退休职工的境遇。
2000年4月18日:
本报“维权行动”:《我们的退休金啥时才能拿到手?!》再次向县上有关方面反映8位老人的窘况。
2000年6月23日:
本报“维权行动”《何时能按足额发放离退职工的活命钱》第三次将富平县8位老人的现状作为事例披露于社会,以求引起县上的关注。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