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正道是沧桑
——走近缔造西安翻译学院的“东方之子”丁祖诒
不经风暴不足以言雷霆
不历坎坷不足以语人生
——题记
引子 猎猎的原上风鸣咽着,滚滚的黄尘漫着。这个曾裹护过华夏始祖黄帝英灵埋藏过历代王者之骨,洒满无数折腰英雄鲜血和寻常百姓汗水的土地在深沉地熟睡着。嵯峨起伏的沟壑山峦,那奔腾跳跃的河水溪流,还有那一望无际的旷野田地,这一切都似乎在昭示着一个又一个伟大灵魂的诞生,预示着一场又一场自古未有的奇迹问世。然而,传说和寓言堆积如山,却没有人推算太阳的周期。
盗火圣徒的沉重抉择
1987年仲夏一个漆黑的夜晚,古城西安一所国办大学校园的寻常斗室里亮着一粒微光。这粒微光忽明忽暗,不久,随着一声发自肺腑的深沉叹息,那粒微光消逝了。接着,一扇半掩的窗被打开,就在这时,一道无声的闪电划破夜空,照出一张男人的脸。这张脸苍白、疲惫,但那双因严重失眠而布满血丝的眼睛,却燃烧出亢奋的火焰。
丁祖诒已经是第二次经历这种灵魂煎熬的夜晚了。
第一次是在30年前1957年的一个夏夜,年方18岁的丁祖诒,南京久负盛名的南大附中(原第十一中学)高才生,南京市中学生数学竞赛优胜者,以高考门门90分的优异成绩被名牌大学所青睐,却因“政审不合格”而落榜。
也是一个漆黑的夜晚,他徘徊在秦淮河的生死边缘线上,两种声音同时在他耳畔响起,“下来吧,孩子,到遥远的极乐世界,那里没有悲愤和烦恼”,“走开,挺起胸脯,去迎接人生的挑战!为自己的价值活着,更要为别人的幸福活着!”终于,他从黑色的七月中走出,终于,他道出一句话:“今天我没能跨进大学门槛,总有一天,我要登上大学的讲台。”
就从那个夜晚,丁祖诒对一位钟情于他的姑娘说:“原谅我,功未成,业未就,我无权栖息在你的港湾”,遂作别江南佳丽地的金陵,来到千里之遥的古城西安,将自己置身于支援三线建设的滚滚洪流中。
就从那个夜晚,他依托在研究所工作得天独厚的氛围,用第一个3年自学了4门外语,翻译了数十万字的译著,并凭借高中时已自学完大学基础课程的深厚功底,在一所业余大学用3年读完了6年制本科,取得了国家承认的本科学历,将生命的时钟整整拨快了3年。他用第二个3年,一头扎进他高中时热衷的被称为数论王冠的费尔马大定理,他的初步成果受到了华罗庚的勉励。他实现着人生旅途上第一次艰难而又神圣的飞跃。
然而,无情的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他的梦想。接踵而来,他被光荣地下放当了8年工人,他被理所当然地扣了一顶白专道路的“桂冠”遭到轮番批斗,他因16首打油诗揭露研究所领导贪污盗窃而被开除了团籍(20年后又得以恢复),他荣幸地以黑五类老“运动员”的身份和红五类的“走资派”关在同一个牛棚。幸运的是,他乘牛棚懈怠之际,携患难与共的未婚妻作了一次胜利大逃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旅行婚礼。幸运的是,得益于一位当年主宰全市领导命运的领导兼舅舅的过问,他被破格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担任一所高中的外语教师。从此,他人生的航程由狂热的爱因斯坦崇拜者转向了神圣的教育殿堂。
面对着酷似他当年冲刺高考的一群孩子,他不顾淋巴结核病魔缠身,硬是利用3个月住院期为高考生编写了一部30万字的“英语常用词用法手册”,冒着倾家荡产的危险借钱自费出版发行了5万册。
然而,就是用这本书,一张并不起眼的本科毕业证和并不显赫的中学教师头衔,丁祖诒凭借着他的执著、他的果敢、他的才华敲开了一所国办大学的大门,不久又担任了外语教研室主任。一个从未进过正规大学校门的人,30年后就这样登上了大学讲台,实现了他18岁时的梦想和誓言。
30年后的今天,他又不得不面对他所创办的西安翻译协会招录的几百名高考落榜生作出人生的第二次抉择。他无法兼顾他的大学本职工作和为落榜生深造的分外义务。要么委曲求全维持半生拼搏、半生梦寐以求的高校公职,保住终将到手的高级职称和三室一厅,占领30年工龄的劳保胜利果实,要么为魂牵梦绕的落榜生做一次光荣的殉道者,为曾与他同命运的落榜生踏上民办高教的荒凉处女地。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这一夜,在情与理、公与私、成与败、荣与辱的裂变中,丁祖诒接受了生平最严峻的自我拷问。最后,噩梦醒来般地他最终选择了“与落榜生同行”。顶着人们的嘲笑,攥住亲人的不满毅然踏上了神圣而光荣、艰苦而清贫的人间正道。
就像当年鲁迅先生向全社会大声疾呼“救救孩子”的呐喊一样,丁祖诒深深地体验着教育对于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巨大分量。且听丁祖诒如是说:
“高考落榜生就像烧了七八十度的水,如果给他们添上一把柴,让他们在民办大学里继续深造,他们就完全可能成为我国的高等职业技术人才,这应该是第二个‘希望工程’。因为他们同样是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
这种超越普通意义上的深层理念使得丁祖诒必须以非常的行为来实施决断,甚或以离经叛道的方式来点燃心中的那把圣火,他愿为人间的落榜生盗来天上的希望之火。
攀登陡峭的天梯
1987年7月,丁祖诒忍受着心灵的剧烈伤痛,孑然一身地从他所挚爱的国办大学中“下海”分离出来,擎起了“社会办学”的大旗,掮起了为“落榜生”远航的巨轭。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以求索”。那段时日聊以自慰的只有这句话了。
万事开头难,白手起家的丁祖诒当时手里只有一张西安外国联合培训部的民办招牌。在一无经费、二无后盾的情况下,丁祖诒租了一间教室,一间办公室。从这里起步,丁祖诒踏上了他社会办学新征程的“零公里”。
“办一所全日制民办大学”的构想刚刚成熟,得到的答复却是:无此先例。不同意。
丁祖诒的执著、信念意外地得到省高教局成教处的青睐。终于,1987年9月,西安翻译培训学院成立了。时年丁祖诒已48岁。他成了陕西省全日制民办高校的先驱。
创业之初,正是盛暑未褪的初秋季节。街头巷尾,路牌灯下,文化宫、体育场、校园操场上,人们常常看到一个面庞白皙风度儒雅的人,推着一辆与自己伟岸身躯极不协调的破自行车在张贴招生广告。他这身行头和打扮,成了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骑着瘦马的形象在中国的最佳注脚。
赤日炎炎或是大雨滂沱,丁祖诒和他的同伴们渴了没有“红牛”,饿了,只是方便面;热了,没有空调,累了,自有台阶和栏杆相伴。他没有固定工资,他需要计划每一枚硬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硬是靠着这股子拼命三郎精神,丁祖诒打胜了创业之初的第一战役。1988年春季,第一次招录了300名学生。
自古雄才多磨难。1988年秋季,为了扩大规模,丁祖诒决定派人到全省各地去招生。身先士卒的丁祖诒给自己确定的地点是远在秦岭南麓的汉中地区。越过巴山蜀水,千里迢迢来到素有“小江南”之称的汉中市,没想到等待他到来的不是鱼米之乡的淳厚热情,而是命运之神给他玩的一场令人哭笑不得的黑色幽默。
在汉中的一个重点中学,怀惴着拳拳赤子之心送来落榜生“福音”的他,还没有来得及讲完意图就被校方粗暴地“推出”校门。事有蹊跷,他带去的介绍信偏偏少盖了一枚骑缝章,竟被曾经被骗过的人怀疑为“骗子”,请进了汉中市公安局。
得益于学生家长兼当地市长的过问,问题澄清了,风平浪静。“闭门羹”吃过,公安局“呆过”,但他就是没有退缩,依然到处游说,热诚介绍。天佑其诚,他在汉中招生270多人,这一年,也就是创办院校的第二年,西译的全日制在校生将近千人。
狂沙吹尽始得金。丁祖诒为国育才的崇高的献身精神,一开始就感动着每一位与之接触的良知有知之士,他在困厄、挫折、打击面前所表现出的坚强,百折不挠,永不停息的奋斗精神,始终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个人。
驰骋在学子的伊甸园
弹指一挥间,西安翻译学院已成为具有专科学历证书颁发资格的民办院校,得以招收部分计划内统招生。西译办学15年,没花国家一分钱,没有任何人赞助,仅靠低廉的学费,如今已成为占地千余亩,校舍36万平方米,校产近5亿元的庞然大校。1998、1999和2000年连续三年,分别招录6800、7000和9700名新生,在校全日制住校生2.2万人规模的西译登上全国规模之最。西译毕业生连续13年就业率达98%,年薪5万、9万、40万如星光闪烁,众多毕业生出国深造,众多专科毕业生跨越本科段考上国办名牌大学研究生……已成为西译一道又一道绚丽夺目的风景线。
生活的跌宕起伏,命运的无常变幻,造就了人生的悲壮传奇与可歌可泣,如果说,当年18岁的丁祖诒顺利通过了大学最后的“政审”关节,那么,今天中国科研领域也许会出现一位“数学奇星”。然而,命运的手指只那么轻轻一转,一个当代民办教育家的神奇前程就这样注定了。一个人的“数学梦”破灭了,而千百万个嗷嗷待哺的失学青年却踏着这个人躬起的脊梁架设的天梯走进实现理想的天堂。
丁祖诒为把他的翻译学院办成一所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民办大学,捧出了一道壁垒和两个模式。
丁祖诒以超人的胆魄对80%的入学新生设置了一道众多民办院校不敢涉足的壁垒,将生源定位于高考专科分数线,决心与国办专科院校甚至与二流本科院校决一雌雄,实行“严进严出”的办学方针,以大批高质量的生源来确保西译的群体学习氛围。
丁祖诒还一反普通高校单一专业的常规,创造并实践了“外语+专业+现代技能”的双专业复合实用型涉外人才培养模式。
学生入学后,要先学英语大专全部课程,取得国家承认的专科文凭,继而选修学院设立的第二涉外专业,同时还要学会办公自动化、礼宾礼仪,现代公关、外贸函电、书法和小汽车驾驶技能。这种把高等教育与继续教育融为一体,把专业学习与技能培训合二为一的教育体系,丰富了高等教育的内涵,造就了一批批一专多能的复合实用型人才。
丁祖诒首创的复合实用型双专业涉外人才教育模式3次敲响了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的大门,众多国家领导人出席并肯定了这一模式。这一模式铺就了“西译”万名毕业生的绿色就业通道,赋予“西译”足以与公办高校分享生原的强劲实力,孕育和引发了我国高等教育向高等职业教育、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变革以及与国际高等教育的接轨。
与教育模式相匹配,丁祖诒针对落榜生为主体的校园实行了三重封闭。学生未到周末一律不得出校门,减少事端;男女生公寓相互封闭,不准谈恋爱;教学区与公寓区互相封闭,杜绝旷课。为的是排除外界干扰,为的是让学生潜心学习。
拿破仑说得好,灵魂比剑更强,在丁祖诒的感觉中,纪律约束,封闭管理只是一种外在形式,而育才的真正关键则在于一颗爱心。“一切为了学生”才是西译办学的宗旨。
丁祖诒有着博大而宽仁厚爱的灵魂。正是对国家、对民族、对青年一代的超越庸常的“大爱”促使他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挽救高考落榜青年的光荣而艰巨的历史重任。丁祖诒是一个用爱心组合起来的大写的人。
15个元旦,他与学生同歌共舞;15个中秋,他将一块块月饼送到学生手中;到灶房检查伙食成为他巡回各教学区的首选驿站;学生病了,他代垫费用派车送往医院;家庭贫困,他常予以减免学费,安排勤工俭学;学生受欺侮了,他身先士卒与歹徒搏斗;毕业生被骗了,他花钱请律师为学生打官司;他为学生,敢于冒犯顶头上司;他为学生,敢向上苍请命……办学15年,他至少在16平方米的院长办公室里睡了10年,饿了,泡包方便面;困了,就倒在沙发上,96级以前的学生都私下亲切地称他“沙发院长”。96年以后的学生还将社会上的民谣改成:“院长院长我爱你,就像老鼠啃大米……”
一个世纪以前,在山东出了一个武训。他有感于自己出身贫寒,没有文化受人欺侮,遂沿街乞讨为穷人的孩子兴办义学,他的义举为后世传颂。100多年后的今天,一个落榜生,呕心沥血地奋斗,为了落榜生创办了一所全国知名的大学,他圆自己的梦,还要去圆成千上万与他同病相怜人的梦。
东方哈佛的不解情结
鲁迅先生曾经指出,中化民族从来就不曾缺少于危难之中挺身而出敢于为民请命的人。这种人实际上就是民族赖以生存、奋斗不息的脊梁式的人物。
丁祖诒用其大半生的创业,来比照如上观点,是再贴切不过了。
丁祖诒心中有一个美好的梦想:那就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建立一所东方最好的民办大学,就像美国的私立“哈佛”,日本的私立“早稻田”那样。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去造就一大批精英式栋梁之材。
一介两袖清风的布衣贫儒,想要成就辉煌伟业,在平常人看来实在是无异于“蚍蜉撼大树”然而,在丁祖诒健行的步履下,它已逐渐从神笔马良的东方神话中走出来了。
如今的西安翻译学院——一座崭新的大学城,早已在西安南郊迷幻般地耸立,它南依翠华山境,东临太乙长河,逶逶迤迤,潇潇洒洒,林木葱翠,青石婉然;校园依山傍水,天空明亮湛蓝,是一个潜心读书的世外桃源。
拥有2.2万名住校生(本科生万余名)的“西译”不仅创造了华夏民办大学“规模”之最,“招生”之最,“声誉”之量,而且使“西译”成功地实现了生源结构由“落榜生”向“线上生”和“学历层次”由3年“大专”向4年“本科”的两个转化,创造了全国民办高校生源“质量”之最。
世纪之交的2001年秋季,西译近3000名97级本科和98级大专毕业生,于毕业前的6月初就被专程来院的全国368家“三资企业”聘用了98%,其中不乏年薪5万以上的一批佼佼者,创造了自86级到98级连续13年毕业生推荐的满堂红。2001年5月份《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中国农民报》和《陕西日报》等多家媒体,均在头版头条以“西译毕业生走俏”为题对“西译”毕业生被高薪聘用作了典型报道。
1996年“内参”透露,国家权威部门对在南方“三资企业”工作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工作能力所作的专项抽样调查表明,排名第一的竟是民办“西译院”。
“西译”学子或以其外语优势,或以其双专业集合型人才特征,或以其就业于“三资企业”的近水楼台,15年来,在万余名毕业生中,通过“西译”公派,企业选派或业务驻外,通过“托福”考试自费留学或出国劳务者2000余人。“西译”公派美国杜布克大学留学(每人享受全额奖学金4.4万美元)的大专生冯君、顾莉娅和余卓涌均已取得硕士学位并留美工作。1993年“西译”一次送出100名在校生赴吉尔吉斯斯坦国立师范大学留学,开创了西北五省大规模出国留学之最。
担任哈佛大学驻京办事处翻译的“西译”毕业生张晓梅,带领美国专家来陕考察时,其流畅纯正的口语翻译能力受到省考试中心领导的高度赞扬并见诸报道。“西译”91级大专毕业生与众多公办高校生竞争,有幸被法国里昂银行聘为驻华分行行长助理,月薪数千元,“西译”96级旅游专业大专生洪沂1999年刚刚毕业就被上海市多家涉外企业争聘,月薪炒到3800元,终以一家提供一套住房,解决户口接该生父母进沪方遂心愿,该生流利的英语受到内贸部部长吴仪的赞扬。1996年新加坡银行系统在陕招30名劳务白领文员,几经周折,以月薪7000元招录了30名西译学子。今年3月份,四川迈普数据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外事业部以年薪5万元向全国招聘市场代表。在与西北大学、西安外国语学院和陕西师范大学在三所公办大学的同台竞争中,西安翻译学院被录用的6名毕业生竟占17名中的30%。这些不争的事实再一次说明了西译“优秀毕业生英语水平尤其是口语水平并不比国办四年制英语本科毕业生逊色。负责招聘的罗鹏副总经理感慨地说:“我是第一次来民办西译院,也是我们公司第一次来民办院校招聘。真是百闻不如一见,西译院不愧为民办院校的领头羊。通过这次招聘,使我们对民办院校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下次我们一定来贵院多招人才。”
在众多用人单位寥寥无几的录用名额中,“西译”学子呈垄断之势屡屡发生。“西译”前几任闯荡沿海开发区的众多毕业生由就业初期的“白领”文员过渡为“总经理”、“董事长”和“总裁”者已屡见不鲜。
尾声
丁祖诒教授以其对中国民办高等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和无私奉献,先后被推选为“东方之子”,陕西省政协常委、亚洲名人、中华新闻人物、华人百杰等。百名驻华使节两度专程参观西译;全美20多所大学校长同时专程来华访问西译签订友好协议;丁祖诒被特邀赴莫斯科为申奥助威;十多位国家领导人或为其题词、或与其合影、或亲临视察研讨;国内外上百家媒体聚焦西译,聚焦丁祖诒。他登上巍峨耸立的秦岭山脉,脚踏着绵延千里的黄土地,多少年来一直存于心底的那个苍凉而古老的声音又一次响起,那声音如海啸松鸣,如龙吟狮吼,让他激情似潮……
又一个寻常的夜晚,丁祖诒拖着疲倦的身躯斜靠在沙发上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强光下的影子被拖得很长、很长,他梦见自己走进了一个巨大的棋盘,棋盘上的棋子硕大而繁密,他吃力的,一个又一个地将它们挪开,每挪开一步,都留下一个鲜红的印记……
梦醒时分,已是东方泛白。丁祖诒推开窗户,听到一阵阵强劲悦耳的广播声,操场上、河滨小道撒满了晨读的人群。由眼前的2万多名西译学子,丁祖诒仿佛看到全国200多万嗷嗷待哺的民学大军。
梦醒时分,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千里之外的南海之滨,传来聚会一堂的数十名刚就业的毕业生异口同声的话音:“丁院长,我们感谢你!”,“丁院长,我们想念你!”
丁祖诒刚毅而严峻的面容一下子变得松弛、模糊、柔和、甜美,两颗晶莹的泪珠滴在墨迹未干的条幅上,那条幅书写着七个大字:“人间正道是沧桑!” (供稿 赵利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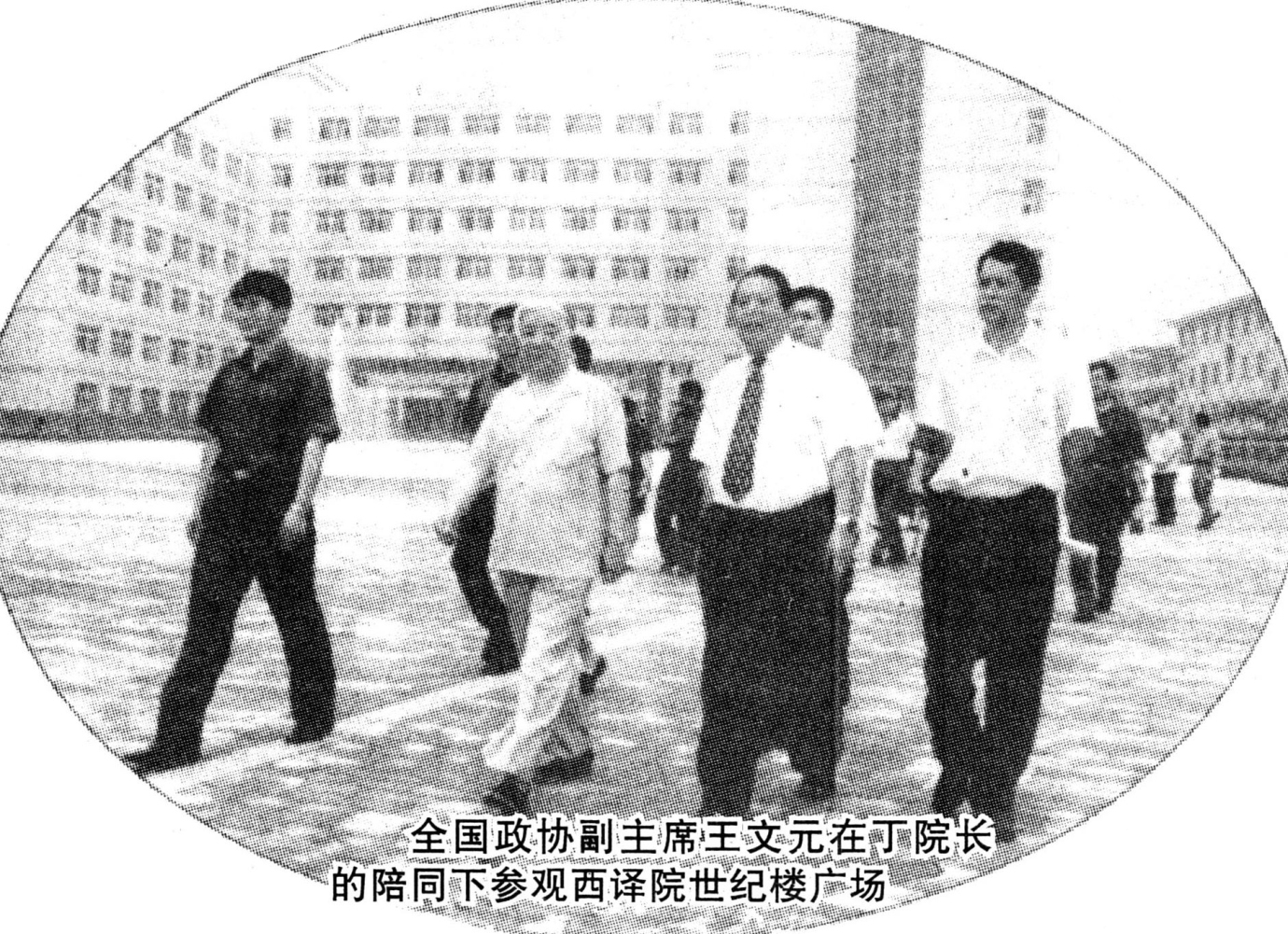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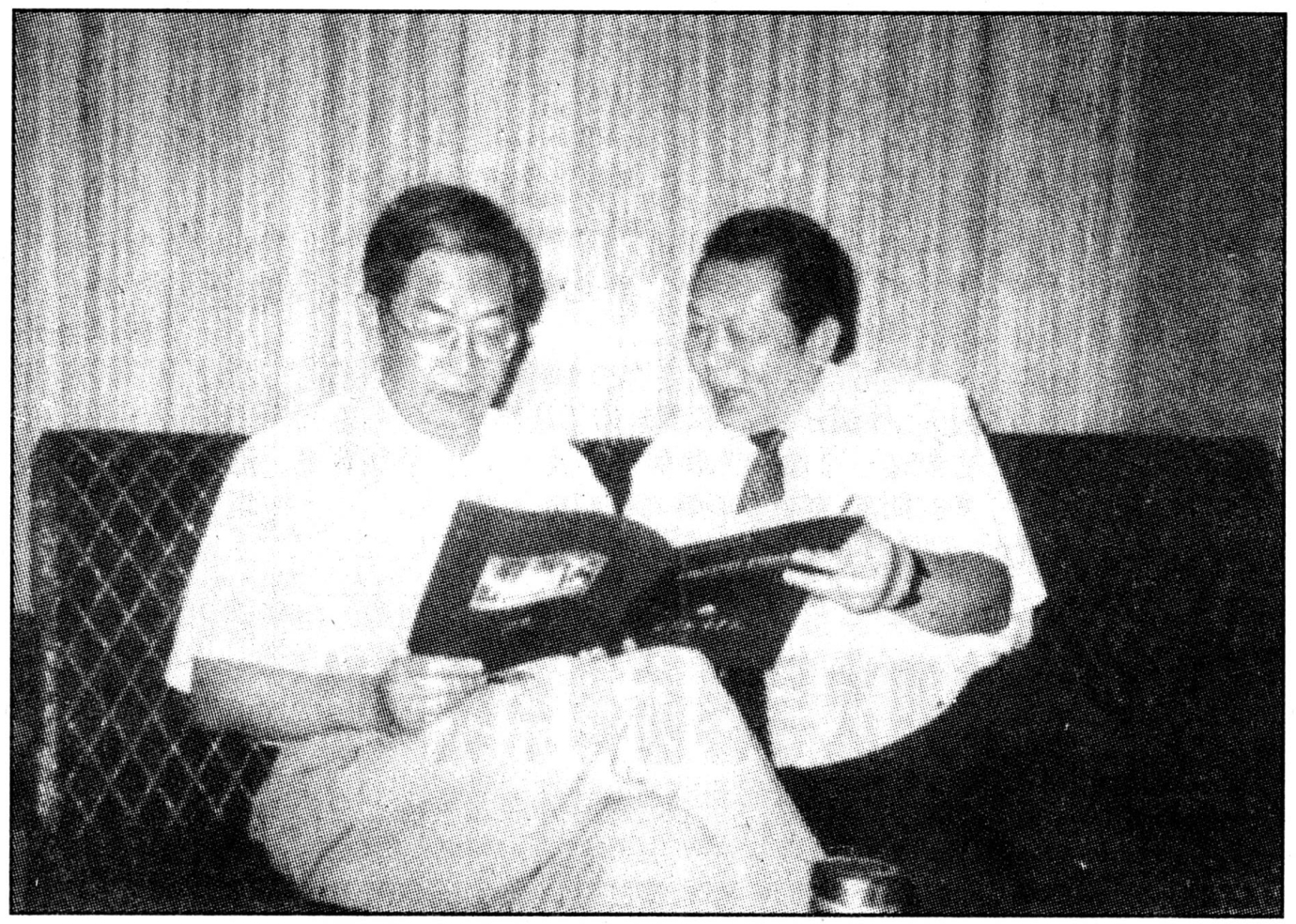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和西安翻译学院院长丁祖诒在一起

蓬勃发展的中国民办高校——西安翻译学院2.2万名学子为申办奥运会助威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