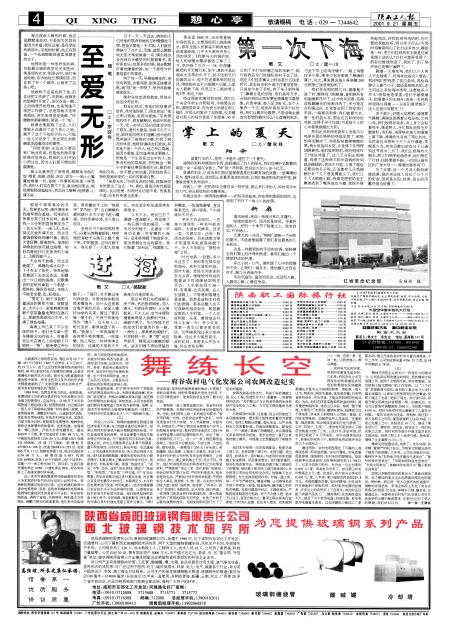赶海
散文 □文/郝晓新
那是个异常寒冷的冬天。我弃笔从军、满怀惆怅来到海军烟台基地。同来的伙伴都分到了技术兵种,独有我一人分到团直指挥连当了一名火头军。一连几天,乌云阴沉沉地布满天空,西北风像饿狼般呜呜嚎叫着,鹅毛大雪狂舞,碧海怒吼,惊涛拍岸溅起的浪花越过海塘,前赴后继地扑打在营房的石墙上,飞溅到窗户上。
天空终于放晴,西北风疲倦了,沸腾的海水似乎一下子失去了依托,哗哗地喘息着退下去老远老远,袒露出一片辽阔的海滩。沉默寡言的老班长拿起一个条筐一把铁钩,慢吞吞地说,年轻人不能老坐着,走,赶海去。
“雪花飞,蛎子顶盖肥”,童谣说的果然不错。放眼望去,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的海蛎子层层叠叠地聚附在礁石上,那蛎壳表面凹凸不平,长满了绿色海藻。
海滩上早已来了不少活泼的孩子。他们手中拿一把鸟喙般尖尖的钩子,对着那些生长在礁石上的海蛎子只轻轻一“啄”,蛎壳便应声分家,再用戴在手上的“铁指甲”灵巧地一铲,白白嫩嫩的蛎肉就汁水不少地飞进小罐里。动作优美协调,令人赏心悦目。
老班长可不耐烦那样秀气,闷着头挥舞着蛎钩,哗哗地把海蛎子从礁石上整个揭下来,扔到筐里,这叫打蛎子头。班长择了一只肥大的海蛎子,一下撬开,双手捧过来叫我尝尝。尽管他拼命鼓动那笨嘴拙舌,说什么这是烟台海产里的珍品,法国人嗜好如命的名菜,错过了要后悔一辈子的。可我宁肯被他骂作“傻子”,也不肯入口,班长见状,鄙夷地望了我一眼,“吸溜儿”一声将海蛎子连肉带汁吸到嘴里,一阵猛嚼,脸上现出一种异常满足的神态。说真的不是我不开化,实在是生吃怕里面带有病原虫。
工夫不大,班长已打了满满一筐海蛎子。我也拣了一些五颜六色的扇贝、一堆半尺长的蛏子,还逮住一只身后长着一对背鳍的小海马。后来将其晒干制成标本,成为我烟台当兵的留念。我们抬着“战利品”,唱着歌儿,高高兴兴地回家去。
班长叫我们先把海蛎子洗干净,然后放到锅里,加入清水,不放任何调料,大火煮起来。不大工夫,空气中便弥漫着鲜得使人欲醉的气味。海蛎子熟了,早已按捺不住的战友们如饿虎扑食一般,一涌而上,那煮熟的海蛎子,只须轻轻一扒,便“嗄”地应声裂开,裸现出白嫩嫩的蛎肉。战友们顾不得怕烫猛吞到嘴里,一阵雄咂豪嚼,直说鲜美无比、满口留香,个中滋味妙不可言。
多年之后去深圳,一位客户请我吃一种名叫蚝的海珍,大讲如何鲜美,及至一尝,又硬又艮,还有一股淡淡的怪味。后来请教方家才知道原来蚝就是海蛎子干,令人不免陡生“曾经沧海”之叹。
时光如箭,一眨眼,多少年过去了,我时常在梦中回到烟台,来到大海的怀抱。面对大海,老班长用浓浓的东北乡音,缓缓地对我说的那番话不时清晰地回响在耳边:人生就如同大海一样,有落潮,也有涨潮。在人生道路上,不管遇到落潮还是涨潮,那都是造物主对我们的恩赐,都是完整人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都是最宝贵的人生财富。一个人应该积极、乐观、睿智地去对待人生每一天!多少年来,我都一直牢记着老班长的话,它伴随我闯过多少惊涛险滩,经过多少喜怒哀乐。此时此刻,我是多么怀念大海,怀念老班长啊!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