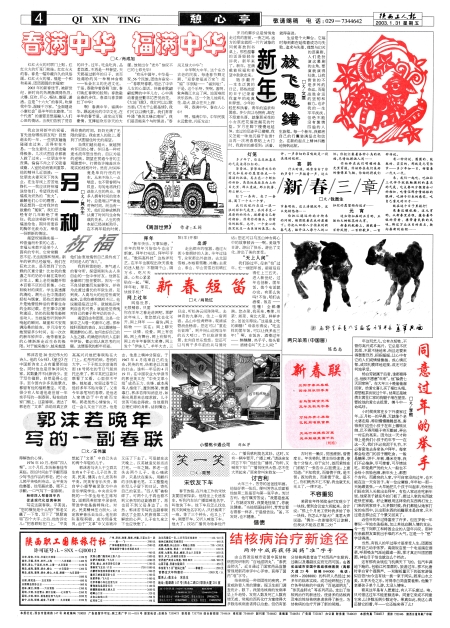
同意过年的举手
□文/李根
年这玩艺儿,它有点韧性,不管你高兴或不高兴,它总是不厌其烦、不屈不挠地来,而且还要来得轰轰烈烈、招招摇摇。让心中有它的人们或情绪激越,或心情沉郁,或顶礼膜拜地迎接,或无可奈何地承受。
杨白劳就属于后者,谁都看得出,他极不愿意“年来”。他“躲债七天回家转”,在大年三十晚偷偷溜回家,给爱女喜儿买了根红头绳,原想粗茶淡饭过个年,结果还是被债主黄世仁家的狗腿子堵在屋里,要抢他的爱女去抵债,搏斗中一命呜呼。
小时候我常在乡下外婆家过年。正月初一的早晨,天就像个老太婆走路,特别慢慢腾腾显亮,害得我们这些小孩子在床上辗转反侧,巴不得用棍子将天戳破,弄出一村庄的亮来。因为这一天才称得上是我们小孩子的年节——在这一天,我们不必拘泥于礼节,不必客套地去各家各户拜年。每家都会给进门的孩子赠吃食,一般是糖果、饼干、年糕、爆米花等,我们不必推辞,尽可接着,可尽情地吃。即使最严厉的大人一般也不会给小孩脸色瞧,新年头上,都图个吉利。而最穷的人家,宁可自家没肉过年,也不能在这一天穷孩子。有一位应舅娘,年年初一那一天她最紧张。一大早她把几个孩子叫起床,吩咐他们赶在别人头前出去拜年,有些人家还在吃新年饭,他家孩子就在外拍门板了。接过人家的东西就赶快往家跑,好让舅娘用这拜来的东西再打发上门来的别家孩子。大多数时候,我们都能从她家打发的东西中,认出那东西的祖籍原本是自家,只不过是去那边应了个景又回来了。
近些年的年过得富庶了许多,但压岁钱一年赛似一年地水涨船高,加上其他应酬人情的支出,令一些下岗职工和特困企业的人望年兴叹。那种在亲戚朋友面前出手难的不大气,岂是一个“愁”字话得清。
当然,有钱人的年过得才是享受人生。团圆饭不用自己动手张罗,高级饭店里一个电话搞定酒菜,呼朋唤友气派地圆桌一围,那才真正叫团团圆圆,神仙日子怕也就这么个档次。
还有那有余钱包飞机满天下飞的,包汽车满地下跑的,包船江河里漂的,旅游过年,那不比唐时李白背个酒葫芦,一双脚板量天下的孤家游强似百倍?如今这有钱一族一家子同乐,既享山水之美,又享天伦之乐,衬得李白简直要羞惭,他撇下老婆孩子单个儿游,太没人情味。
看来这年是有人愿意过,有人不乐意过。唉,只可惜这过年不能差额选举,同意它来或不同意它来,以多数压倒少数定夺。果真如此,我这心真还替它担着,年——它还能来得了么?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