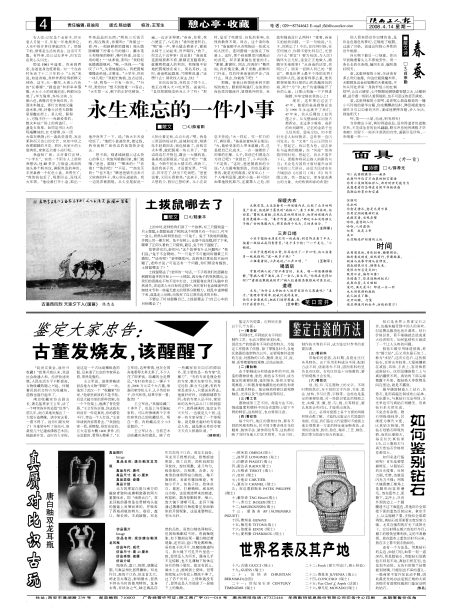
永生难忘的一件小事
□文/薛瑜阳
有人说:记忆是个金筛子,时光老人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拨弄它,人生中的许多往事就消失了,那留下的,常常是生活的真金。这话可不假。有件事,虽已过去多年,但它总在我心头闪光。
那是1961年盛夏,我来到西安,在爸爸身边度暑假。对一个在农村生活了十二三年的小“土包”来说,初进省城,我样样都觉得新鲜又神奇。这不,天一擦黑,大街上白色的“长棒棒”、“圆盘盘”和那串串簇簇、大大小小的玻璃泡泡,转眼间全亮了;华光璀璨,烁烁交映,五颜六色,真像百花争艳似的。当洒水车驰过,那灯光倏地又融进水里,嗬,好像天河把无数颗星星撒在街上。星儿呢,踩得上,可捉不住……我最爱看的,数火车站广场上的两盏灯。一盏是五角星,如同是用巨大的玛瑙雕刻的,红光熠熠,似一团火焰在燃烧;另一盏晶莹透亮,发出柔和而又洁白的光芒,宛如中秋之夜那圆圆的月亮。那时,我家乡的土崖湾里,家家还点着小油灯呢。
我盘桓广场,正对着灯出神,“小学生”,突然一个陌生人上前和我搭话:他40多岁,方脸盘,高高的肩头挎个帆布包,满眼焦急的神色,手里拿着一个红色小盒。我愣住了。“我的钱包丢了,现要回去,没钱买火车票。”他说着打开小盒,取出一件亮晶晶的东西:“两块三毛钱买的,现在贱卖,你要吗?”我接过一看:呀,一把新崭崭的圆规!端头圆圆螺帽下拧着小巧的插口、蘸水笔头和细细的钢针,精巧玲珑,还是三用的呢!“一块多钱,卖吗?”我轻轻抚摸着圆规问。“唉,一块钱……”他叹了口气,失望地摇摇头。我把圆规慢慢还给他,正要走。“小学生,你有一块几呢?”我赶忙掏钱,边点边说:“一块、两角……只有一块半。”“行呀,卖给你!”想不到他竟一口答应:“火车票一元,剩下的正好吃顿饭。”他冲我笑了一下,说:“我大半天没吃饭了。”他把小盒递给我,接过钱,转身就朝广场旁边的饭馆快步走去。
想不到,刚进城就碰上这么快心的事儿!我旋风般跑回家,推门就嚷:“爸爸,圆规!”“哪来的?”“你猜!”“拣的吧?”“不是。”“商店买的?”“也不是!”瞧爸爸猜不出来可又较真的样子,我心里乐滋滋的。我一边晃弄着圆规,从头至尾叙说一遍,一边洋洋得意:“爸爸,你看,我占便宜了,八毛钱!”谁知爸爸听后,“啪”地一声,拳头猛击着桌子,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厉声喝斥:“放下,你怎么干这种事?没出息!”爸爸竟连圆规看都不看,眼睛直直瞪着我,就像两把逼人的利剑。我惴惴不安地把圆规放在桌上,莫名其妙。这时,爸爸抓起圆规,气咻咻说道:“还愣什么?领我找人家去,快!”
在站边饭馆,我找见了那个人。他正在埋头大口吃米饭。爸爸问:“是你把圆规卖给我儿子了吗?”那人抬头看见我,点点头说:“嗯。我是三原县防疫站的,进城取疫苗,刚搭电车赶着回去,钱包被偷了,没钱买火车票,就把圆规一块五卖了。”他边说边打开挎包,露出一大摞药盒。爸爸亮出圆规说:“是这个吧?”“就是。今晌午民生大楼买的,两块三,是给我孩子的,才没要发票。”“同志,你辛苦了,快坐下吃饭吧。”爸爸说着,又回头看着我:“这孩子,为别人想的少,替自己想的多。从小在农村,是受了些落后、自私的影响,也怪我教育不周。同志,这个请你收下!”爸爸顺手从衣兜掏出一张贰元的人民币,连同圆规一起放在了饭桌上。这时,那个叔叔眼里闪着激动的泪花,双手紧紧握住爸爸的手:“谢谢,谢谢你。同志,你真好!”蓦然间,我疚愧交集,鼻子发酸,拔脚向门外走,耳后传来爸爸的声音:“没什么。同志,你就收下吧!”
那晚,爸爸让我领他来到买圆规的地方。眼前那两盏灯,在浓黑的夜色里泻银流丹,显得格外明亮。我忍不住说:“火一样红、雪一样白的灯,真好看。”爸爸却意味深长地说:“火,能给受冻的人带来温暖;雪,总是把自己化成水,一点一滴都给了田里的庄稼。儿子,你说它们都是在为自己吧?”我脸红了,小声回答:“不是的。”这时,爸爸摸着我的头说:“人生最难做到的,但也是最宝贵的,就是光明磊落,没有私心!一个人唯利是图,就和小偷一样可恨!如果他投机取巧,还要乘人之危,那就和强盗没什么两样!”接着,爸爸又拍拍我肩膀,一字一句地说:“儿子,你别忘了!今后,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你都不要先利自己,光想占什么‘便宜’!要为祖国,为人民!胸怀大公无私,堂堂正正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从爸爸的话里,我明白了:原来一切损人利己的“便宜”,都是世界上最不干净的东西!祖国和人民,爸爸看得那么重,使我联想到雄伟壮丽的山和浩瀚深沉的海,两个“为”字,如千钧重锤敲开了我的心扉,让那山和海一下子拥进胸膛,牢牢定格在我的心上!
现在,这件事已过去了47年,敬爱的爸爸薛维亚也在1990年永远离开了我们。47年来,我从后稷故土赴雪莲之乡,从戈壁油城又回到古都西安,走过多少艰难、曲折的坎坷路呵,记忆的金筛子也几经风雨、雷电交加,但不管时光老人如何拨弄,这件事一直闪闪发光:在“文革”乌云压顶的日子,想起它,我以笔为枪,迎击诬枉与迫害的棍棒;在“风波”惊涛裂岸的时刻,想起它,我从不落井下石,更鄙弃将同志推入陷阱的勾当;无论是为国育才面对塞外油田子校的三尺讲台,还是为民请命在古城创办《北国月(周)末》的不眠之夜,我一想起它,浑身就充满山的力量、火的热情和春的希望!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