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导读
余英时评冯友兰:犹在“功利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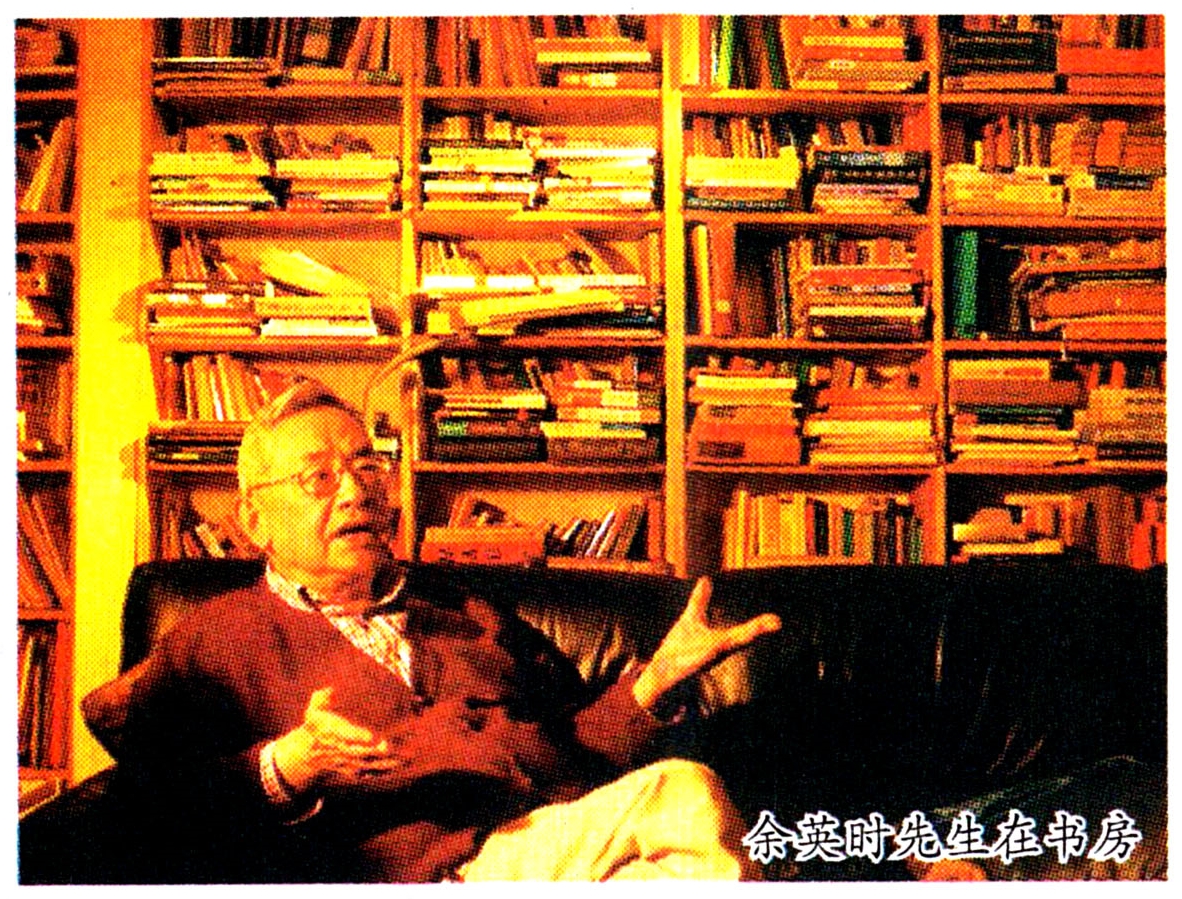
余英时先生在书房
余英时先生在与学者刘梦溪的一次谈话中说,他对冯友兰先生晚年写的《三松堂自述》一书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原准备想写文章。但是后来当他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的朱子国际学术会议上与冯友兰及其女儿宗璞见过一面后,他说,尽管他对冯友兰有看法,但却不便再写文章公开批评了。看到这则材料,当时我就很想知道余英时先生对冯友兰究竟有怎样的看法和评价?新近出版的《余英时访谈录》一书终于将这一谜底揭开。
1982年夏天,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举行了一个为期长达十天以上的“朱熹国际会议”,冯友兰先生作为大陆代表团成员应邀参加。在为期十天的会议中,余英时先生经常有机会与冯友兰接触并聊天,原因是当时来自大陆的其他与会学人大多不太愿意和冯友兰接近,且唯恐避之不及。
在此间,余英时还促成了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冯友兰荣誉博士学位一事。具体经过是,在另外一个会议上,余英时对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教授偶然谈起,作为冯友兰先生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似乎可以考虑赠予冯友兰先生一个名誉博士学位。毕竟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料,狄百瑞教授竟认真考虑了这个提议。很快哥伦比亚大学便作出决定。决定在1982年的9月授予冯友兰先生荣誉博士学位。余英时先生应邀参加了授予仪式。晚宴时余英时又坐在冯友兰旁边,二人交谈甚多。正是因为这些近距离的接触、聚谈,余英时先生对冯友兰才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并进而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和评价。
余英时先生认为,冯友兰思想的最深处始终有一种向“帝王”进言的意识。这只要读一读他的《新世训》中《应帝王》一章即可知。余英时讲,冯友兰不敢以柏拉图的“哲学王”自任,他的中国背景使他只想做“王者师”,或者至少要做政治领袖的高级顾问之类。纵观冯友兰的一生,我们不得不承认余英时的这一评价是大体公允的。从早期的献媚蒋介石,到40年代出席国民党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从“土改”的粉饰太平,到“批林批孔”的摇旗呐喊;从迎合“总裁”,到歌颂主席,乃至媚谄女皇,冯友兰一生不脱“应帝王”情结。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一书中对冯友兰有这样一段评价:“冯友兰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像他《新世训》的最后一篇《应帝王》等,都是给蒋介石捧场的。在我们看来,一个学者这样做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有失身份。”同样,邹承鲁院士在一次访谈中回答记者“西南联大的先生里您最欣赏谁,最不欣赏谁”时,也坦言自己“最佩服的是陈寅恪,最不欣赏的是冯友兰。”
时至今日,为什么世人对冯友兰一直是多有异议呢?余英时先生认为,这和冯友兰提倡的哲学有密切关系。冯友兰在《新原人》中把人生分为四种境界,由下而上依次是:一、自然境界,二、功利境界,三、道德境界,四、天地境界。冯友兰自己是以“天地境界”自许的。西南联大时期,冯友兰路遇金岳霖,金氏开玩笑道:“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答曰:“到天地境界了。”遂相顾大笑而去。可惜冯友兰所谓“天地境界”云云,终不过是虚言诳语耳。正是因此,余英时先生才说,冯友兰以“天地境界“自许,但50年代以后他的实际表现似乎在“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之间。非但如此,他所有的所作所为都是向帝王进言的潜意识从中作祟,不过境界确实未超出“功利”之上而已。
□史飞翔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