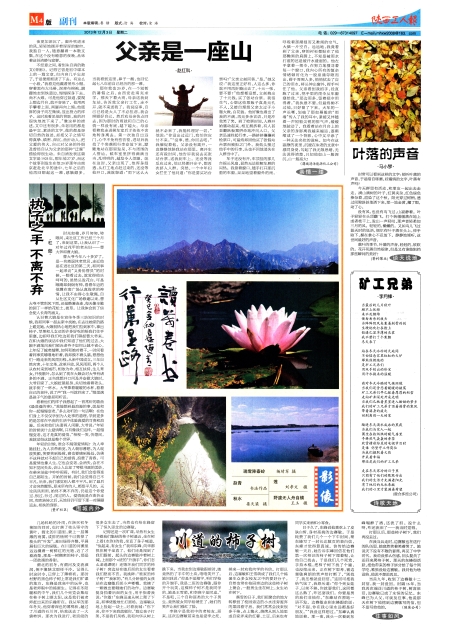父亲是一座山
·赵红科·

夜更加深沉了。窗外吹进来的风,轻轻地摆弄着厚厚的窗帘。我独自一人,随意翻着一本散文集,在这个没有睡意的夜晚,品味着这份清静与寂寥。
不经意之间,看到朱自清的散文《背影》。记得它曾是初中课本上的一篇文章,但内容几乎忘却了,于是便细细读了下去。有这么一小段,“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像这样的描述,文中还有很多,朱老用的都是最平实、素淡的文字,做的都是恳切自然的叙述,却把父子之情写得真挚、缜密、深沉,曲折动人,把父爱的伟大、自己对父亲的怜惜及曾经自认为父亲的那种“迂腐”描绘得很生动。朱自清发表这篇文字是1925年,那年他27岁,而这个故事则发生在他20岁那年由南京赶赴北平的途中,七年之后的他再回想起这一幕,感触颇多。当我看到这里,鼻子一酸,也回忆起七八年前自己经历的那一幕。
那年我也20岁,在一个短暂的暑假之后,由西安赴南充求学。那天下着大雨,母亲送我到车站,告诉我父亲打工忙,走不开,就不来送我了。我说没事,自己已经是大人了不必担虑,我会照顾好自己。然后劝母亲快点回去,因为那时的雨就和自己的心情一样没有底,越下越大。母亲看着我走进候车室后才依依不舍地转身离去。第一次独自出远门,心中不免有些彷徨,进站后我找了个角落把行李安放下来,默默地站在那里发呆,不与周围的人搭讪。候车室里挤得满满当当,乱哄哄的,越发令人烦躁。就在这时,父亲出现了,他浑身湿透,从打工地点赶过来的,还没等他开口,我就怨道:“雨下这么大就不必来了,我能料理好一切。”他说:“你没出过远门,我怕你应付不来。”“没事,爸,你回去吧。”我催促着他。父亲没有离开,一直静静地陪我站在那里。离开车还有段时间,他告诉我说去买张站台票,送我到车上。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已经挪开步子,想再次挤入人群。突然,一个中年妇女拦住了他问道:“你是要买站台票吗?”父亲立刻回答,“是。”她又说:“我这里正好有,人这么多,你就不用再折腾出去了,十元一张,要不要?”他想都没想,立刻掏出了十元钱,买了张站台票。我很生气,心想这些票贩子真是无孔不入,又暗自埋怨父亲太过于小题大做,白花钱。他好像也看出了我的不满,再无多余言语,只是冲我笑了笑。到了检票时间,人群开始骚动起来,相互拥挤着,有人甚至翻跃板凳拼命地冲向入口。父亲迅速拎起行李,一路挤挤攘攘到检票口,可最终却因他买了张假站台票而被拒之门外。我低头接过他手中的行李,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人群当中了。
车子还没有开,车顶挂的那几台摇头风扇,显然无法排解车厢的闷热。我靠着窗口,随手打开那沉重的车窗,呆呆地望着窗外的雨,呼吸着那潮湿而又难闻的空气,大脑一片空白。远远地,我竟看到了父亲,穿的衬衫都贴在了他那黝黑的肩膀上,不知是被雨水打湿的还是被汗水浸湿的。他左手拿着一把伞,在努力地搜寻着每一个窗口,我内心所有的复杂情绪顿时化为一股泉涌夺眶而出,碍于周围人多,悄悄拭去了自己的泪水,将头伸出窗外,挥手叫住了他。父亲看到我招手,径直跑了过来,把手里的雨伞从车窗塞给我,“那边雨多,留着把伞用得着。”我执意不要,但最终拗不过他,只好留了下来。火车的一声长嘶,划破了那如幕般的“雨墙”传入了我的耳中,紧接又伴随着一声短暂尖锐的排气声,缓缓地驶动了。我看着站在月台上的父亲的身影离我越来越远,逐渐缩成了一个背影,心中又平添了一种无法名状的滋味。如今在这寂静的夜里,沉浸在朱老的文章中感同身受,勾起了我无限思绪,无法说得清楚,只知他如山一般深沉,山一般高大!
(蒲城清洁能源化工公司)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