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导读
27个春秋的期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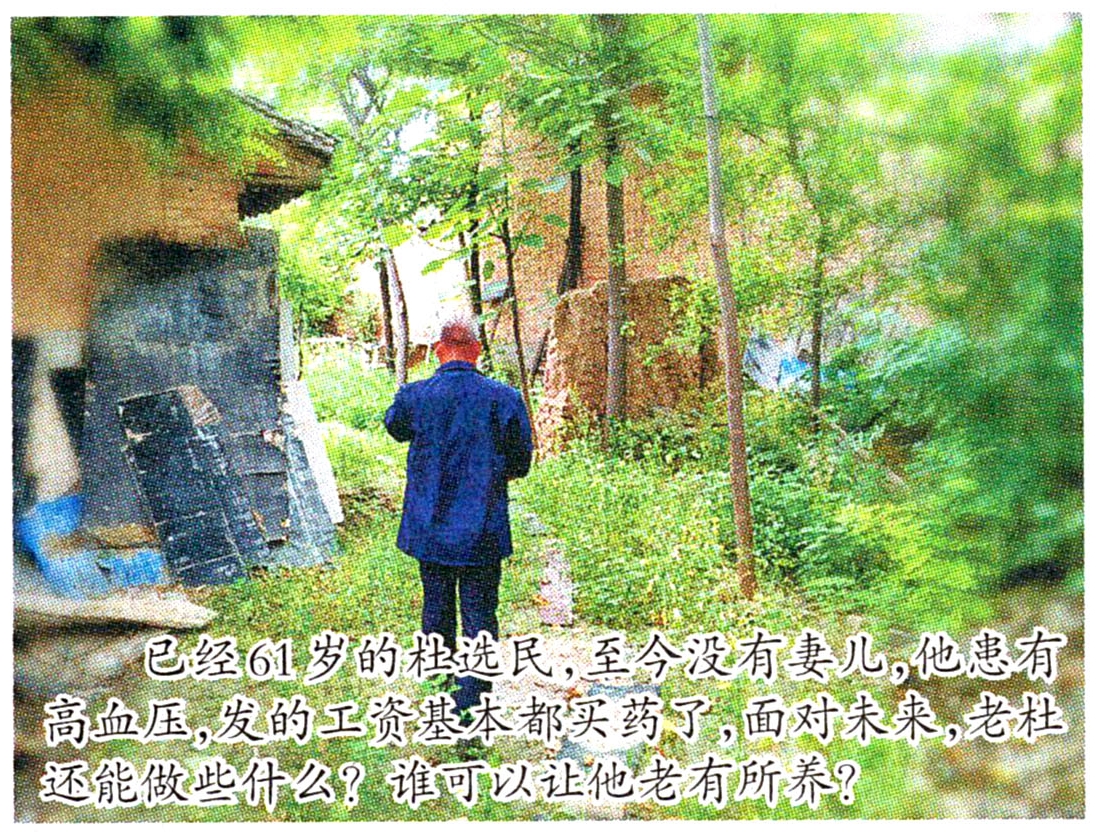
已经61岁的杜选民,至今没有妻女,他患有高血压,发的工资基本都买药了,面对未来,老杜还能做些什么?谁可以让他老有所养?
咸阳市渭城区北杜镇中心小学六十多岁的杜选民,工作二十七年,每月就两三百块钱工资,他没有回过几次自己家,而家仅仅一两里路程;没进过一次城,而离城不过三四公里路程。没买过几身衣服,更是没见过他生病进过诊所……
5月28日,记者见到老杜后的五六分钟内,跟他说了三句话,他从门房到大门口10米距离跑了5趟(开关大门)。他十分不好意思,让记者再次稍等,说先把这十来份报纸给领导们送到楼上去。背影消失在二层楼约十来秒后,满头银发的老杜又急匆匆冲出来,飞奔向学校大门口,嘴里还大声喊着:“我来开门”,紧接着一辆小型货车从学校院子里驶出。
学校领导说不亏待我
“1988年到北杜镇中心小学上班,当门卫,打铃,烧开水,除草修剪树木,打扫厕所,垃圾箱等杂活我都干,工资从1988年的70元干起,80、90、120……一直到2013年的350元。”谈起自己的工作,老杜如数家珍,感觉不到半点沮丧。
“工资一直这么低?有找过相关部门办理低保吗?”记者问。“以前领导都让我好好干,说学校亏待不了我。”老杜如此回答,并有些抵触地补充道:“低保都是没有劳动力的人吃的,我在学校上班,咋能吃国家的低保?”
他今年已经61岁了,从1988年的书记、校长王鹏义到2013年的书记杜保国,校长杜超,老杜告诉记者,他已经经历了20多任书记和校长。当年上班时,学校就没有楼,这么多年过来,学校从前到后全变了。旁边的路人告诉记者,她上学时,就是老杜在当门卫,为学校里干了许多活,她大学毕业都几年了,老杜现在还在当门卫。
我不能害学校领导
“这么多年,我没找过领导说我的事,甚至没有给其他人说过一次委屈。我总认为终有一天,上级会公正对待我,解决我这个问题。如果反映了,上级肯定怪罪校领导没处理好。”在学校隔壁他姐姐家里,老杜如此表达了他的观点,并一直喃喃重复,“我不能害人。”
“没在学校上灶时困难点,不过我没买过菜,有野菜能满足。我不太花钱,习惯了。”老杜轻描淡写了自己生活的艰辛。
“你就是嘴硬。这么多年你买的衣服最多三四身吧,你哪件衣服不是穿别人的?你身体那么好,二三十年不用看病?你生病是拿命在扛!”她姐姐一股脑说了许多。
“我买了,就是便宜点,也有不少呢!”老杜强撑着某种情绪,他眼神里透射出来一许幽怨,他嫌姐姐揭他短了。
“当年进入学校时,我弟与其他民办教师一样,发70元工资,挣一样的工分。可是其他民办教师们一个一个都转正了,而他却一直踏步走……”
“您都没自己去跑跑?”记者问老杜。“他就没有那个能耐,两次跑得就没有路费了。”他的姐姐如是说。
老杜两只手交织在一起,不自然地撮弄着手指。“学校是国家单位,我一直相信总会有个样子。”在一旁沉默的像个孩子的老杜,冒出了这么一句。
我觉得希望就要来了
2013年2月,老杜说他突然接到学校口头通知,以渭城区教育局有文件,要开除掉这些临时工为由让他交回大门钥匙,并停发了工资。对他而言犹如晴天霹雳。25年来,他昼夜不分,周内周末不分,五六个平方的门卫房已经成了他的家。多年等待的公正这一刻差点让他晕厥……
那一年,为了自己的问题,59岁的他终于去了一趟咸阳。相隔不足5公里,却是他几十年来第一次有时间进城。他用儿时的印象鉴定对比着这个高楼林立的地方,在迷茫中一遍又一遍地探索着、寻找着。直至2014年9月2日,他才完成了一份成型的“劳动仲裁申请书”,几经修改后提交至咸阳市渭城区劳动仲裁委员会后,却被其告知,时效已过,不予受理。上诉至渭城区人民法院后,法院到学校,与其所在镇教育组,专干以及学校校长,书记等进行了调解。给予老杜1988年到2013年经济补偿2万元,并让他继续上班,发每月1100元工资。“尽管里面有诸多的不合理,但我看到了希望。这次学校跟我签订了劳动合同,并给我发了一件雨衣,一双胶鞋,一个电热壶。国家一定会公正对待我的问题。”老杜显得信心满满。
学校就是我的家
周围人都说,这根本没有解决实质问题,这点工资连咸阳两区的最低工资标准(渭城区最低工资标准1280元)都不够,你为何非要一直坚持在学校?
“我的家就在学校,我对学校的感情要远远大于那个多年未归,杂草横生的家。我看报纸,说我这种情况今年7月底前就能解决,我坚信国家政策能改变我的‘困境’。”老杜这样坚持着自己的信念。
你渴望改变哪些现状?有什么样的诉求?记者问及他目前的想法。“我受的委屈不算什么,我认了。也没渴望改变太多,工资能有个两千多块就是我最大的梦想了。其实我就是想让人们知道社会上还有一个我,至少对我有一个公正的对待。”老杜说。
“学校最近要开运动会,上面要来人,老杜你尽快用油漆把学校大门刷下。对了,操场和园地里的杂草你也尽快铲下,花园里的植物叶子也修剪下。”接到领导的命令,老杜匆匆与记者告别,重新回到了工作中。
学校就是老杜的家,他与学校签订过两次劳动合同,可是合同里均载明不提供工伤、医疗、住房养老等保障。没有社保,没有家庭,也不知道他这样的身子骨还能坚持劳动几年……
本报记者 王何军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