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人们面临娱乐至死的“威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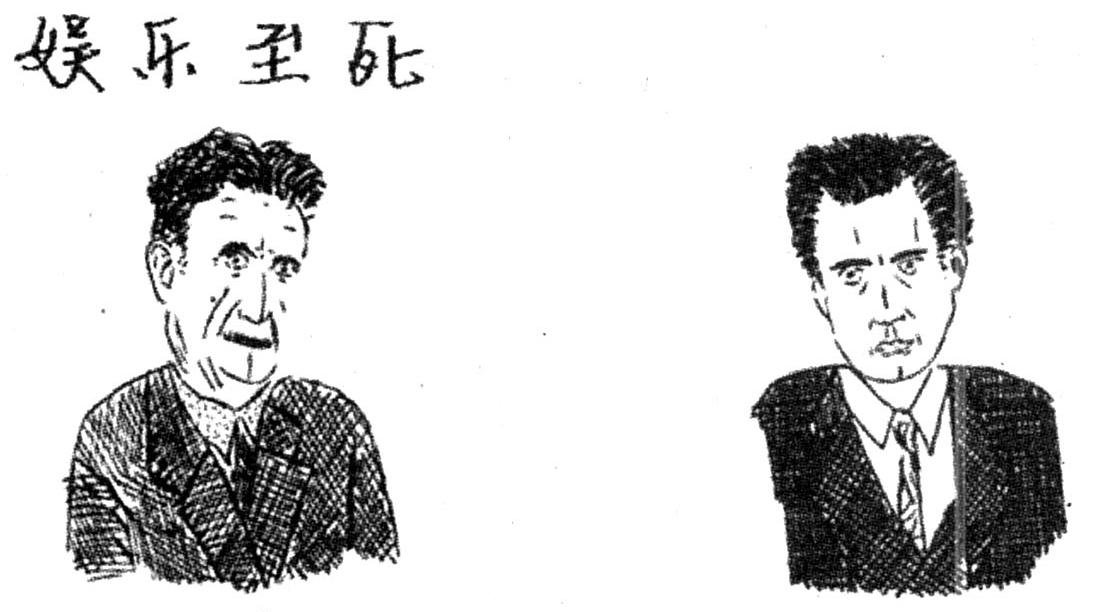
乔治·奥威尔 vs“一九八四”作者
阿道司·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作者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忧心忡忡地告诫我们,不要在娱乐文化中失去作为人应该有的思考能力,作为人应该追求的原本的单纯,因为娱乐可以改变政治、宗教、教育等领域个人的原则,为了迎合电视的形式而放弃初衷,最后生命枯萎。如果失去了这些,无异于死。作者深知自己的这番苦心,会被视作杞人忧天,疯人之语。但是,他不能够掩饰自己的清醒,不能够沉默。
人们面临娱乐至死的“威胁”
波兹曼看到,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也不会料到,人们面临的不是奥威尔警告的来自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是娱乐——致死的“威胁”。赫胥黎认为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是因为人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他清醒地看到,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人们,在崇拜互联网技术方面,用五体投地也不为过了。人们受这种技术的控制并且参与使用这种技术的控制,直达自己。
“互联网即隐喻”,建构交流新模式
波兹曼认为“信息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明确具体的说明”,媒介并没有这个功能,所以主张用“媒介即隐喻”一说替代。因为“媒介更像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例如,媒介将这个世界分类、排序、放大、缩小、着色,最后建构这个世界的意义。根据这个思路,我们可以说互联网即隐喻。互联网以及与互联网有关的微博、微信等交流方式,无一不加速建构我们的人际交流新模式、新感受,甚至新认识。
为了使“媒介即隐喻”这个命题被理解与被采纳,他以钟表为例,详细论述了钟表如何在制造分秒的时候,“把时间从人类的活动中分离开来,”人们便相信时间是可以独立存在的,时间可以成为精确和可计算的单位。当钟表以这样的面目重新出现的时候,我们接受这个观点比较容易:分分秒秒是人类创造的机械和自己对话的结果——正如芒福特所指出的“自从钟表被发明以来,人类社会便没有了永恒”。眼镜也是如此,眼镜不仅仅矫正视力,同时也告诉人们不必听信天命,人的身体可以依靠医疗技术得到完善。还有今天充斥在媒介中的那些美容广告,对美容术的依赖,同样使人们相信改变的力量,改变要依赖各种美容手术,这种观念的形成与此类广告的意图一拍即合。
网络对我们的规范强过电视
理论建构之外,波兹曼的基本思路是电视的时代是娱乐的时代,这种娱乐是以“看”为中心的,围绕“看”的娱乐形成了这个时代的共鸣,不论是政治家、教师、运动员、传教士、企业家还是新闻记者都深谙此道。这种共鸣在娱乐时代的表现是:政治家的智慧和驾驭能力被化妆术取代;电视播音员在吹风机上花的时间超过播音备稿的时间;商品的质量和用途在商品展示时无足轻重;优秀的教师靠把戏惹得同学哄堂大笑……
我们之所以能够把自己娱乐至死,是因为我们将陷入“美丽的新世界”中,这个“美丽的新世界”已经没有禁书的任何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冲动和自私;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李岩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