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远去的背影
——一个县委书记的人生片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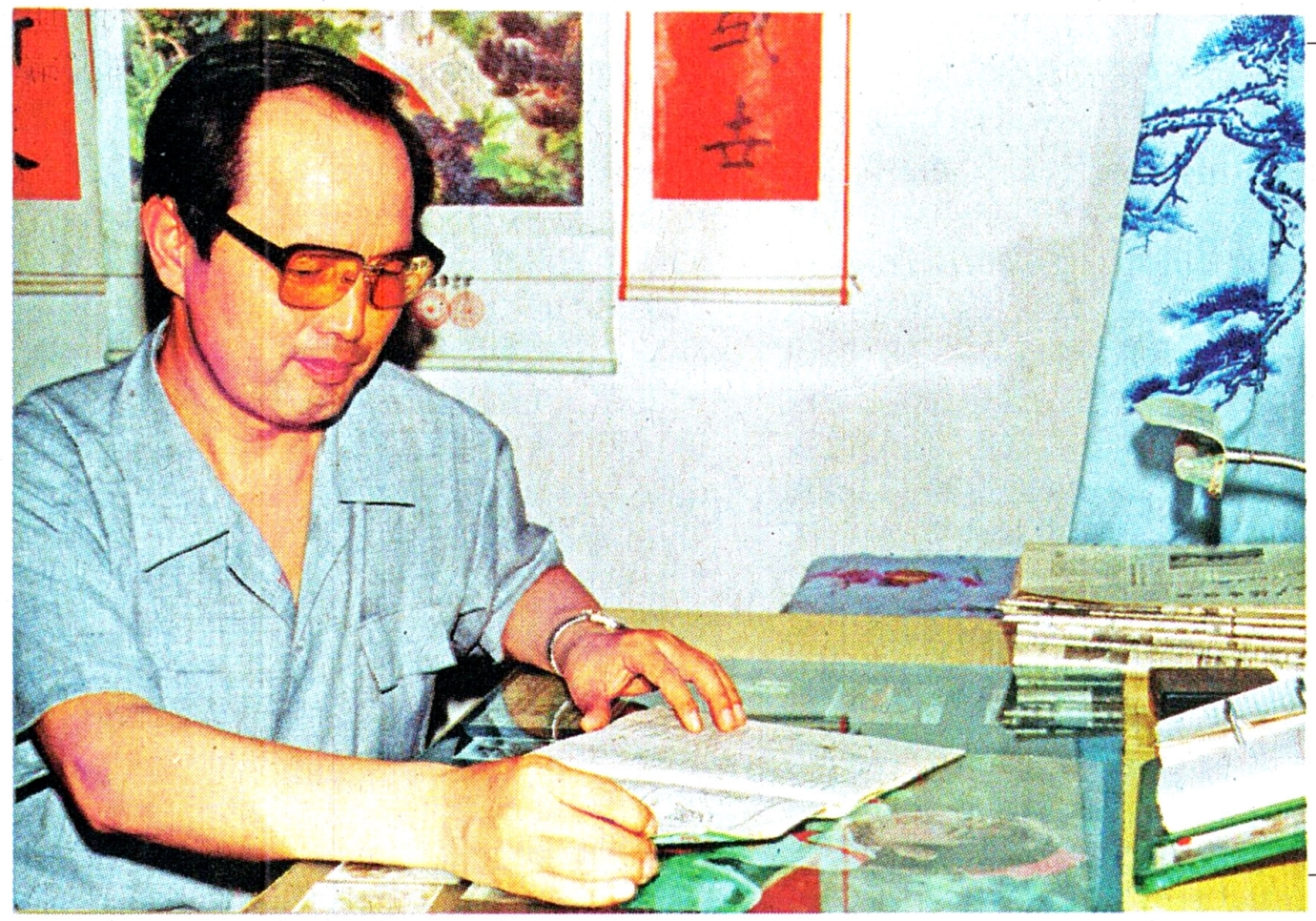
杨尚坤在家学习
(上接三版)
九零年的某个晚上,我坐在他家的沙发上,摇着扇子,拍打着飞起飞落的蚊子,和他面对面地聊着天。从国内到国际,我们漫无边际地乱扯着。扯着扯着,就扯到了个人的收入上。他告诉我,他的工资才一百六十多元,远远赶不上水泥厂工人的收入,水泥厂工人都三百多了。从他的神情里,我倒隐隐地窥探出他对水泥厂工人的羡慕。
他的妻子始终是一个机关的普通职员,上班干着属于自己的一份差使,下班则买菜系围裙下灶房,路上行走见谁都和和气气地微笑——不微笑不行,如果见了熟人不打招呼,那就有摆架子的嫌疑,一旦让杨尚坤知道了,她准会挨一顿批评。
至少两三个周末,我都在杨尚坤的家里见证了他的妻女回老家的情景。杨尚坤的老家在宜君,相距耀县六十多公里。那个时候,道路不怎么好,交通也不怎么发达,耀县与宜君之间,没有直接通达的车,且山路弯弯,忽而下沟,忽而上坡。要回宜君,还得在铜川换乘车,期间需要耗费四五个小时。
杨尚坤妻子与女儿一边收拾着行李,一边在议论着铜川开往宜君的班车的时间,她们担心自己行动迟缓,延误了班车。铜川每天开往宜君的班车并不多,一天大约两三趟,她们一旦与班车失之交臂,就会被抛弃于铜川街头。
杨尚坤叮咛着妻子女儿回老家后要看望这个,要探望那个——这些人要么是老人在生病,要么是年轻人在结婚——他性子急,嫌妻子磨蹭,督促她们快快走。
我询问他妻子,为什么不用县上的车送送自己呢?他妻子朝杨尚坤努努嘴,说他自己回老家都是坐班车,还能让我们坐他的小轿车?杨尚坤妻子的神情有着些许的抱怨,但很快就释然了,她说自己习惯了,非常习惯了,现在让她坐公车,她倒很别扭。
关于坐班车,我想起了一件终生难忘的事。有一年夏日的中午,天很热,我骑自行车从城东的一座桥上经过。桥下方不远处,是长途班车的停车点。从停车点到街道,得爬一道坡。我骑车从东往西行,老远看见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在坡路上吃力地朝上走。他脱了长衣,只穿着一件白色的背心,肩膀上如褡裢一般,一前一后地垂吊着两个鼓鼓的旅行包。我从后面瞅着那个男人,越看越像杨尚坤。这样的念头在我的心头纠集,但我坚信自己认错了人。一个县委书记,怎么像一个退休工人一般光着膀子?再说了,杨尚坤纵然出差归来,总不至于坐班车呀?
我奋力地蹬了几脚车子,车子一刹那就越到了那个男人的前面。我扭头回望,不禁怔住了:眼前的这个男人不是别人,正是耀县县委书记杨尚坤。
我下了车子,问他干什么去了?杨尚坤回答他去北京参加亚运会了,刚回来。参加亚运会,是他在任时惟一的一次奢华。据我后来所了解的情况,开亚运会之前,他就接到了上级的通知:凡县委书记都得去参加亚运会,这既是政治任务,又是特权待遇。他本来不打算去,但经不起周围人的劝说,于是就前往了北京。
我问他从北京回来,为什么没有车接呢?杨尚坤表现得很淡然,他甚至奇怪我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他说有什么好接的?他从西安火车站下了火车,火车站广场一侧就有长途班车,他买了一张票就回来了,用车接,那可不是多此一举?
我已经被他感动得没有话说。我卸下他肩膀上的两个旅行包,把它们放在我自行车的后座上。我在前面推着车,他尾随着我的车子走。直到把他送到他家门口,我才卸下他的行李,挥手与他告别。
5
我与杨尚坤有很多年的往来,但我去他家,从来都是两手空空,没有拿过一针一线,没有拎过一盒烟半瓶酒。及至他退休后,我去看望他,才给他送了一壶菜油和几斤水果。不向官员行贿却不被官员冷落,别说现在,即使在那个年代,都堪称奇迹。
杨尚坤对我照顾有加,不存在任何个人目的,纯粹是他把我当成了一个可用的人才。求贤若渴,这样的成语用在他的身上,再合适不过了。杨尚坤有一套自己的识人用人的价值体系,不受社会风气与社会习俗的影响。他特别重视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对那些吃吃喝喝、拍马溜须、巧舌如簧之徒极度反感,以至于说起那些人,满脸的鄙夷之色。他对有思想的人特别尊重,哪怕思想者的思想与他的思考南辕北辙。我亲耳聆听了他和一位局长的对话。那个局长显然在告一位下属的状,说那位名叫某某某的人虽有能力,但太偏激,什么都看不惯,牢骚满腹。局长没有料到的是,他的一席之言却在杨尚坤这里遭遇了碰壁。杨尚坤神色凝重,他以严肃到近乎凌厉的口吻正告局长:什么叫偏激?有思想的人才偏激!没有思想,他只知道吃喝玩乐,你让他偏激他也偏激不了!杨尚坤自嘲自己就是个偏激之人,因为对现实中存在的种种丑恶看不惯,因此免不了常常牢骚满腹。杨尚坤质问局长为什么不能多看别人的优点呢?只要某某某没有人品上的严重缺陷,他发点牢骚又算什么错误呢?发牢骚不会导致山崩地裂,他想发就让他尽情地发吧!人憋闷了,总得有个发泄的渠道呀!杨尚坤叮咛局长要多聆听群众的牢骚,如此可以避免自己的工作失误。真相有时候就埋藏在牢骚之中,真理也经常以牢骚的狰狞面目出现。
很多人也许会产生疑问:杨尚坤生活简朴,显得很落伍,那么他会不会是一个因循守旧之人呢?我可以告诉有这样疑问的朋友:不,情况恰恰相反。杨尚坤不但极其开明,而且视野异常辽阔,学养也非常深厚,他的很多思考,都是世界性的,全局性的,根本性的,前瞻性的,甚至是惊世骇俗的。他和许许多多的官员同在一个院子里办公,但他与他们,却是两条轨道上行驶的车。他能一眼洞穿他们,但他们却未必能读懂他心灵的图谱。
杨尚坤不论到哪个部门讲话,都能激起海浪般的阵阵掌声。除了他的话语结实,句句都能抵达和撞击人们的心扉,更重要的是,他无论到什么行业,就能讲出那个行业的内行话。财政会议上他讲得头头是道,农业会议上他讲得头头是道,交通会议上他依然讲得头头是道。他讲话从不用秘书写稿子,都是自己拟一个提纲。
“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人们很容易把华威先生式的人物视为“万金油”。但我相信,凡听过杨尚坤讲话的人,没有谁会把他和“万金油”三个字往一起拉扯。因为他不但有着各个行业丰富而扎实的知识储备,而且对那个行业的特点与本质,常常有着个人化的深度思考与深度解析。他所讲之言,不是隔靴搔痒,而是如同挥动手术刀,要割开那个行业的肚皮,将那个行业的五脏六肺展示给众人看。
有时候他主动和我聊起了文学,我惊讶地发现,他仿佛就置身于文坛的围墙之内,对文坛的是是非非,对作家的长长短短,对作品的高高低低,了如指掌,如数家珍。有一回,他高声赞扬起了鲁迅,并声称当下的社会,太需要鲁迅这样敢于直面现实直面黑暗的勇士了。说着说着,他有点儿愤愤然,斥责现在的某些宣传机构不像话,它们在故意歪曲着鲁迅,在刻意玷污着鲁迅。
有一回,县上召开新闻工作会,邀请了好几家省城的媒体从业人员。在会上,杨尚坤讲了话。会议结束,我和那些记者同桌就餐。几位《陕西日报》的记者对杨尚坤赞不绝口,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问我杨尚坤从哪里毕业,学的什么专业,怎么会对新闻写作如此内行?比内行人还要内行,比从业了半辈子新闻职业的他们还要内行!他们笑称杨尚坤当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太屈才,而应该让他去做他们报社的老总。
杨尚坤没有什么业余爱好——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他在辛苦之余,惟一的乐趣就是读书。他的床上、椅子上、桌子上,到处都是书。书的门类也很庞杂,有最古老的诸子百家,也有最新流行的思想与经济理论等等,包罗万象,应有尽有。他读书有一个几十年岿然不动的习惯,那就是记笔记。所有他认可的论段,他欣赏的句子,他都不辞辛劳地予以摘抄。他的读书笔记,摞起来,有半人高。
6
有不少记者到了耀县,他们先找到我,尔后我把他们引领到了杨尚坤的家里。记者若需要和他单独攀谈,为了回避,我就暂时离开。很多时候,他都是躺在床上打着吊针,但却不耽误回答记者的提问。几乎所有与他接触的记者,都被他所感动。他们从他家里出来,感慨不已,赞声不绝。其中有好几个记者都对他做出了这样的评断:杨书记是一个很高尚的人!
但若有某位记者想写写他,那是绝对不行的。他用恳切之辞连连劝阻之外,还会为此而大发雷霆。他不容许搞个人崇拜,他看不惯各级领导利用媒体为自己歌功颂德。很有可能,他还会对记者进行一番教育,告知他们新闻的本质是什么,叮嘱他们少写官员,多写老百姓。
他的家与县广播站相邻。在某些地方,个别的媒体一定是那个级别领导的私家花园。媒体为同级别的领导抬轿子,抹脂粉,把黑乌鸦塑造成白天鹅,不但理直气壮,而且理所当然。杨尚坤成为耀县的一把手后,耀县尚没有报纸之类,惟一的媒体耀县广播站沿袭了那种“特色”之风,自然就把他的言行当作最为重要的内容,作为广播的头条新闻。如果是别的人当书记,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可杨尚坤却非但不领情,而且被这样的新闻所激怒。他亲自跑到广播站去,找到站长,冲着站长就是一顿训斥:广播里天天杨尚坤长杨尚坤短,杨尚坤是不是把魂丢了,委托你们给他叫魂呢?你们关注的就是县长县委书记,眼里还有没有老百姓?一番疾风暴雨过后,他变得和风细雨,然后语重心长地对站长说:要把目光投向基层,老百姓的疾苦才应该是新闻关注的重点,再不要为领导唱高调了。从此之后,杨尚坤的名字几乎在耀县的广播里销声匿迹。
他不让宣传自己,但却为一个农村妇女能上报纸而给报社亲自打电话。农村妇女名叫赵春,寺沟乡崔家坡人。赵春从小就学习刺绣,成家后远走他乡,在兵马佣博物馆门口安营扎寨,设了个出售刺绣的摊点。某一天几个北京的专家游览兵马俑,发现赵春的的刺绣不但气势磅礴,而且特别有个性,于是他们就向故宫博物院推荐了赵春的刺绣。故宫博物院经过审核,觉得赵春的刺绣有一定的艺术价值,便收藏了她几幅刺绣。
这件事情被杨尚坤知道后,他无比高兴。单在我面前,他都好几次谈到了赵春,既慨叹赵春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又说他要给赵春创造舞台,让赵春的能量得以最大程度地释放。他的心里,已经对赵春的去向进行了勾画:安排赵春去职业技术学校当老师,职业技术学校新开刺绣班,吸引农村妇女免费来上课。也就是说,要让一个赵春,变成成百上千个赵春。农村妇女有了致富的技艺,日子就会好过许多。
赵春要从一个农村妇女,变为一个吃商品粮的教师,杨尚坤也有自己的理解和说法:谁该吃商品粮?谁不该吃商品粮?多少庸庸碌碌的人啥也不干,却端着个铁饭碗养尊处优,为什么不能让有才华的人端铁饭碗?耀县的财政紧张是事实,但也不在乎多一个赵春或少一个赵春。
但杨尚坤想见到赵春,却并非那么容易。刘备“三顾茅庐”请动了诸葛亮,但杨尚坤往赵春家里跑了三趟,却连赵春的发梢也没见到。
崔家坡距离耀县城十三华里。那时候农村没有电话,无法联络,杨尚坤在下午下班后,不和任何人打招呼,他独自一个人步行去崔家坡找赵春。前两次,他都找到了赵春家,可惜赵春不在,于是他就给赵春的父母留了话,让赵春回来后尽快到县委找他。一月两月过去了,赵春始终不见在他的门口闪现,于是他决定第三次去找赵春。这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天下着雨,杨尚坤撑着一把雨伞,绕开乡村道路的泥泞,沿着一条铁路行走。脚下一打滑,他摔倒在地上。从地上爬起来,疼痛难忍,但他一瘸一拐,硬是咬着牙走进了赵春家。赵春依然不在。但这回,他不再停留于留话上,而是要留言。他趴在赵春家的柜子上,提笔给赵春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
赵春终于来县委找他了。赵春找杨尚坤的那天,天也在下雨。我坐在县委宣传部的办公室里,和几个人说着其他事情。在场的人中,就有宣传部部长。我们正在言谈之际,突然竹门帘被一只手挑开,出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个土里土气的村妇。那个村妇,不事装扮,皮肤粗糙,头上垂吊着两根粗粗的辫子,辫子上的白发一根根地翘起。她的衣着非常简陋,穿着一双老式的雨鞋,一个裤腿绾得高,一个裤腿绾得低。更为刺目的是,她竟然是个瘸子,走路一歪一歪的;咧嘴说话,亮出两排参差不齐的黄牙。村妇问杨书记在哪个房子办公?在场的人朝后摆摆手,以极不耐烦的口吻冲着村妇冷硬地说道:往里走!
村妇走后,从他们含有轻蔑的议论里,我才恍然知道刚才所见的村妇,就是成天挂在杨尚坤嘴里的大名鼎鼎的赵春。宣传部部长努着嘴,满脸不屑地说:你看她那个样子,要体态没体态,要体型没体型,邋邋遢遢,就这种货色,竟然成了大掌柜的心肝宝贝。
我因此知道,在县委这个院子,惟一珍惜赵春的人,只有杨尚坤。
后来也是在众人的议论声里,我知道杨尚坤为了让赵春上报纸,亲自操起电话向某个报社的总编打。只是人家把他的这个举动,当作笑料谈论。

杨尚坤与宜君老干部合影
7
杨尚坤离开耀县后,我对他的了解少了许多。我到市政协看望过他一回,他就坐在市政府办公大楼三层的某个办公室里。就是在这间办公室里,他却“受贿”了。
“受贿”的情节是他亲口对一位与自己关系密切的朋友讲的,并一再叮咛朋友不要外传。他的办公室,与一位副市长的办公室门对门。凡领导的办公室,都没有门牌。许多次,他听到了敲门声。门一拉开,就有人急火火地从门里闪了进来。来人的手里,拎着各种礼品,礼品以昂贵的高档烟酒为主。当来人看清楚站在他面前的人是杨尚坤时,一下子怔住了。杨尚坤从来人发愣的神态里,也明白送礼者敲错了门。送礼者都是市政府的机关人员,他们都认识市政协副主席杨尚坤,而杨尚坤或许觉得他们面熟,但未必能搞清楚他们究竟是谁。送礼者一时处于尴尬的境地,他们坐也不是,后退也不是,送进门的东西又不好意思带走,于是只有硬着头皮把礼品给杨尚坤放下。杨尚坤怎么肯收人家的东西呢?于是在一番拉扯甚至搏击之后,多数人将礼品又从他的门里拎了出去。但有两个人,扔下礼品落荒而逃,他追不上他们,又不清楚他们的单位,想退还礼品却不知道往哪儿退,只好让礼品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沉睡。
这样的难堪接二连三地发生,让杨尚坤颇伤脑筋。他苦思冥想之后,用毛笔在一页纸上写了五个字,然后将这页纸贴在自己办公室的门上。这五个字是:“我是杨尚坤。”自此以后,再也没有送礼者敲错门的情况发生。但就这五个字,却惹得对门的副市长很不高兴,认为他是在故意讥讽自己。
他从政协的岗位上退休后,我去看望过他几次。他的家,依然如故地简陋寒酸,没有任何改变。有一回,我坐在他家的旧沙发上,与他聊天,整整一个早上,他都被激愤笼罩,都被忧患吞噬。此时正是乱收费猖獗之时,他痛惜百姓的民不聊生,他痛斥官场的腐败糜烂,他担忧一个民族精神的堕落,他为一个社会的千疮百孔而陷入深深的痛苦当中。
六十三岁,杨尚坤便告辞了这个让他热爱也让他忧心的世界。他去世的消息我是在两个月之后才知道的。如果能及时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无论多忙,我都会去送他一程。我尽管遗憾自己没有参加他的葬礼,但他去世后的情景,却成为了耀县人久久的谈资,传送进了我的耳孔。很多很多的人听说他去世的消息后,都悲痛不已,放声大哭。那些在街头摆摊钉鞋的、摆摊卖菜的、开小餐馆的、开小书屋的、开三轮车的以及许多工人、农民、教师、干部等等,他们中的很多人或许与杨尚坤并不认识,也没有接受过杨尚坤的恩泽,但当听到杨尚坤去世的消息,都闻风而动,执意买一个花圈送去祭奠。于是,送给杨尚坤的花圈,从一公里长的巷子的两旁密密匝匝地蜿蜒而出,摆满了几公里长的街道。人们用这种方式,表达着对这位老书记的惋惜与哀思,也表达着对一种伟大人格的崇尚和敬仰,更在表达着对官场清明的诉求与呼唤。向杨尚坤致敬,其实是向中国的良心致敬。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杨尚坤在任时,严厉批评了很多干部,处理了很多干部,也让很多失去既得利益的人对他心怀不满。但就是这些人,在他去世之后,却都纷纷举着花圈拥向他的家,向他表达深切的怀念与哀悼。杨尚坤不仅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征服了自己的朋友,也征服了自己的敌人。这些被他得罪者的表现至少说明了一点: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埋藏着对正义对真诚的守护与渴望。
杨尚坤去世至今,我所见到的,只有两篇文章在缅怀和追思他:一篇为现任铜川市交通局局长蒲力民所写,一篇为他的弟弟杨尚青所写。蒲力民从骨子里尊崇杨尚坤,他的身上,呈现着杨尚坤的某些烙印,这是我和他交往二十年友谊依然牢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蒲力民的文章里,有一个细节让我铭记:杨尚坤一辈子没穿过西装,但遗像上的他,却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事情的起因是,他在担任市政协副主席期间,曾接到一个通知,让他做好准备,参加一个由省政协组织的考察团去日本访问。在妻子儿女的劝说下,他终于奢侈了一次,订做了一套西装。谁知,西服拎回家,另一个通知却摆上了他的桌案,告诉他去日本的考察活动取消了。于是那套西服只是被他穿着拍摄了一张用于办理护照的照片,就一直折叠着压在柜子里。那张本应用于护照的照片,成为了他的遗像。也就是说,他的脚,终生也未跨出过国门。
杨尚青的文章让我知道了杨尚坤的生活何以捉襟见肘的原因。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孝子,对父母亲的孝敬不遗余力。他的很多钱,都拿去给父母买了衣服食物,更交给了为父母医病的收费窗口。他有一颗博爱而慈善的心,除了对兄弟姐妹无私付出,还经常接济老家那些贫穷的亲戚、困顿的朋友和走投无路的邻居。他的工资,显然是入不敷出。
一个人走了,远远地走了。他把背影留给了我们,也留给了这个世界,而这个朴素的背影,却是那么地熠熠生辉。没有什么官位能比老百姓竖起的大拇指更高更大,也没有什么头衔比活成了一个真正的人更为光荣。
作者简介:安黎,著名作家,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原籍耀州,现供职于西安《美文》杂志社,其作品有长篇小说《痉挛》、《小人物》、《时间的面孔》,散文集《丑陋的牙齿》、《我是麻子村村民》等,获过多种奖项。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