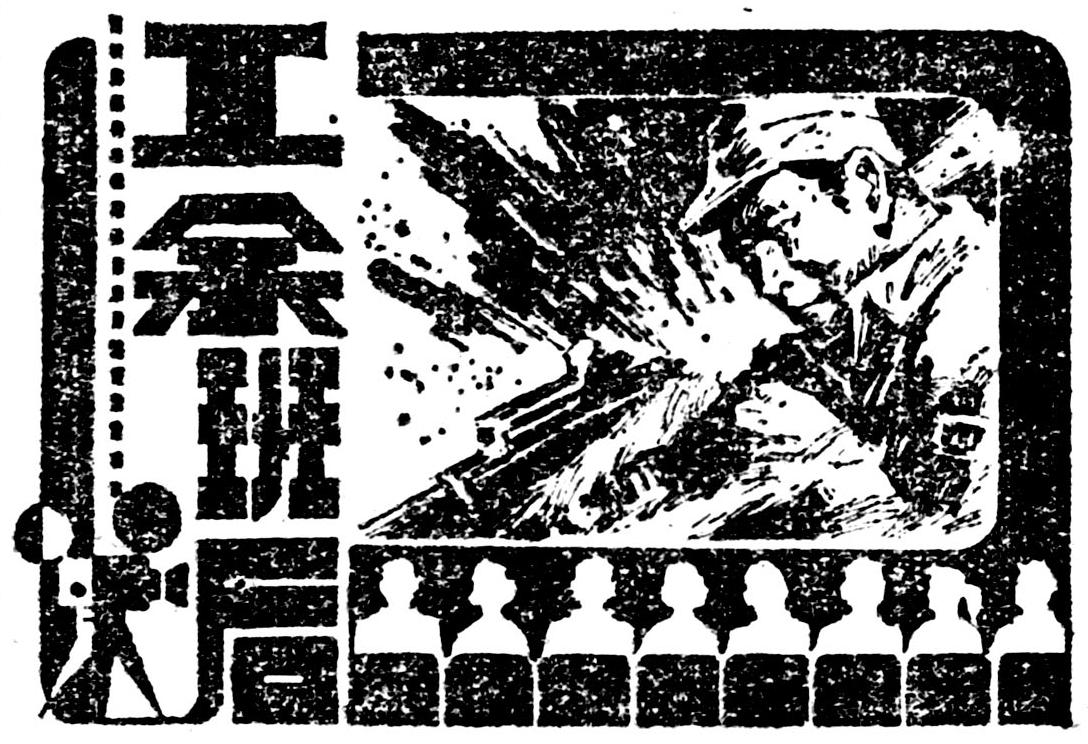苏晓康
第三章新泪与旧怨组成的秦香莲古幡京都“秦香莲”上访团
秦香莲当年手抱琵琶哭诉于开封相府的那一幕,如今又在北京正义路的一座大厦前重演了。
十几个女人被同一种命运驱赶到这里来。她们都已经不年轻了,而生活却偏偏就在女人的一切全都木已成舟的中年让她们触了礁,把她们翻进旋涡中。她们那早巳随着鱼尾纹和发胖的体态一道成熟、定型乃至固执起来的感情无论如何不能想象,那个在几十年里已经同自己血肉合躯的男人竟会发疯一样要撕裂出去。
“姐妹们,咱们不能眼瞅着让人象破烂一样甩了。古时候秦香莲都咽不下这口气,今儿个老娘能去咽?走,咱们联合起来告他们去!”
大伙儿这才觉得,这振臂一呼的人是她们真正的主心骨。她叫薛桂荣,一个服装厂的工人,快五十岁了,可那股子泼辣火爆的刚性儿,别说女流中少有,就是大小伙子撞上也得退让三分,而这恰恰是眼下这群没了主意的落难女子们所最缺乏的。
落到了今天这一步,她们也没弄明白丈夫为什么象中了邪魔似的非要跟另一个女人跑。光华染织厂的赵文秀只知道,丈夫嫌她不会生养,去唐山抱了个男孩来,可她偏不愿受这份窝囊气,倒要看看他老爷们儿自己怎么带小孩!谁曾想他居然找了另一个女人来帮忙,掉过头来还要离婚。赵文秀冲法院撂了这句话:你敢判离,我就撞死在这里!同丈夫两地生活了快二十年的胡玉蓝,一调进城就发现他在外面有姘头,她知道丈夫反正不会回心转意,干脆横下一条心;我拖上几十年不离,看他怎么办!演员出身的吴俊更是满肚子倒不尽的后悔药。她那个风流丈夫,年青时就拈花惹柳,出不尽的桃色事件,每回闹出龌龊来,都会跪着求她别离婚。那晓得二十多年把吴俊熬得人老珠黄了,他竟要跟着一个正在红紫的年青名角跑了。吴俊虽然压根儿不是能唱“秦香莲”的旦角,可她四处哭诉之状要比秦香莲还凄惨三分……。
薛桂荣一听吴俊的哭诉就火冒三丈。她可不是吴俊这号从耳根儿到心肠都软得象面团的女人。自打爹妈包办把她嫁给黑冠宇那俊俏小伙子,她就以为牢牢地把他攥在手心了。人都往半百上走了,冷不丁叫一个狐狸精给勾去了魂儿,这却是薛桂荣万万没有想到的。先把娘家人叫来将黑冠宇臭揍一顿,再撬开家门把一切值钱物件连同票证全部裹走,然后独自搬到厂里去当“秦香莲”了。如今,她的官司已经是“六进宫”了,虽然连孩子们都说爹妈俩没法再过了,可薛桂荣巍然不动,宁死不离。官司打久了,她也有了理论,说“要为妇女解放闯出一条路来!”
她这几年一直跟着姐妹们四处告状,那张状子递进中南海去,她还起了关健作用。可她渐渐觉得,事情好象并不象当初想象的那么简单。这几年法院倒是被她们告得轻易不敢判离了,可也没见哪个“陈世美”回心转意呀。这些家伙们都“王八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姐妹们当中好象也有那么几位,压根儿就没指望破镜重圆,准备把后半辈子全豁出去,耗他个一、二十年,把两个拖老拖死拉倒。一瞅这阵势,她真有些望而怯步了。
吕秀敏可是从一开始就不愿意把事情彻底闹掰。后来她听妇联说,她们找他谈了。那大老爷们儿哭得很痛。说自己一直是先进工作者,又是党员,五七年结婚那会儿,不懂什么叫感情,就知道厂里干活,回家也干活。后来,七九年碰上那个寡妇,觉得她比老婆待他好,象头一次见了女人似的,心里一热乎,犯了一回糊涂,这就让吕秀敏抓住,又扭送派出所,又告法院,把他往死里整。她这一闹腾,厂里行政党纪一块儿处分他,打那以后无论他怎么卖力气。先进也没他的份儿了,回到家里孩子们也瞧不起他,觉得做父亲的给他们丢了脸,人混到这一步还有什么劲呢?
她听了这些,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她有些委屈,觉得世上哪有男人在外面乱搞。做老婆的不去捉奸、不告法院、不整治整治他们的道理?七九年六月那天夜里如果她不跟踪了去当场把他俩捺住,当场扭送派出所,他俩能断了情吗?她一个堂堂正正的女人,让那些不正派的婊子把男人勾引了去,能躲在一边干受欺负吗?可她也有些后悔,当初要是肚量大些,火头上忍一忍,不把事情闹腾出去,兴许还不致于让他失了做人的脸面,绝了夫妻的情分,一头撞死南墙?
我在北京市妇联看到一本不算太厚的卷宗,里面就记载着这支“秦香莲”上访团的挡案材料。案卷首页写道:“上访团的形成,是从八〇年新婚姻法执行后,离婚率逐步上升,有些受害者经常在法院上访或候审,互相认识、互相诉苦、同清。为解决问题,团结起来,共同上访”云云。
我问出面接待的张玉梅同志:“她们后来的命运怎么样了呢?”
她长叹了一声,说:“还能怎么样呢?大部分人到了儿还不是都叫判离了。这事把我们腿都快跑断了。磨破嘴皮子,到了儿一对也没捏成。所以,这些人就是一个秦香莲的命啊,拆腾了一通也是白搭!”
旁边有个年轻女同志,别人管她叫小李,听到这里也扭过头来对我说:“说心里话,这些秦香莲虽然叫人同情,可她们确实也太弱,太可怜了,除了死拽住男方之外,没一点别的辙儿。今天都是什么时代了,女人要是还象几千年来一样由着男人摆布,不当秦香莲才有鬼呢!你自个儿挺起腰板来,谁怕谁呀?他不想过了就叫他滚蛋,离了谁地球还不照样转。要有这点骨气,也不受欺负了,也不当什么秦香莲了。中国什么时候没了秦香莲,那女人才叫人哩!”
我虽然不免还是替那些秦香莲们发愁,不过觉得这妇女的“娘家”里也终于有了不屑于与秦香莲为伍的人,真乃一大幸事。
(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