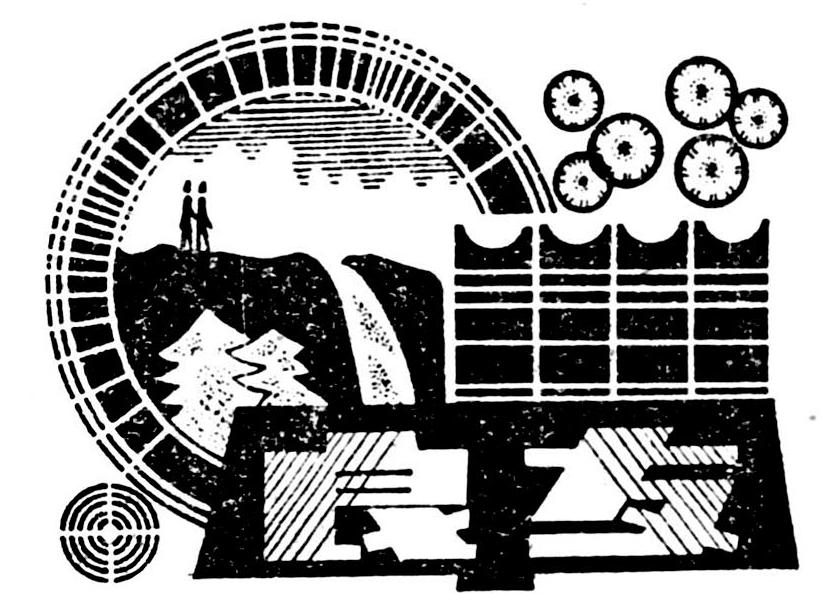彭仲劼
不久前从某家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东北某市领导视察一座烈士陵园时,发现东北剿匪时牺牲的战斗英雄杨子荣的墓及碑宏伟太过,显然超越了烈士生前一个小小排长的“规格”,因此决定为杨子荣迁葬,并减低墓碑的高度,以名副其实云云。
与此同时听到一位高干夫人的抱怨:高干本人为革命鞠躬尽瘁后,他的骨灰盒理所当然放进了领导干部骨灰堂,享受他应享受的“规格”。然而这一来却引起老夫人无限忧虑,因为她的身份是一般干部或家庭妇女,百年后只能进平头百姓的骨灰堂。老夫妇革命情谊甚笃,相依为命数十载,生而同志,一旦死而不能同穴,感情上实在难以通过。
我们的祖宗对“死”这一现实问题是极为看重的,因此制礼作乐者便绞了许多脑汁为之立下许多规格,如皇帝老儿死日“崩”、诸侯则日“薨”,乱用是要杀头的:再如五品以上的官儿坟前许立龟跌螭首的“碑”,高四尺以上,而五品以下则只许立“碣”,方跌圆首,高不可逾四尺。诸如此类,难以缕述。所以为杨子荣迁葬改碑是有经可据的,但老夫人的这段公案则翻遍三坟五典也寻不着祖宗遗训,因为古人封建,讲究夫贵妻荣,宫女当上皇后,一样筑地宫,卧皇陵;妓女从良,丈夫官至宰相,一样封为一品诰命,死后并肩享受龟跌螭首的高待遇。并且我国人民自古有个传统道德(不知道是美德还是败德)观念:人死为大。过去的法律,开棺见尸是要论罪的。即使对已死的敌人,除非苦大仇深,很少鞭尸三百。伍子胥这样做了,人们尚能理解。但今天我们的个别“四品州官”为了正“规格”,竟让一位人民爱戴的战斗英雄不得安眠就实在让人心里不是滋味了。何况炎黄子孙自古有崇祖的习俗,假如作此新“礼乐”者是郑三炮、蝴蝶迷的后代,自不足怪。然而怪就怪在他们正好是杨子荣等先烈的碧血浇沃的土地上培养出来的革命接班人,这就只好令人用过时的“数典忘祖”“忘本”之类词藻来解释了。遗憾的是建国之初未将烈士们追赠为师长、军长,以至遗下今日之患。不过笔者相信,杨子荣这样的“小排长”,雷锋这样的“小战士”,即使尸骨无存,他们在人民心目中却自有光辉夺目的丰碑,而热衷于为死人定“规格”的个别领导干部,“薨”后连自己的夫人都愤愤不满,更从何谈万民敬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