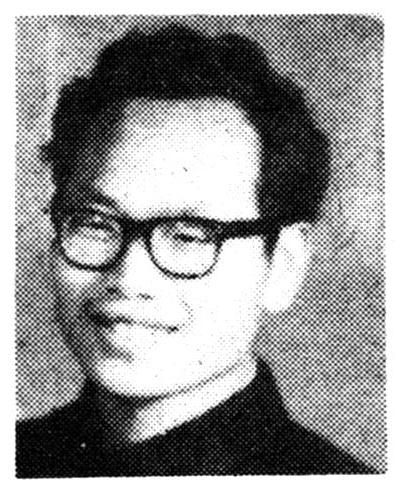陕西农垦中学 张斌礼
咱是长安人,生于秦,长于秦,口不改秦音,耳爱听秦腔。这喜爱秦腔的癖好,打从儿时由父老乡亲培养起来之后,便“没有秦腔,酒肉不香”。工余饭后,便收听秦腔,看戏的机会从不放过。求学在异地,常听几段戏以慰思乡之情;谋生在他乡,常哼几句秦腔以遣独处之愁。对秦腔,咱是忧时百听不厌,喜时不厌百听。就连谈恋爱那阵,也宁可失约,不误听戏。记得新婚之夜,为了喜中添乐,打开收录机,开足音量,“王朝马汉叫一声!”包相爷开口一句,但见新娘子闻声掩耳,在座的见状皱眉。妻子是北京人,喜流行歌曲,极不爱咱这秦腔,说秦腔和西凤酒一样,听了上头。此后常唇枪舌剑,口角不断。
“秦腔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传播面广,生命力强!”
“历史悠久不一定就好。‘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刺耳难听,古人早有定论。”她倒会引经据典。
“当年《三滴血》、《火焰驹》,风靡一时,而今《千古一帝》,进京获奖,这又作何解释?”
“大喊大叫,嗓子吼破,评委觉得精神可嘉,才给你们个奖。”哼!把人的牙都气成了骨头。
咱想,总不能娶了媳妇丢了秦腔,咋办?弄副耳机听吧,不到一周,就把耳机扔了。那样听法形同衣锦夜游,顿失往日的光彩和自豪。白天躲进厨房,晚上钻进被窝,如此听戏,与秦腔高亢粗犷,雄放洒脱,慷慨悲壮之风大不协调。干脆我行我素,想咋听就咋听。不料一位邻居找上门来:“你们陕西的秦腔很棒,听着满带劲的,只是我家小宝听到了害怕。”真叫人不可思议。后据别人讲,那小孩从小寄养在上海姥姥家,人们常想吓他:“再哭,让你听秦腔!”哭闹立止。咱就想不通,外省人来到这里,爱吃长安的“桂花球”,爱喝大荔的矿泉水,为啥就不爱秦腔?!我就不信“同化”不了你!先有意给他们听一些柔的戏文,再来一些刚的段子。功夫不负有心人,自从搬到新居后这五年下来,不再有人和咱唱对台戏。中午一点半、晚上七点陕西、西安两电台播放秦腔的时间一到,咱真是忙得不亦乐乎。尤为可喜的是我那年只四岁的小女儿不知何时也学得了一句“悔不该门前做针线……”。遗憾的是那位来自上海的邻居,没爱上秦腔,却迷了上眉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