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 陈德宝
文 陈德宝 程路
有人说他是“大侃爷”,有人说他是“玩文学”,更有人说他是新生代京味语言的开山祖,还有人说他集机智、幽默、哲理于一身。我去北京组稿,很想见见这几年玩得很火的王朔,寻遍了京城也没找见他,经哥们儿拐弯没角地介绍,总算找到了冯小刚,问他,他跟我一样地迷茫,不知道王朔又躲到哪儿去写字啦。
王朔曾在“走投无路”但又持有追求的时候,报考过《北京青年报》,他和冯小刚一样,都有过一个“编辑梦”。是的,在一家报纸或杂志社当个编辑、记者什么的,岂不是一件很有意思的差事。但两个人的梦都没有实现,因为他们身上的“故事味”太浓了,而新闻工作者必须是个稳健扎实、给人以信任感的人。从那个时候起,两个人就一直有“编辑部的故事”的野心。
冯小刚给我说了他们把《编辑部的故事》整出来的一些事。他说:那是1989年11月,那年的天气冷得早,我正在家里自个儿和自个儿过不去,烦得要命,电话铃响了……
是王朔打来的,冯小刚一拿起话筒就听出音来,可王朔还是变着声音唬他:“喂,你是冯小刚吗?我是公安局。”
“噢。”
“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
“知道,为了挽救我,让我争取主动,配合你们挖出躲在我背后的坏人王朔,纯洁人民队伍。”……
王朔和冯小刚在电话里神侃了一会儿,肆无忌惮地笑完,才说:“郑小龙约我们给你们艺术中心攒一道喜剧,是写一个编辑部的,本来想把这活儿掏给中央电视台,可郑小龙说他要了,他既是编辑,又是你们编辑部的头儿,他拍板组的稿不会瞎喽,所以,哥几个说这活儿给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练了。”
“都哪几个哥们儿?”
“苏雷、魏东升、朱晓平,你愿淌这混水儿吗?”
“愿意淌愿意淌……”
这便是《编辑部的故事》的序曲。
之后,这些人真的聚到了友谊宾馆,郑小龙说:这室内剧是个新品种,多机切换,现场录音,成熟了3天就出一集戏,投资小见效快,观众爱看,关键是要有好故事……他的话并不多,因为他知道聚在这儿的可都是些受之无愧的文坛大腕儿。
五天后,他们把朱晓平加工整理的一份故事梗概交给了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依依惜别地离开了住一晚上官价80块的宾馆,分别开练……一个个“快枪手”似的。
于是,李冬宝、戈玲、余德利这些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诞生了。
不久,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公开上演,当即轰动了全国。评论家蔡骧看后真诚地说:“我认为该剧是多年以来的一部高品位的作品。”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这次由北京华艺出版社副社长杜建业先生亲自挂帅,编辑部主任金丽红女士带队,由西安天地书院和女友杂志社《文友》编辑部等几家单位联合组织协办的“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新书大系”签名售书活动在西安举行,推出了以王蒙、李国文、刘心武,也包括王朔在内15位作家的新书佳作。
签名售书活动安排在5月16日、17日在陕西省体育馆内举行。
王朔、刘心武等几位作家,在华艺出版社编辑部主任金丽红女士陪同下,一行7人乘火车于14日早上9点24分到达西安。王朔单肩挎着一个深蓝色的、装得不太饱满的旅行包,走下列车的时候,他那1、78米的个头儿,显得很高大。有些文气的小白脸,小平头,黑茄克衫,灰筒裤下套了一双薄底黑布鞋一一朴素得跟我一样,整个儿一个俗人。
陪着作家们参观了著名的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一听都是些著名作家,还有那个写《编辑部的故事》的王朔要来,便早早地在贵宾厅候着,并给作家们赠送了一袋博物馆小资料,最后还安排了一位漂亮的小姐讲解。从讲解员小姐那里,王朔认识了那件青铜饕餮珍品上,“饕餮”两个字的准确读音。作家们在惊叹不已中感受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博大,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
晚上,我做东请作家们到西安著名的桥梓口夜市去吃哈木家的、风味独特的“烤羊肉串”,还叫了醪糟、粉蒸肉,牛羊肉泡馍、还有啤酒。王朔唯独钟情的是那碗“牛羊肉泡馍”,他吃得很过瘾,嘴里直叫着“好吃!”
16日上午10时,王朔和刘心武、梁晓声、李国文、从维熙、叶楠、莫言、张抗抗8位著名作家,在仪仗队的鼓乐声中,走出了汽车,王朔在读者的“围追堵截”和簇拥下,不紧不慢地走进了售书大厅,照像机、摄像机一齐向他射来,闪着耀眼炫目的光。他稳稳地落坐在读者面前。那些从清早就来了,等了几个小时的读者,或许是因为对他的崇拜而显得特激动,问起话来多半是傻乎乎地、语无伦次。那本定价4、90元,书名《过把瘾就死》的书,似水流一样涌过来,他和善地、微笑地和热爱他的读者轻松地调侃着,然后把字体很不规范的“王朔”两个字歪歪斜斜地签在他的“玉照”下面,然后写上日子。但签完了名的还没有满足,还要仔细地再睹他的风采,久久不愿离去,致使签名的队伍排得好长,使几名治安员汗涔涔地跑前窜后。我看着他回答着读者漫无边际的问话,漫不经心地又在书的扉页上写上:“你不是一个俗人!”、“都不容易”、“都是苦孩子”、“爱喜欢不喜欢”、“一点正经没有”、“爱谁谁谁谁”、“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有钱多好”、“晕菜!”、“只要我过得比你好”之类的没边没沿的话直想乐。一位读者一次买了两本《过把瘾就死》,要他签上姓名,他笑呵呵地说:“你可救济我了!”然后,随手写上了“你真疼我”的话把书递给读者,读者问他写作的目的,他便毫不犹豫地写上了一句:“沽名钓誉”;夸他几句,他又是一句:“没什么炫耀的”,“都是抄的”、“我什么都不是”之类的妙答。把那几位围了他一天的“王朔迷”崇拜得“五体投地”、“一塌糊涂”的时候,我便觉得,王朔就是王朔,一点正经没有!
晚上,在客房里,王朔签了一天的名,疲惫得澡都不想去洗,只是一根接一根抽着烟,我们边看电视边侃。无意中便侃到了写小说。王朔没有染上名角儿的傲气,显得很随和,说他算不上一个作家,顶多只能算个写字的。说他经历特苦特坎坷,出生不久赶趟似地逢上了自然灾害,刚上学又遇上了文化大革命,高中毕业去青岛服役,在北海舰队稀里糊涂地干的是卫生员的差事。复员后待分配那阵子,寂寞得不行便去倒腾收录机,差点没把自个儿赔进去。后来分配到医药公司,不知咋的显得特无能。他说:他是走投无路了才去写小说的。没想——一写字,不小心就写红了。之后,干脆辞了工作,待业当“坐”家,真正地玩起小说来。他毫不隐瞒地说:这方面我命好,不象别人草稿、退稿笺压了大半箱子。
这几年王朔的确红得发紫,光稿费就挣了十几万。可这让人眼红的收入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人们不得不承认,王朔的确是一个感觉、悟性很好、笔头很快的青年作家。他写作一般是构思好了以后,从头到尾一气呵成,顶多是改几处笔误,从来不写二稿。可为了写小说,有时他常常会突然间消失一段时间,连他最“铁”的哥们儿都不知道他的行踪,他整个儿把自个儿“封”起来,一天一万字地写,当他再出来“面世”的时候,瘦了一圈的身后一定会带着一部新作。当读者又为之赞不绝口的时候,王朔仍然会用他的那轻松的,带着调侃的京腔说:“我把手都写残了,人整个儿一个虚脱……”
所以,与其说王朔是在“玩”文学,不如说王朔是在玩命。近几年,他的7个中篇、两个长篇、6部作品被搬上银幕,参与了我国第一部室内电视剧《渴望》的创作,是轻喜剧《编辑部的故事》前10集的编剧。仅1988年,王朔就有4部小说拍成电影,这在中国电影史,乃至世界电影史上都是不多见的。《顽主》作为我国的优秀电影出国参赛,并获得金鸡奖九项提名。而北影也一年一气儿拍王朔的四部片子《轮回》、《大喘气》、《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和《顽主》。尽管评论界对王朔褒贬不一,有人骂他是“痞子文学”的祖宗,然而,读者和观众接纳了王朔,这是事实。
当华艺出版社准备推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新书大系”时,曾向王蒙、从维熙、李国文、刘心武等著名文学家征询意见,文学家们都一致认为,王朔的小说是文学,做为“新北京族”的代表应该收入。
今年6月,华艺出版社还将推出可以让爱好王朔作品的读者一次看个够的“王朔系列小说全集”。它将以“纯情卷”、“娇情卷”、“挚情卷”、“谐谑卷”命名,共四卷,约160万字。
王朔越玩越火的现实,使王朔觉得自个儿不必急着去混个大专文凭什么的。王朔又点燃了一根烟,继续侃着他自个儿。他说:我最早写小说是写通俗的,是那种能让普通百姓看出乐来的那种言情的,模式就是把美好的希望塑起来,然后,再残酷彻底地砸碎,是所谓有价值的美被彻底的破灭。悲剧色彩较重。
后来语言有了些变化,把写小说当作和自个儿最知心的哥们神侃,虽然写的大都是些入不了“流”的小人物,痞子味十足,但我认为小说不是某个具体的人物或某件事物,我要表现的是一种人生态度,写这个生存环境的及这个环境中活生生的人,离我们的生活特别地近,就好像是我们身边,昨天或今天发生在大街小巷或某个角落的事。我讨厌道貌岸然的虚伪,我寻找真实,我写字时第一个首先要感觉到的是我自个儿是真正的正常人,然后才是个“写字的”。
他接着又说:我承认这几年我特“兴”,还能写,说不定过几年,我就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但我或许会去上大学,或者去干点别的什么事……
前阵子,王朔赶写完了一部40集的言情戏《女演员》、《爱你没商量》也已由北京音像出版社改编为电视剧。这次更是宋丹丹、英达、谢园等名星荟萃,用王朔自个儿的话评价是“倍儿红!”
当别人问起他,为什么突然改走言情的路子呢?王朔自有打算地说:“这是证明我王朔绝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在此之前,我玩过侦探小说《单立人探案集》,那曲折的案中案也并非只有柯南道尔会写。我要玩起言情来也绝不在别人之下,我想今后当人们再提起中国的言情小说时,再不会想到琼瑶,只会想到我王朔。”
今年年仅34岁的王朔,平日里除了写作,和哥们儿聚会神侃,还经常看一些自个儿感兴趣的各类书籍,来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他也读一些当代青年作家苏童、刘恒、刘震云的小说,这些小说里常常会有一些令王朔也叫绝的精采描写,他常常发出这样的感叹:“这家伙,怎么和我想的不一样!”
王朔是个很恋家的主儿,他很珍惜他那收拾得跟宫殿一般的家,旁人只知道他漂亮的妻子沈佳是北京东方歌舞团的演员,4岁的女儿王佳是王朔的心肝宝贝,平常由王朔父母带着,小丫头可是绝顶的聪明可爱,受王朔的语言“污染”最为严重,也是个爱侃的“小京油子”,侃起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绝不亚于被称为“大侃爷”的他爸爸。而王朔只要把女儿接回家,他绝不会再去碰那支给他带来了名气、财富的笔。他唯一的乐事就是与女儿游乐玩耍,女儿喜欢撕书,撕到兴头上,连王朔的书也会被撕得“六月天里漫天飞雪”,王朔也不制止,嘴上说:“撕得好!”心里却在想,“女儿啊,你可知道,你老爸可就是靠这吃饭的呀!”
这天早上李政醒来的特别早,便硬拉我到王朔房间去侃,可到房间一看没人,老作家叶楠也早早地下楼锻炼身体去了。金丽红找见我们,才知道王朔受伤了。原来,从来没有早晨洗澡习惯的王朔,今早却非要到浴池里去泡泡,或许是昨天签名售书太累了或许是昨晚侃的太晚了,反正他没留神,脚底下打滑摔倒了。眉角也挂了彩,下颌毫不留情地“亲”在盥洗池的边沿上,顿时张开一个红艳艳的小红嘴,吐吐吐地往外涌血,血染红了那条方毛巾
我和李政窜下楼,穿过人迹稀少的马路,跑进对面那家职工医院,在光线幽暗的走廊里找到了王朔,干过卫生员的王朔把那口子根本没当回事,没事人似地捂着伤口坐在走廊长长的条椅上,寂寞地等着上早班的大夫。
大夫是一位曾经看了《编辑部的故事》乐出泪花花,正在使着性子让男朋友去买《青春无悔》高价票的,把口红抹得跟他的伤口一样红艳的小姐,她麻木地用笔杆顶起了他的下颌,看了看伤口,开始用她的玉手写病历,写处方的时候,才想起还没问病人的名字,我在一旁骄傲地用纯正的乡音报告“王朔”这两个字,可她的玉手写出来的却是“王烁”。我们相对无奈地笑了笑,拿了处方,交了费,小姐不带一丝笑容地操家伙给你缝了3针。
你裹着白纱布走出医院的样子,挺滑稽,我真觉得你——也整个儿是一个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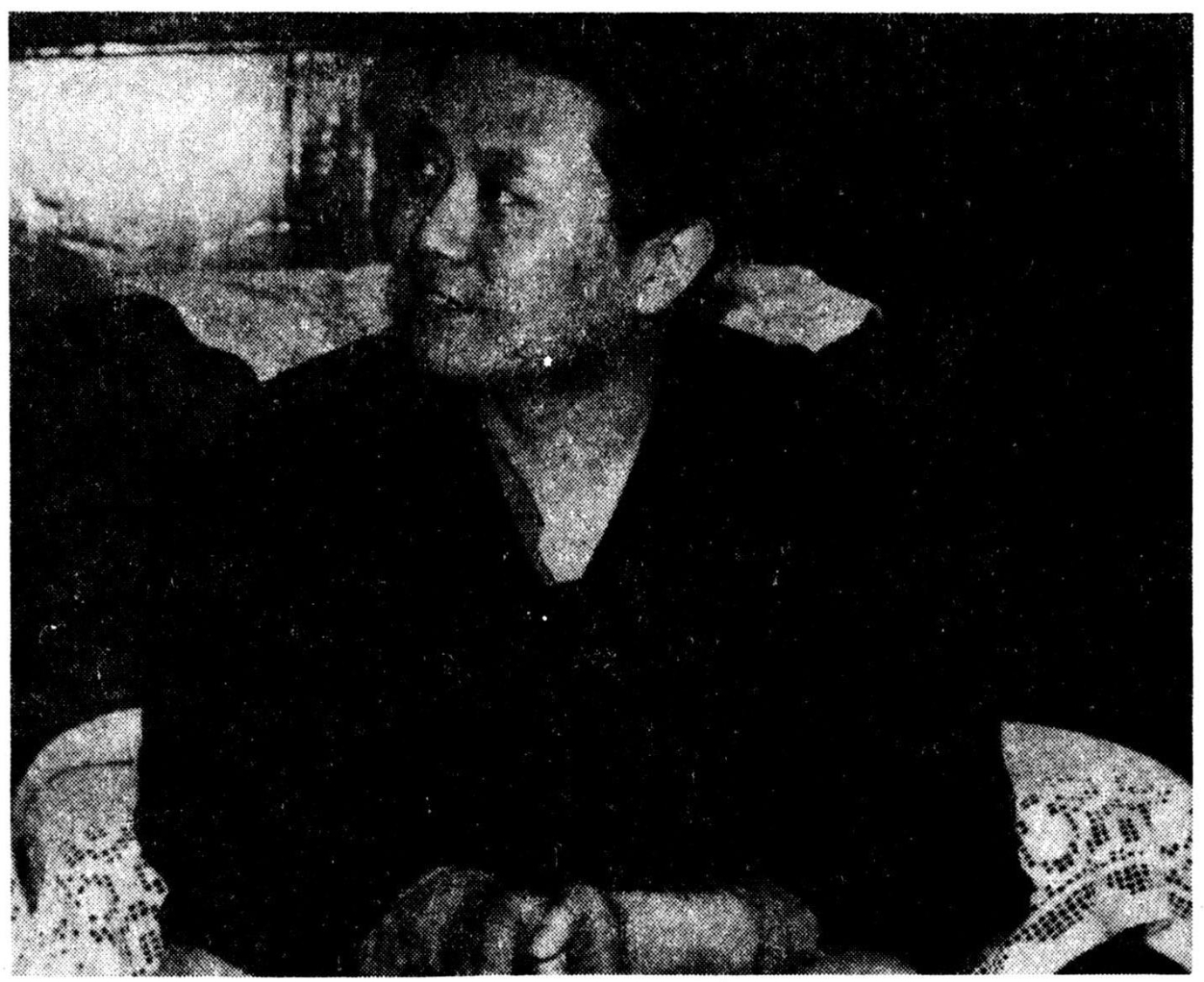
王朔接受记者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