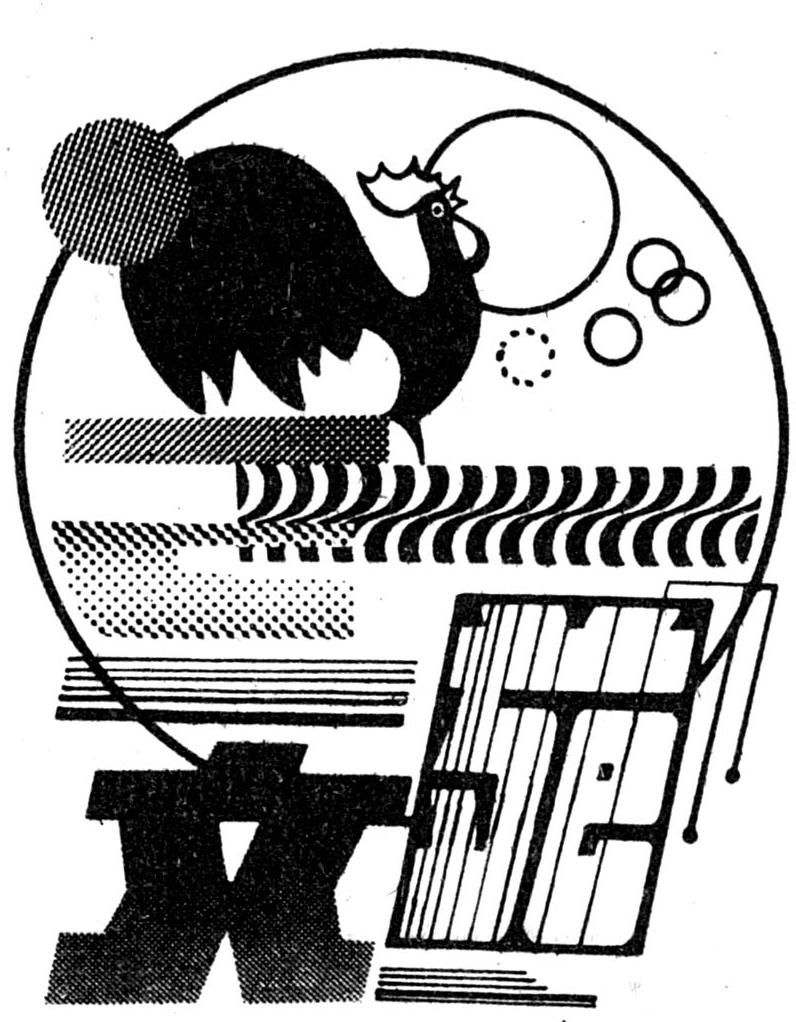彤彤
·1·
离开西安的时候,朋友说,还记得那个开元进士王昌龄作的诗吗?我说,不记得了。朋友又说。那你还记得唐时那个被演义了的将军薛仁贵吗?我说记得。不过历史上是真有薛仁贵的,怎么能说是被演义了的将军呢?朋友只是笑笑:“去了青海后可别忘了到大非川。到了你就知道了。”
·2·
向好多人打听,翻好多旅游图册,可是怎么也听不到看不见大非川三个字。青海有没有大非川呢?也许是朋友在和我开个严肃的玩笑吧。
湟水河畔。
寸草不生的土褐色山峦静默地听着若断若续有如老妇人最后喘息般的河水声。我就站立在河岸上秃山下,望着河望着山。而山垭上半轮血浸的落日也凝重地注视着我。我的目光飘移开河面,沿了嶙峋的山坡向上缓缓移动过去与那半轮和我相视的落日相会。陡然,我的眼帘剧烈地跳动了,旋即就终极性的合上——我坠入了一片血晕。
在无声无息静穆悄然的血晕中,我看到也听到了王昌龄的那首千古绝唱。
烽火城西百尺楼,
黄昏独坐海风秋。
更吹羌笛关山月,
无那金闺万里愁。
一千二百年了,那位飘逸疏狂又郁郁不得志的汜水尉王昌龄竟随着他的诗跨越渺渺时空与我在湟水畔这块尘封的土地上猝然相遇。
一袭长衫腰悬利剑独立戍楼的王昌龄与我久久相望,任朔风猎猎吹刮着我们之间那道思乡忘亲的目光。这目光从唐开始如波光耀耀穿越千年直到今天。
·3·
落日西沉,冷月悬天的时候我告别湟水,绕过青海湖……当又一个落日在西天出现时,褐色的山便在极远处迤逦成了一道道黑色的浪,狂劲地拍打着苍茫的天宇;没了脚踝的枯草傲立着,凝视向高远的穹隆;残雪片片,在无际的草原上分散成一个个圣洁而孤寂的故事。
这片冬季的草原就是朋友告诉我的大非川。
群山,枯草,残雪都若公元六七〇年冬季的那个傍晚一样一下子凝固住了。各自保持着那个傍晚最后一瞬间的姿态。这里的一切都个性地生存了千余年。
在等我的到来?还是……
·4·
大唐高宗成亨元年(公元六七〇年)冬季的一个傍晚,就是在这里,十万大唐兵士的血流尽了。十万鲜活的生命就永远沉寂在了这里。浑身被血裹浸的吐蕃将士们此刻看着遍野的尸体,又把目光投注向远山——经幡在山的托衬下飘舞挥洒着一曲哀歌。
吐蕃将士们陶醉在哀歌声中。
猛烈,不知从何方如电掣雷击般的一匹白马在草原上飞驰。一个人,一个丢盔落甲的将军兀地从一堆尸体中腾跃而起,飞上马背。白马驼着将军瞬间闪电般消失在东方的夜幕中。
冷月悬天。
吐蕃的兵马刹时散尽。
凄冷的月光,黑红的血、锃亮的刀枪,飘舞的经幡便恒定在了大非川。
十万兵士的生命永远在大非川寂寞着了。
无数个白昼,无数个黑夜,凭吊者只有风,只有天空上若豆的鹰。而人,却不曾再来。
吐蕃的,大唐的都一样。
·5·
那从尸体堆里奋然一跃的将军便是薛仁贵。
咸亨二年春(公元六七一年),薛仁贵单人匹马回到了长安。
·6·
织机旁油灯下,兵士们的妻儿,老母无数次地透过紫门。望着通往西方的驿道。终于,她们看到了薛仁贵从驿道上疾驰而来,掀起的却是一道孤独的尘烟。并没有遮天蔽日。
妇人们丢下了手中的活计,只留两道目光在复又清冷的驿道上停驻。她们什么也不说(能再说些什么呢?),把已将尽的几点泪珠滴在织机上,滴在还未绣完的锦帕上。
·7·
文人们得到将军战败的消息。嗟然一声长叹——走出了书房,用握惯了笔的手握一握饰玉雕金的剑柄,然后无奈地又折回书房,研好墨,拿起笔如将军执剑挥戈般写一首诗。完了就掷笔,就对月长啸……
文人们大多都是失意者。
妇人们流干了最后一滴泪,收拾起那块没绣完的锦帕,不动声色步履迟缓地走出茅屋倚在已经将朽的柴门旁,看一眼长安望一眼通往西方的驿道。长安可以去,可以去看看败将薛仁贵,甚至可以大声地在心中质问他。可是儿子、丈夫们往战的地方却在遥远的西方被重山被恶水阻隔着。又看看长安又看看西方,罢了,那里也不用去了。从日出站到日落又从日落站到日出,心中便编排着一个人,让这个人带着她们去跨越险山恶水,去寻找儿子、丈夫们。这人绝不能再是个男人,男人太让她们不放心。就这样,樊梨花便开始了千年的征西,在舞台上,在每个妇人的心中。
·8·
起风了,群山依旧迤逦,枯草依旧傲立,残雪却随了风凄迷着草原。在风中,我把目光抛问远山,隐约间,我看到半山腰上经幡依然在重复着不变的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