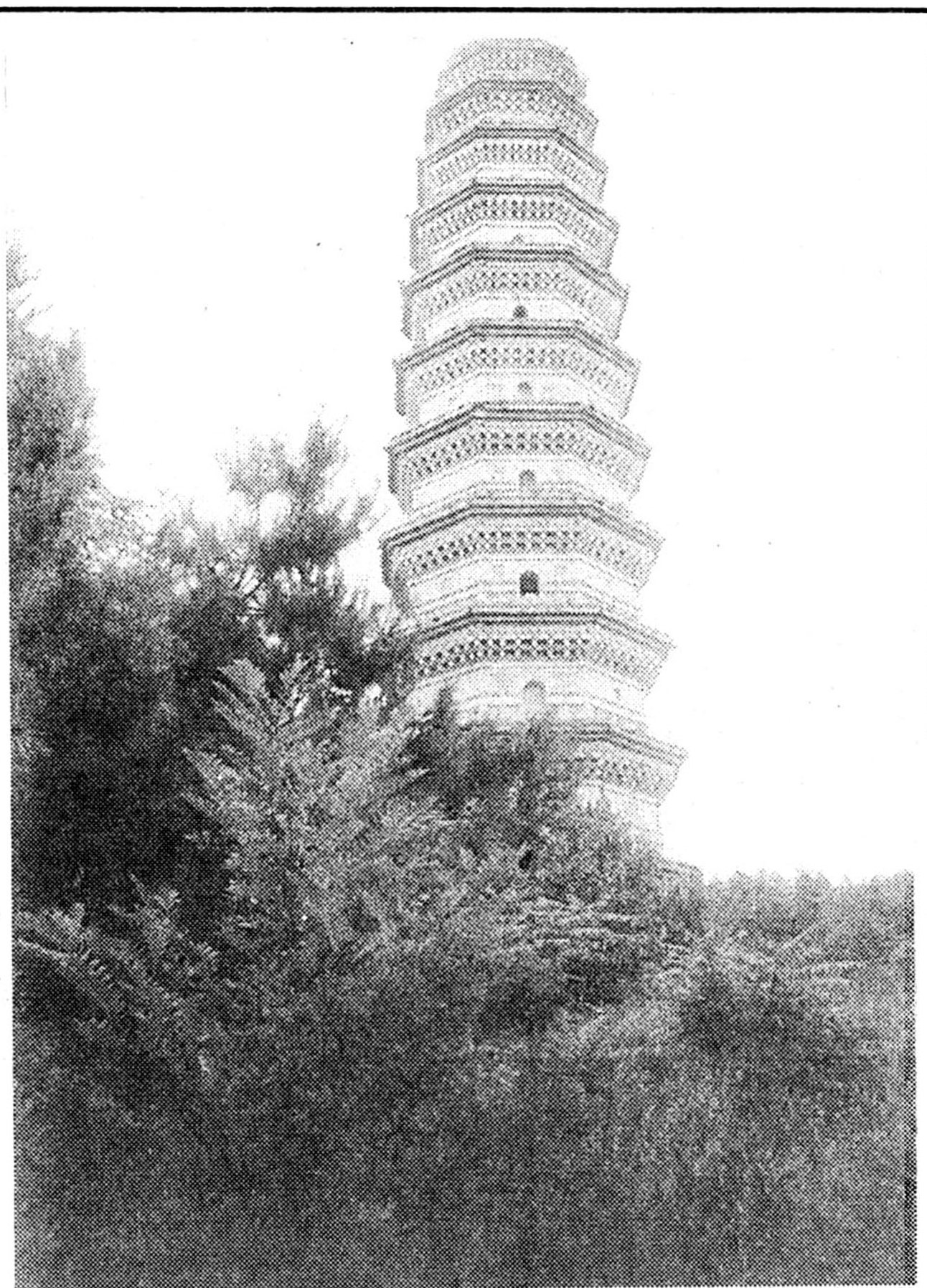薛海春
我家住川口,黄河一渡口。从古代大禹治水到而今的现代化治黄工程,无不凝聚着纤夫们祖祖辈辈的希望,子子孙孙的感慨。就是现在,这个古渡,仍然是军事、交通、生活、运输的一个重要口岸。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主席率部也从这里东渡。
人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村的人世世代代生活在黄河岸边,“只靠吃水”因而男人都作纤夫,都走“西口”。即沿黄河上下拉纤,经商,或是长途贩运。
我从小生长在黄河岸边,深知纤夫的艰难。我的爷爷就是在数九寒天,为了使全家人度过年关,冒着生命的危险,在黄河上拉纤摆渡,因船困河涂,赤身下水背船,腿部筋骨被几尺厚的冰凌刺断,保住了性命,落了个终生残疾。我的父亲又是在黄河上拉纤,一次在碛口上游七八丈高的悬崖上拉纤,因上游涨水,浪高风紧,逆水行舟,人力所不及,七八个纤夫套着纤绳从悬崖上摔下,随着货船下流,把人拉入水底,我的父亲凭着高超的水性,清醒的头脑,脱掉套在身上的纤绳,浮上水面,被人救下,其余纤夫连同货船全部遇难。从此,父亲发誓改行,给小镇上的“老板”当了店员。到了我们这一代,应该说改一改历史,我十九岁那年,正值困难时期,村里人普遍没有粮吃,听说黄河上游的河曲、保德一带粮食便宜,便三三两两不约而同去贩粮,父亲通过熟人高息借到一笔款子,我与门中两个有经验的哥哥海清和海喜结伴出门,走了“西口”,去时每人担了五六十斤土布,到了保德地面,粮食确也便宜,三人卖掉了土布,买了一只木船,装了一船小米。三个人做了明确的分工,海喜年长,经验丰富,熟悉航线,负责掌舵,统一指挥;海清头脑灵活,负责买办;我高中文化,负责帐务。对我来说,平生第一次出门,而且走的是“西口”,开始时年轻气盛,听着纤夫们演绎出许多动人的故事,觉得很是潇洒,很是开心。可当木船行至离家还有一百多里路的时候,面前出现了黄河上著名的佳芦浪峰,宽阔的河面上山一样的暗礁不规则地排开,形成一个一个汹涌的浪涛,浪涛一个跟着一个,雪崩似地重叠起来,卷起巨大的浪峰,掀到半天空,发出雷鸣般的吼声,然后象瀑布一样崩泻下来,横挡在奔腾咆哮的黄河急流之中,使本来雄伟怒号的黄河更加怒不可及,几十丈高的浊浪腾云起雾,凌空翻腾。这其中只有丈余宽的一个口子可以航行,在这个口子通过的船只成千上万,毁掉的船只也不计其数。我们的木船行驶到佳芦浪峰的上游,停在一个较缓的口岸,爬上附近一个高高的山坡,有经验的两位哥哥看好了航线,三个人便上了船,脱掉了衣服,包好自己口袋里的钱财,真象赌徒最后的一搏,开始放船,我只死死抱着木船上那只棹扇,全靠两位哥哥密切的配合,木船接近那个口子时,一下跌入浪峰谷底,满天的黄泥水雾,溅得人浑身透湿,还没有回过神来,又一下跃上浪峰峰顶,真如银河冲破天际倾倒下来。突然,两位哥哥大喊一声,木船如离弦的箭,飞出佳芦浪峰的豁口,这时的我早已魂飞天外,冷汗和泥水交织在一起,溅满了全身,呆滞地站在船上。海清哥哥初通文墨,随口念出两句诗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时我才回过神来,好像凝固的生命又一次获得了新生。现在想起,当年的惊险情景决不次于今日柯受良先生的壶口飞越,后来,听说当地政府组织水文站的同志把佳芦浪峰的暗礁炸掉,船毁人亡的事件也就很少发生。
离别三十年,弹指一挥间。这次回家,看到黄河的水势有变,涛声依旧,昔日赤身裸体的纤夫生活彻底结束。沿河两岸停泊的多是机船,少量的木船上也安装了马达,年轻的纤夫西装革履,时髦夹克,英俊潇洒,船上放着悠扬的歌曲,成了人们旅游观光的去处。这不正是黄河纤夫象先辈一样濡山岳之精灵,沫河川之气韵,怀着希望,怀着理想在艰险崎岖的坎坷中踏出的路吗,这不正是黄河纤夫象先辈一样,祖祖辈辈,世世代代,英勇顽强,流血牺牲,治黄治水踏出的路吗,我将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