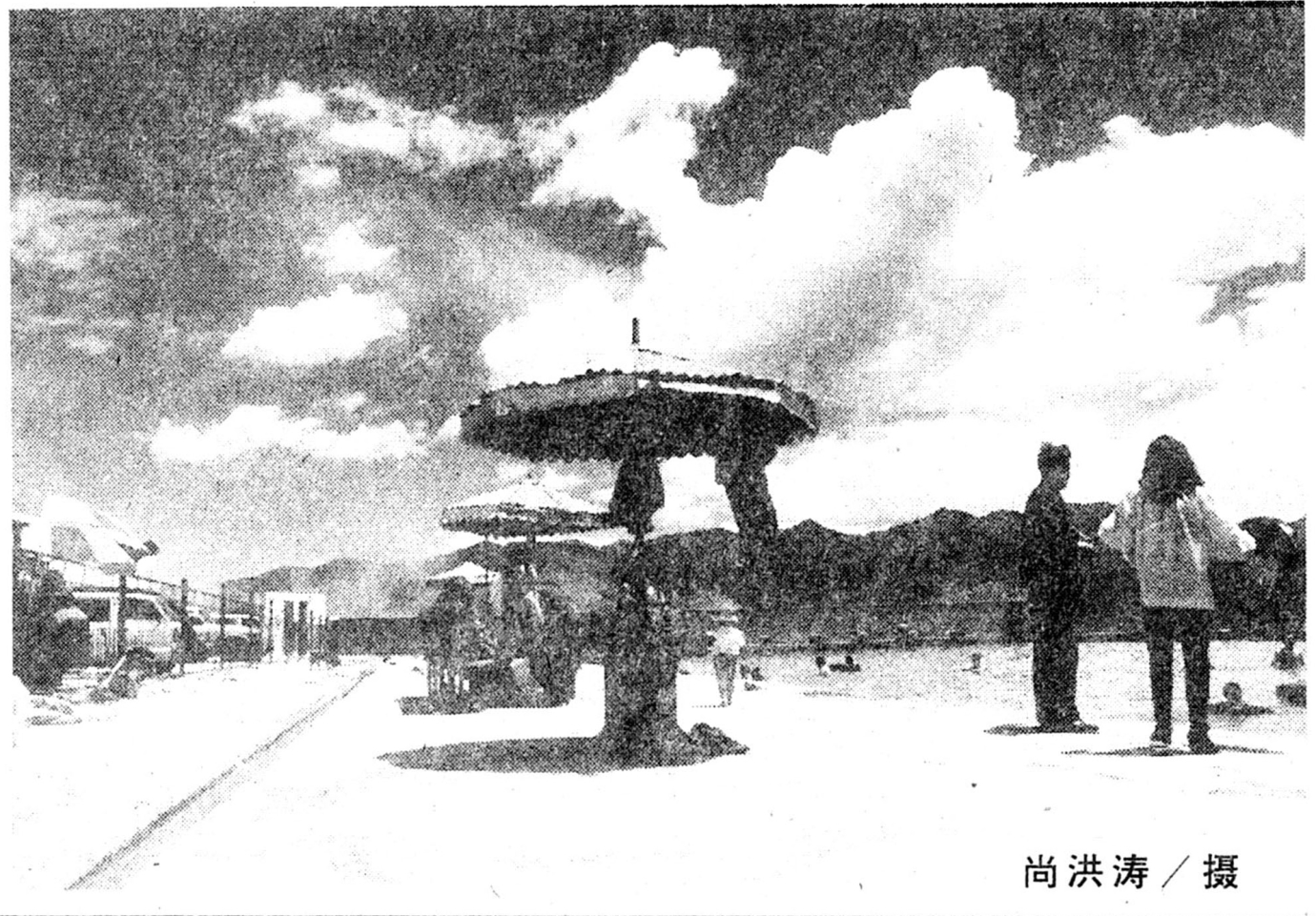文/李文少
傍晚,起风了,阵阵凉意袭来。散步是去不成了。于是,淡茶一杯,坐于窗前,风卷着残叶刮来,敲得玻璃波波作响。那随风而去的残叶飘飘忽忽,忽高忽下,忽而荡荡悠悠,忽而盘旋升腾。心绪也随着那无根残叶攀升,飞向风雨故园——我那座落在关中平原的老屋。
老屋当是更苍老和干瘪了。前年回去,那土坯墙已然墙皮剥落,参差地露出些许麦秸来。门前的六棵梧桐只剩一棵了,抚着粗糙的树干,寻找儿时刻在上面的戏语。树间的小间方曾是一块繁茂的菜地,盈盈绿色承载着儿时许多憧憬和欢乐。如今只有这一棵老梧桐默默伫立。经历风雨,梧桐若有知,他会说些什么!
“吱呀”一声,推开两扇黑漆的大门,走进尘封已久的儿时岁月。土筑的地面泛着幽冷的青色。阳光从房顶的细缝中射进来,形成光线,在地上落成斑驳的亮点。周遭一片寂静,能静听自己的呼吸。细微的灰尘在光线上盘旋。当年,全家就是由这里走向城市。由于对新生活的恐慌,母亲带上了能带的所有东西。乡邻问几时回来,母亲说三、五年吧。而十多年后的今天,母亲仍寓居于汉江边的小城。
那宽大的土炕曾是儿时的全部记忆。现在,土炕上已落了厚厚一层灰尘,墙上的主席像也尘封得形象模糊。在这土炕上,我曾伊伊呀呀地学语,也曾有模有样地吼秦腔。冬日里,我钻在被窝里高声朗诵人、口、手,母亲借着晕黄的灯光翻寻我衣缝上的虱子,把它们哔哔剥剥地辗死;夏日里,我躺在凉席上望着天空的星星,母亲默默地纳着鞋底。麻绳呼呼地响,夹着微风掠过脸庞,无限地惬意。那窑窝上的煤油灯依然立在那里。想起那如豆的灯焰,可惜,那瓶中已然没了煤油。
推开灶堂边的后门便是宽宽的后院。这里曾是母亲的银行,鸡猪曾经喧闹不堪。那个夏夜,儿时的我半夜小解。风中婆娑的树影在我看来愈来愈象袭来的怪兽,于是提着裤子大叫着冲回屋去。如今抬头望去,树影依旧婆娑,只是树干粗了许多。
回头看见屋檐下堆放的纺车和织布机。见到这入驻心底已久的物什,我不由得伸出手,要拂去那厚重的尘灰。童年的梦总是伴着母亲纺车的嗡嗡和织布机的咔嗒。现在,兄弟姊妹结婚仍有母亲手织的粗布床单铺在席梦思上。
如今的我已然学会了陕南的软声侬语,也会讲一口京腔。但秦声秦韵却是临世后听到的第一声而溶入血液。它在身体内左冲右突,时时有突围的危险。有时痴想,或许梦中的痴言呓语便是一腔的秦声。当汽车一出丰峪口,空气中的秦腔迎面扑来,我的心不由一颤。
我自信于自己的乡音,想自由地倘徉。话一出口,不由一怔。不,这不是我记忆中的乡音。我不敢再开口,这声音阵阵刺痛耳膜。我与乡邻操着同样的言误,却又那般地格格不入。这相同的言语如此隔膜,难道这声音不再属于我,或是我已不再属于这个声音!我不敢想,掩面逃去。奔逃中,我感到身后的老屋深切地注视着我的脊梁。
那老屋在我脊梁上栓了一根线,将我象风筝一般放出去,无论何时何地她都牵挂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