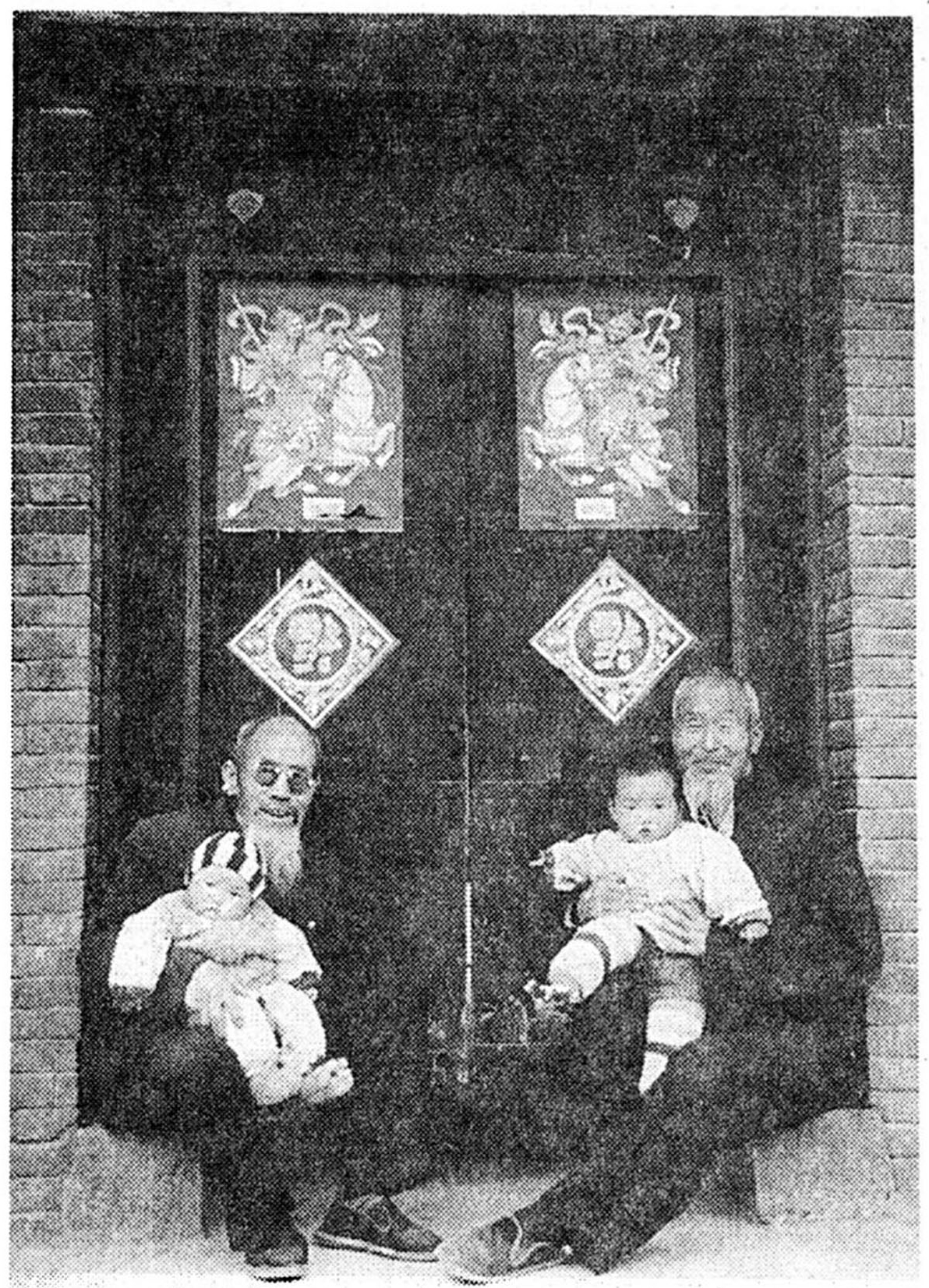(散文) 王晓云
我是你不能够了解的冰清玉洁。
虽然我的身体已经丰茂地成长为女人,所有少女的记忆迤逦而去,刚刚具有少妇丰润的颜色。
然而你何曾了解呢?如果人类只存在身体,岂不是无异于兽类,我的被你千遍调笑的冰雪聪慧具有什么意义?
冬天的时候,我站在玻璃窗内,一遍一遍用手去刻划玻璃窗上的水珠,哈着热气,一遍遍地看见你,闪烁在冰凌中。你说你已经是个不再年轻的男人,看着我守在热气腾腾的房子中,和我的夫君。当年讲童话给我的情景已经不再,我是一个为爱守候的女人。
从来没有一个女人在做其他事时象爱着那样的动人,叨着冰淇淋袋子,将甜心送给孩子;停在新鲜的果蔬前,眼中那一种温柔的神情,以及唱着轻歌飘洒在飞一样浮沫的洗衣气泡里。你可是这样认为吗?
几年以前,我说过我不能为你守候,因为曾有一个女人爱得那样动人的姿态给我看见,她的漫漫温柔塑造了你,你没有改变的余地。她是你生命的一部分,是你所有忧伤岁月不能忘记的慰藉。而我,不能有爱,走在泉水清澈的岸边,我伸下一只手臂在水中,看得见臂上的脉络清晰如线,没有丝毫错乱的痕迹。大地总是装扮得如此齐整,没有水会向上而行,没有日月会交错了晨昏。就好象我不能仰慕你的学问和财富,因为我不曾培养过,没有温柔浇灌过每一个生命的年轮。我只是一个平凡的我啊,一个有爱,爱着自己身体而又冰清玉洁的女人。
我知道在茫茫人海里必然有我的另一半,他不会象你那样负气,那样沉静,那样的丰富而又深厚,他是一个柔弱的孩子。他只有经过我的雕琢,才会逐渐地完善和玲珑,他是我不能推卸的责任。这种责任是父母予我生命的那一天,就已经交付。他还在那一端凝望我,以亘古的,不能推却的目光,他一路轻轻歌唱,踩着无家的河水向我走来。
地母是一个神,她以她的身体安慰着一切睡着了的人。她是一种真正的大气与母爱,那样不顾一切的,温暖肥壮的,让世间一切的人都奔赴而去。神话中的观音总是手持净瓶,站在路人必将引渡的河边。她丰腴的身体驱逐了一切焦躁的灵魂,给予冰冷的地狱门外一块湿润的春水。女人是有形的,有形而成其为女人,就象大地一样,她有江河丘陵,平原草场,她值得一切造物的检阅与垂爱。假如一个生为女人的人,没有过桑椹子一样成熟的颜色和春水的荡漾,必然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必然是上苍对于她的苍茫的阉割,这是多么地可悲啊!
而她在成为女人的一霎那,必然蹂媚,倦弱,那是因为,心中有爱。有爱而达到物化合一,是境界,是女人本分中的唯一。
但是我虽然与你静静谈笑,却是不能成为柔媚的,因为在我贫弱的心间,只有深深的感激与愧疚。而一切不是冰清玉洁的女人,她会在这样的感觉中,与你同化,被欺骗的是谁呢?金钱、地位、身份,哪一样才是你,哪一样是那个女人抓住的唯一,而竟可以取笑于我呢?笑我这命空烟花的女子错过了你,命里被人采摘过,在那样无奈情况下一次次死去的过去。尽可以取笑于我,让瘦燕肥环在窗外舞蹈,嘲笑我永远不能开化的红尘困顿。你尽可以得意去吧,难道中年的你仍然不懂得热闹是虚伪,难道永不明白天之女子的心胸。
那么,我与你静静谈笑时,是你永不可理解的玉洁冰清,而我,必须温柔地向潮边走去,因为我必须是水和泥土,有一个男人绊倒在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