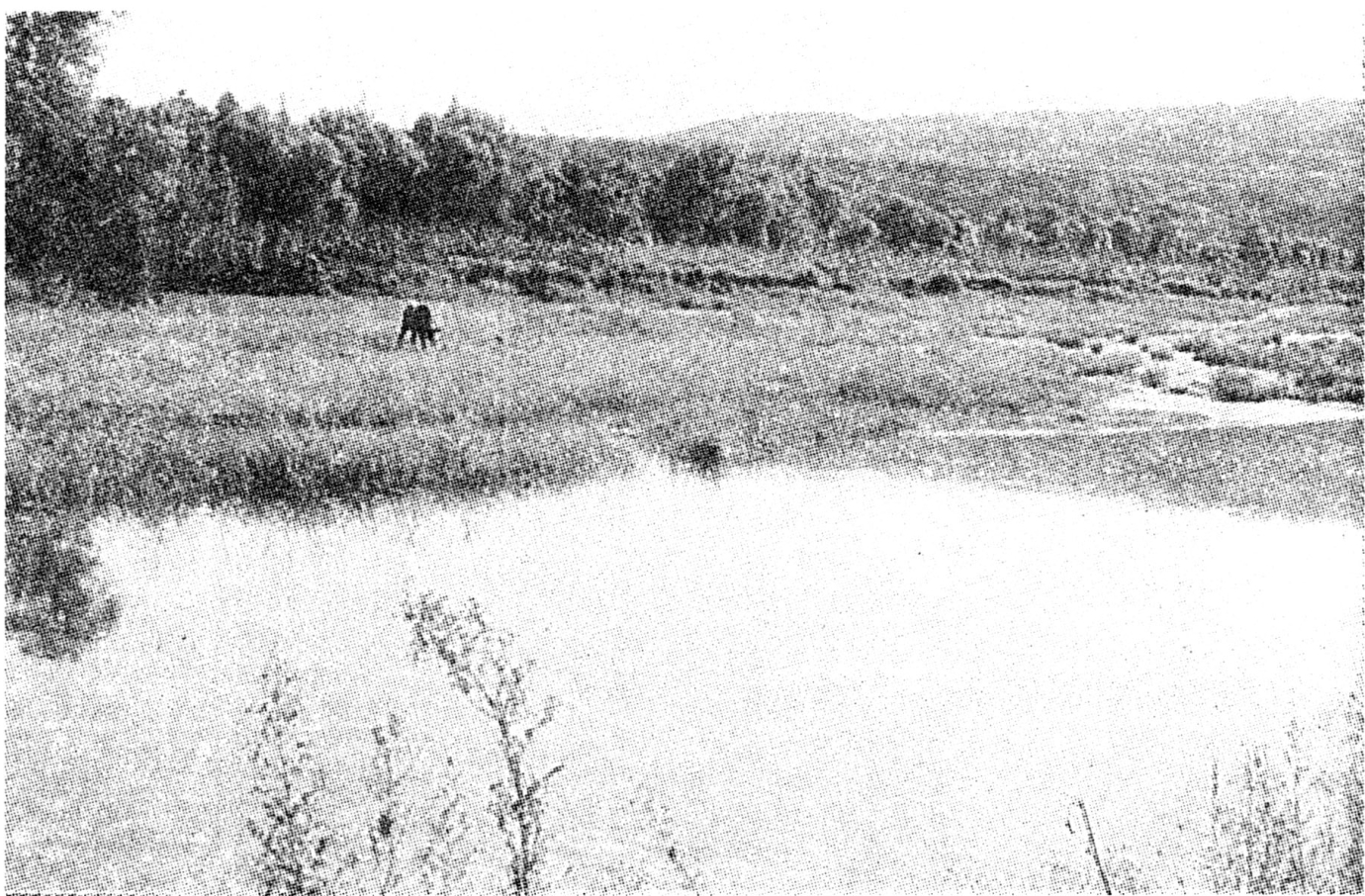(随笔) □文/鲁莽
人和动物之间,如果真的是有一点什么区别的话,我想,穿不穿衣服,大约可以是一个判别的标志了吧?我们早在黄帝时期,就“垂衣裳而天下治”,服饰文化自然源远流长。西洋人开化得比我们晚,但他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也还是知道采几匹树叶来遮遮羞。所以比其他的动物多一层包装,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标志之一,应当不假。
既然服装是做人的标志,顺理成章地,也就成为了人的社会地位的标志。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有几千年辉煌历史的国度,服装作为人的身份的符号,更是成为了专门的学问。一部《仪礼》,大半的篇幅,是在规定各种场合下的穿着。在等级森严的封建时期,服饰作为身份的标志,硬是半点也不能乱套。所以《水浒传》里面的阮小七,因为一时戏耍,穿了一回方腊的赭黄袍、龙衣玉带,就被童贯蔡京之流奏过天子,追夺了宫诰;而《儒林外史》里面的乌龟王义安因为戴了方巾出去吃酒,撞上两个破落秀才,被打了个臭死,最后还不得不从腰里摸出三两七钱碎银子来,送与两位相公做“好看钱”,才得以脱身。瞧,礼仪之邦是多么看重服饰方面的礼仪!
其实,在历史上,服装不仅是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象征,也代表着一定的政治倾向。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众所周知的改革举措;晚清末年满大人顶戴花翎参加大英帝国的国宴,当然也是一种廉价的爱国主义。据鲁迅先生讲,“清朝末年,带些革命色彩的英雄不但恨辫子,也恨马褂和袍子,因为这是满洲服。”及至革命成功,要弘扬“国粹”的时候,“北京大学要整饬校风,规定制服了,请学生们众议,那议决也是:袍子和马褂!”袍子和马褂从异类到国粹的演变,正好体现了当时所谓“革命者”“革命方向”的大转变。
当然,服饰与革命连在一起,并不止于清末。“文革”期间。破“四旧”,禁“奇装异服”,剪小裤管,是响当当的“革命行动”。即使到了八十年代,我从学校毕业时,父亲还特地来信叮嘱,万不可穿西服去单位报到,以防给领导留下倾向西化的不良印象。殊不知眨眼之间,西服的地位竟一落千丈,从洋派人物的标志沦为“阿乡”的装束了。西服与马褂的兴衰历程,何其相似!这也许可以作为我们的文化特别地牢固的一个佐证?
其实,在我们老百姓看来,为穿衣而穿衣的人,大约只算得上是个模特儿吧?而以衣帽取人,以衣帽骄人,则更是可笑得不得了。说老实话,我就顶瞧不起对人家的穿戴说三道四的教师爷,认为他们非常地浅薄和陈旧。毫无疑问,服饰可以折射世情,却不能兴邦或者丧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不妨反问一句:披一件马列主义的外衣,难道就成了马克思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