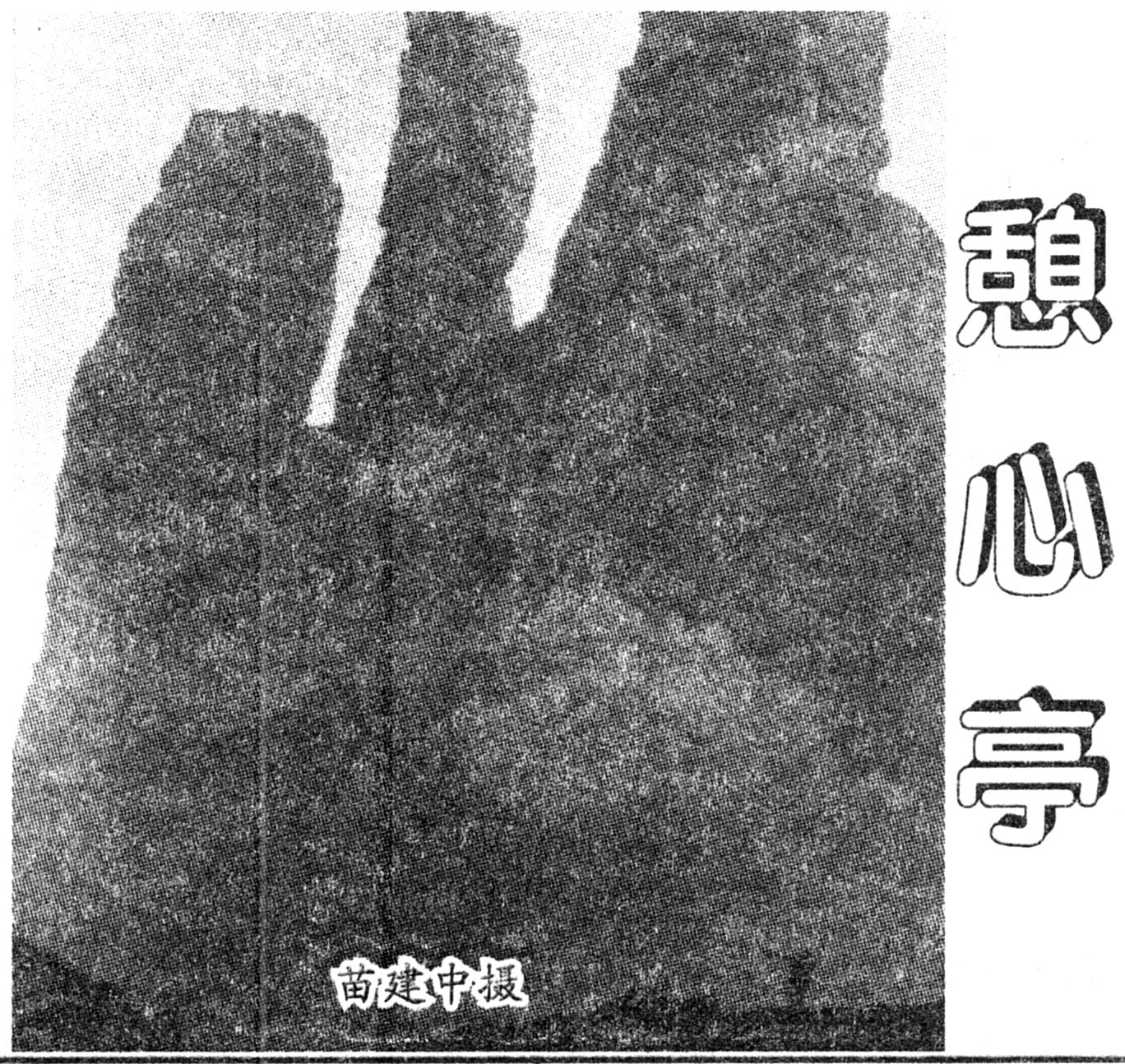文/王志君
大师是从遥远的省城来的。大师瘦长的身影一从坡底下升起来,就引起人们的注意。山里难得见一个陌生人,更何况是一个来自城里的陌生人。人们放下锄把和犁铧,跨过田间的沟垄,互相呼唤着,来到山路边围观大师。大师白净的脸庞上架一副酒瓶底那么厚的眼镜,穿一身干净的中山服,一路风尘,而他的头发竟梳得出奇地整齐。大师向前走,步履不疾不缓,一投足、一甩手都有一种优裕自如的从容和超然。大师向人群颔首微笑,人们都不约而同地“噢”一声,不知道再应该说点什么。
大师是犯了政治错误的“右派”。这是大队支书夜晚在油灯下告诉那些叼着旱烟袋的支部委员的。山里人性格憨直敦厚,他们认定了身体单薄少言寡语的大师是个好人,他便是个好人。生产队分瓜分杏分口粮,总忘不了有大师的一份,大师感动得连声道谢,眼镜片后的目光湿漉漉的。可人们发现大师总有很稠的心思。黄昏收工后,大师总背着手,佝偻着高瘦的腰身,沿着开满野花的幽静的山间小道慢慢地走。月色溶溶,远山升起了淡淡的雾霭,各种昆虫的鸣叫次第响起,月光下的大师显得异常孤独和凄凉。
一个偶然的机会人员才知道了大师是艺术家。那天中午,公社通知说第二天地区要来检查农村革命工作,大队支书慌忙布置人员准备欢迎仪式。村口羊圈的十几堵墙上要写标语。初中毕业的大队文书挣扎出满身汗珠写的字依然象龟爬一样丑。这时有人想起了大师,赶紧去请。大师手持刷子,颤巍巍地爬上梯子,人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大师停在梯子顶端,微眯双眼,深吸一口气,一刷子下去,一个遒劲有力的大字一气呵成。这个字有墙那么高,也有墙那么宽,围观的人嘬起嘴唇发出连连的赞叹声。十几个大字写完,大师飘然落地,双眼炯炯有光,腰杆笔直。人们发现,他风纪扣扣得严整的衣服上连一滴白灰也没沾上。
第二天,地区革命委员会来了一位肠肥脑满的官员,他问起大师的情况,然后厉声喝斥:“这样的人怎么能留在村子,放到后山打石头去!”大师于是又被发配到了更加偏远的后山。
大师在后山一呆就是四年。大师的眼镜片被小石子碰碎了,用胶布粘着;大师的手掌已被石头磨得粗糙,还有一条条细长的疤痕,手指骨节粗大,几乎要撑破黝黑的皮肤,指甲盖全都被铁锤砸得断裂脱落。这就是一个艺术家的手吗,谁能知道,这双手创作的画和书法作品被东南亚博物馆和日本皇室收藏过,而他却在中国最偏僻的山村里,用这双精巧的充满灵气和智慧的手砸石头!
大师依旧衣着整洁,长衫长裤,哪怕再炎热,他也绝不会解开衣扣。在这个女人不会涉足的世界里,充满了荒蛮、粗砺和狂野,人们只穿着一条裤头,头发蓬乱,满身臭味,满嘴秽言,而大师每晚总要将衣服洗得干干净净,晾晒在热烘烘的石头上。他沉默不语,饱含忧患的眼睛望着远处起伏的山峦。山风吹过来,他单薄的身体一阵颤抖。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有时侯,要坐到天亮。
四年里,砸石头的民工换了一拨又一拨,而大师依旧拿着他的钢钎,编在下一拨民工的队伍里。
“文革”结束后,落实政策,又是那个肥头大耳的家伙来到我们村。他的肚子比四年前更大了,一走动就左右乱晃,几个在老槐树底下纳鞋底的老太婆捂着嘴偷偷地笑。他的官职更大了,管全省的“平反昭雪”。他坐在大队部的太师椅上,让大队文书从后山叫来了大师。大师尽管苍老了许多,可依旧昂着挺胸,目光犀利。大肚子官员斜倚在太师椅上,故意一字一板地宣读了文件。也许他想大师一定会跪在地上,感激涕零,然而没有。大师表情依然沉静,眼光越过他光亮闪烁的秃顶,望着一个遥远的地方,淡淡地说声“知道了”,就转身离去。他的脚步响亮而沉着。
大师是最后一批回到省城的“右派”。
半年后,大师用他补发的工资买来了一台粉石机,安装在后山。粉石机日夜歌唱,而大师却再没有回我们村。
省城里的大师日夜创作,他农村题材的画作轰动了画坛。我也只是在报纸上才能了解大师的行踪和近况。
两年后,大师因积劳成疾,不幸与世长辞。 全村一片哭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