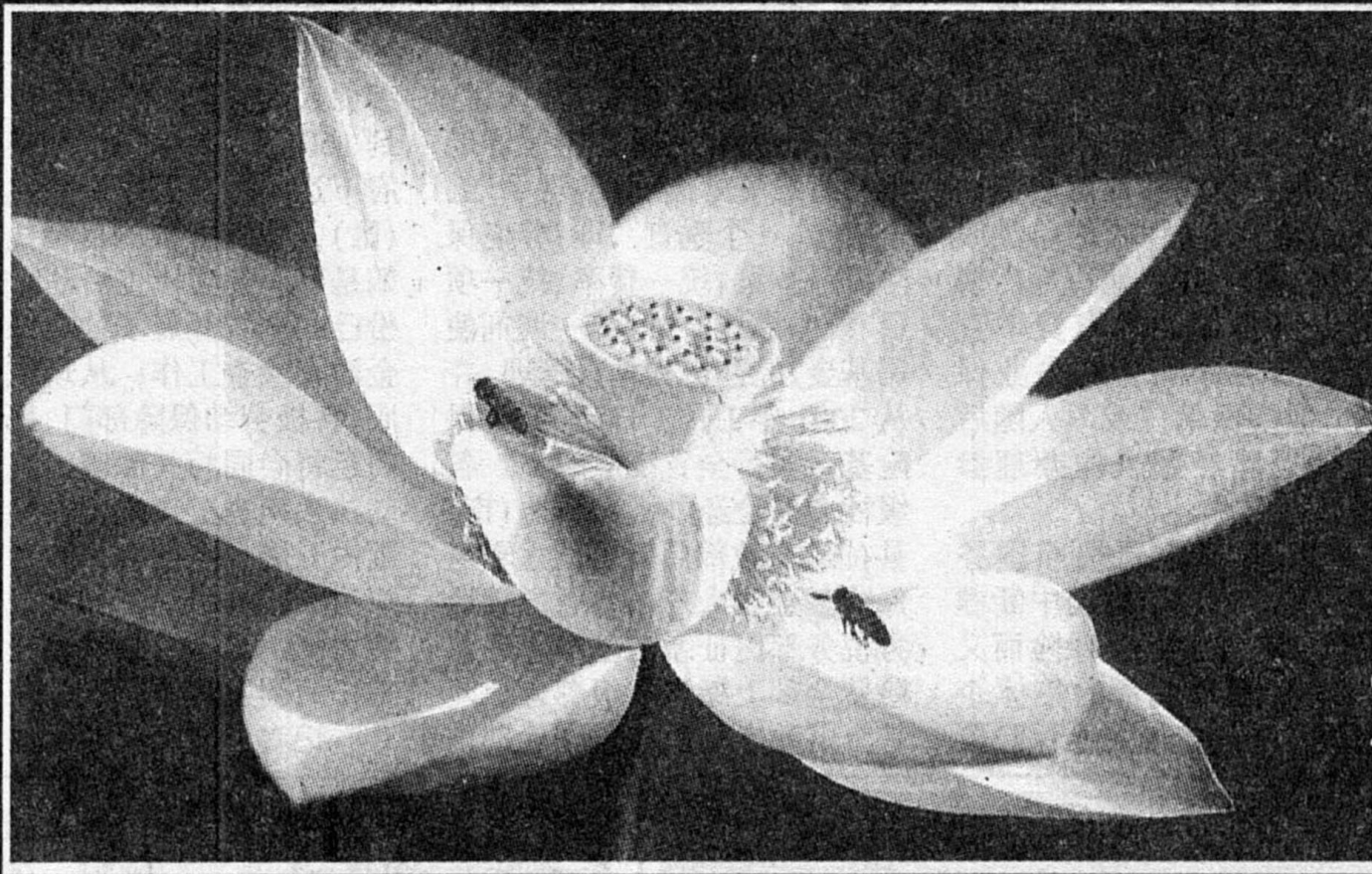文/张晓峰
在发电厂工作了一辈子,他人缘颇好,厂里的男女老少他都合得来。东家找他喝杯酒,他醉醺醺地回来说,今天喝得痛快。西家请他陪陪客,他摇摇晃晃地回来说,今天喝得舒服。这一来,他就成了全厂有名的醉汉。这一来,厂里的红白喜事他都得随份子走人情了。
厂长的儿子结婚,书记的闺女出嫁,他都得送红包。车间主任的父亲去世,工段长的母亲住院,他也要花钱。就连班组长的朋友过生日什么的,他照样红包在先。有时红白喜事重了,他也得象“星”似地赶场,实在赶不过来,也得人不到礼到——最少一百元。这叫“醉汉的心意”。他总是想,泥多佛大。钱是人赚的,也是人花的,花掉又会来。可现在是穷了和尚富了庙,怎么来呢?他“光棍”一条,只赔不赚,眼下可犯愁了:老家来信母亲病危,要他速回。
醉汉开始失眠了。他暗自思忖:回家一趟至少好几千,他猛然想到,厂里人不是有个礼尚往来么?
第二天,他衣冠楚楚,搂着一个艳丽女人的细腰,在全厂上下游了一圈,示意:他再也不是“老光棍”了。大伙都夸赞醉汉有醉福,找的老婆年轻漂亮,馋得年轻人都直流口水。当大伙问他啥时候办?他乐呵呵地回答:“马上办,马上办!”
打铁趁热。他兴冲冲地把几百张请柬分送给他随过礼的人家,请大家十天之后大驾光临“喜之郎酒家”,参加他的夕阳红的婚礼。
灯光望着他聊以自慰的表情。他越想越有意思了,真是:天不转地转,山不转水转,如同日夜旋转的发电机,把所有的灯炮都转亮起来了。你看,这么多红包转到咱手上来了,令他心旌摇荡。摸摸一万多元的礼钱,心中暗道:回家的钱有了,除付给歌舞厅请来的小姐陪着搂了一天细腰费用外,还手头从容,厂里若有什么红白喜事,还可抵挡一阵子。
十天之后,他从老家回来,右手上却戴着黑孝。当大伙问他,婚事究竟是哪一天?他干脆醉话醉说,现在只有把喜事改成丧事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