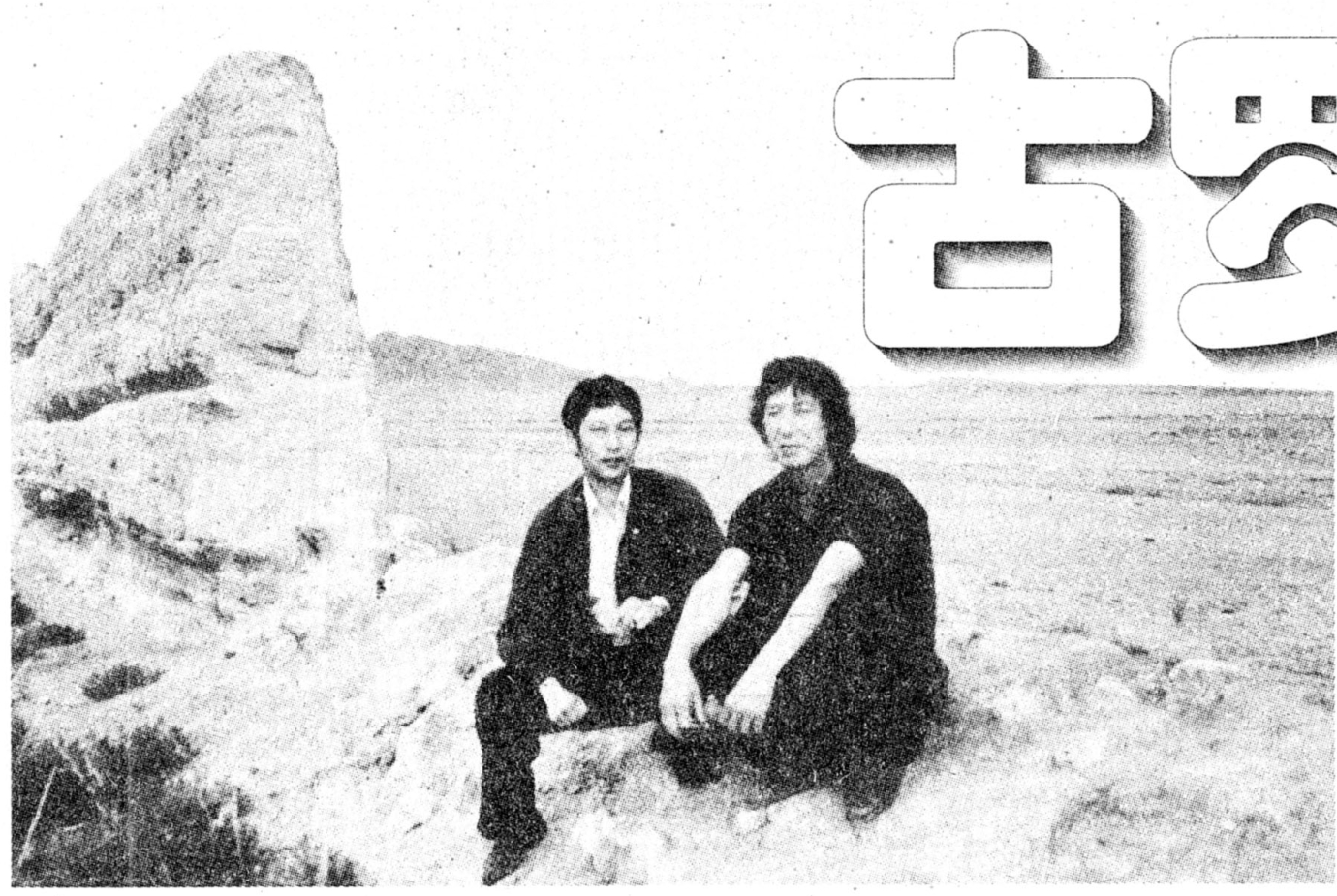□文/徐成淼
生命总是艰难,我们走过了那么曲折、那么坎坷的路,每一步都趟着水,趟着火,趟着泥泞,都要咬着牙绷着劲硬挺。然而,当苦日子真的结束,当那一切都已成往事,我们回首昨日,在感叹之余,却发现那些苦难,那些熬着挺着过的日子,却原来竟有些许诗意。生命之蛹挣脱茧壳之后,总会蜕化成五彩缤纷的蝴蝶。
萧重声就是这样,他找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将他艰难的生命历程,转化为一篇篇刚劲而又不失委婉的散文,那就是他的散文集《神水》。和许多同代人一样,萧重声年轻的生命是沉重而困厄的,饥饿、贫穷、病痛,重叠地压在了他稚嫩的肩上。所有的艰难都是具体的,在当时,那就是一餐饭、一袭衣、一挑柴禾、一盏灯,这样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萧重声用一桩桩真实可信的“细节”打动你,用那些让人有切肤之感的具体经历感染你。你读他的《痴心与抗争》,你和他一起感受到农家子弟求学的艰难。在求生存和求学识之间,那冲突竟是那样地令人刻骨铭心。“那时老弟兄三个尚未分家,全家上下几近二十张嘴巴,每次吃饭时,宽大的案板上仅土瓷碗就是白花花一片,看一眼都让人害怕。”这是一个多么有说服力的细节,具体而又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那一二年天公又不凑趣,家乡闹饥荒。冬春之季,家里常揭不开锅”。在“白花花一片”的土碗中,萧重声却渴望着读书。“因为白天要干活,只有到晚上点灯熬油。父亲一觉醒来,看见我房里灯还亮着,就会埋怨:‘往死里看!油全让你点完了!’”这就是生活!然而,萧重声的散文不是诉苦,不是埋怨,更不是像有些艺术的幼稚者那样,一写苦难就是哀怨和眼泪,就是哭泣和号啕。萧重声的散文既是婉约的、隐忍的,又让人看到一种内在的、男子汉逼人的英气:在苦难和困厄面前,决不退缩,决不屈服。这就是艺术的力度,是沉积于散文中的可贵的“钙质”。
萧重声的诉说总是那样制约,总是寓哀伤与不幸于平静的语言之中。面对《神水》,你会想像自己是面对一位坚韧的男子,哪怕遭遇锥心之痛,他也要绷紧了面孔,让已经涌上眼眶的热泪内流,流进自己的心里,流成诗的语言,也流进了读者的心中。比如搂柴,为了将麦茬地里的柴禾搂得更干净,“身体单薄的”他,“给耙面横梁绑上一块石头,来增加耙齿儿扒地的力量。”“拽着大铁耙本来就挣人,这会儿就更觉沉重了。”他“一步一声喘,一步一滴汗。串串汗珠砸在滚烫的地上,哧溜哧溜地响,溅起一缕缕白生生的轻烟。”接下去他写道:“大铁耙仿佛一架移动的竖琴,徐徐行进,呼呼隆隆,连续不断地奏出浑厚悦耳而又节奏明快的乐曲,听得我心里迷醉。奶奶曾经说过:‘搂柴是给麦地搔痒痒哩!’由搂柴娃子们演奏的这首搔痒之歌,何尝不可视为大地母亲身酥心醉时不由自主的轻吟浅唱呢?”我相信,这是文学给旧日的伤口抹上了一剂清凉的油膏,就像受了伤的战士,他缠上了绷带,不经意就成了画家笔下的艺术形象。这正是萧重声用他那带着浓厚陕腔的语言,不紧不慢地向我们讲述那些当年触目惊心而如今已成为悠悠往事的情节和故事。
读萧重声的散文,使我们感叹,感慨,但更多的是振作,是欣慰:因为我们毕竟走过来了,挺过来了。那一切,毕竟都已经成为可供回味的往事,毕竟可以让我们以从容的心情,将其编织成可供欣赏的艺术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