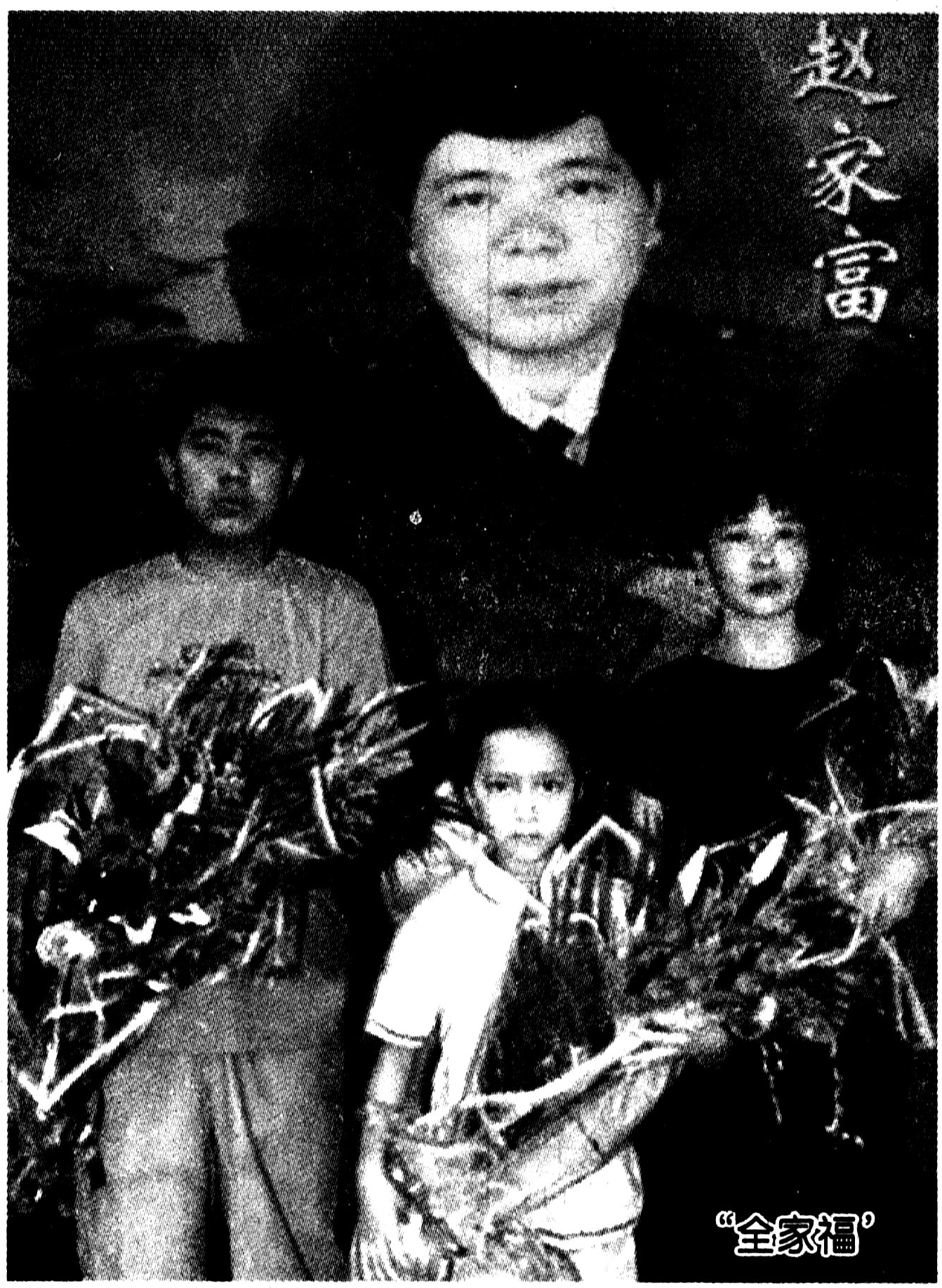□朱进平
多年以来,我总认为,除了政治家外,文人恐怕是最有气度的了,尤其是文化名人,因为他们学识渊博,有涵养。可是现在看来,都不尽然。以著名学者余秋雨为例。
《南方周末》最近刊登了一篇《余秋雨有话说》的长文。文章的第一个大标题是“质问媒体余秋雨七问”全文共两大版,它给我的总印象一是余秋雨在大诉冤屈,二是余在为自己评功摆好。文章开始,余秋雨便连发七问,问媒体,问批评者,问他们多年来为什么总是和他这个“无职无权、没有圈子的个体文人”过不去。而面对媒体从前所报道过的批评文章,余秋雨却没有一点承认自己不足的意思,就连金文明先生指出他书中的那么多“文史差错”他也未认可一条。反说金“咬”他是为了出名,为了“一夜暴富”。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古代有过“一字师”之说,现代亦有过郭沫若先生的“一字师”佳话,可余秋雨却把自己看得如同“完人”一般,一点缺陷都没有,谁也批评不得,否则就跟你急,就说你和他过不去。这种骄傲自满、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作风我却实在不敢恭维。
有趣的是余秋雨在拒绝批评、大诉冤屈的同时,仍没忘为自己评功摆好,讲自己的那几部学术论著是何等的重要,都得了哪些奖,讲自己学生时代的成绩是多么的优秀,讲自己当官时是多么地众望所归,讲自己考察中西方文明时是多么的辛苦卖命……更有意思的是他讲自己面对那么多批评却“没有求助过任何官方的力量,制止这场大批判”“没有向任何人求助”,由此也“可以证我是个善良的人吧”。令人更不可思议的是他还要求“那些恶意批评我的人,请拿出你们的学术著作来比比看”,好像没有学术著作你就得闭嘴,就没有资格批评他似的。批评和反批评本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了,可余秋雨却偏偏地一人说向隅,厌恶主流社会,甚至闹到要“封笔”,要“到一个冷僻的地方”去,嗣后却又跑到陕西来张扬。这除了气度的狭小外,还应当加上两个
字:“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