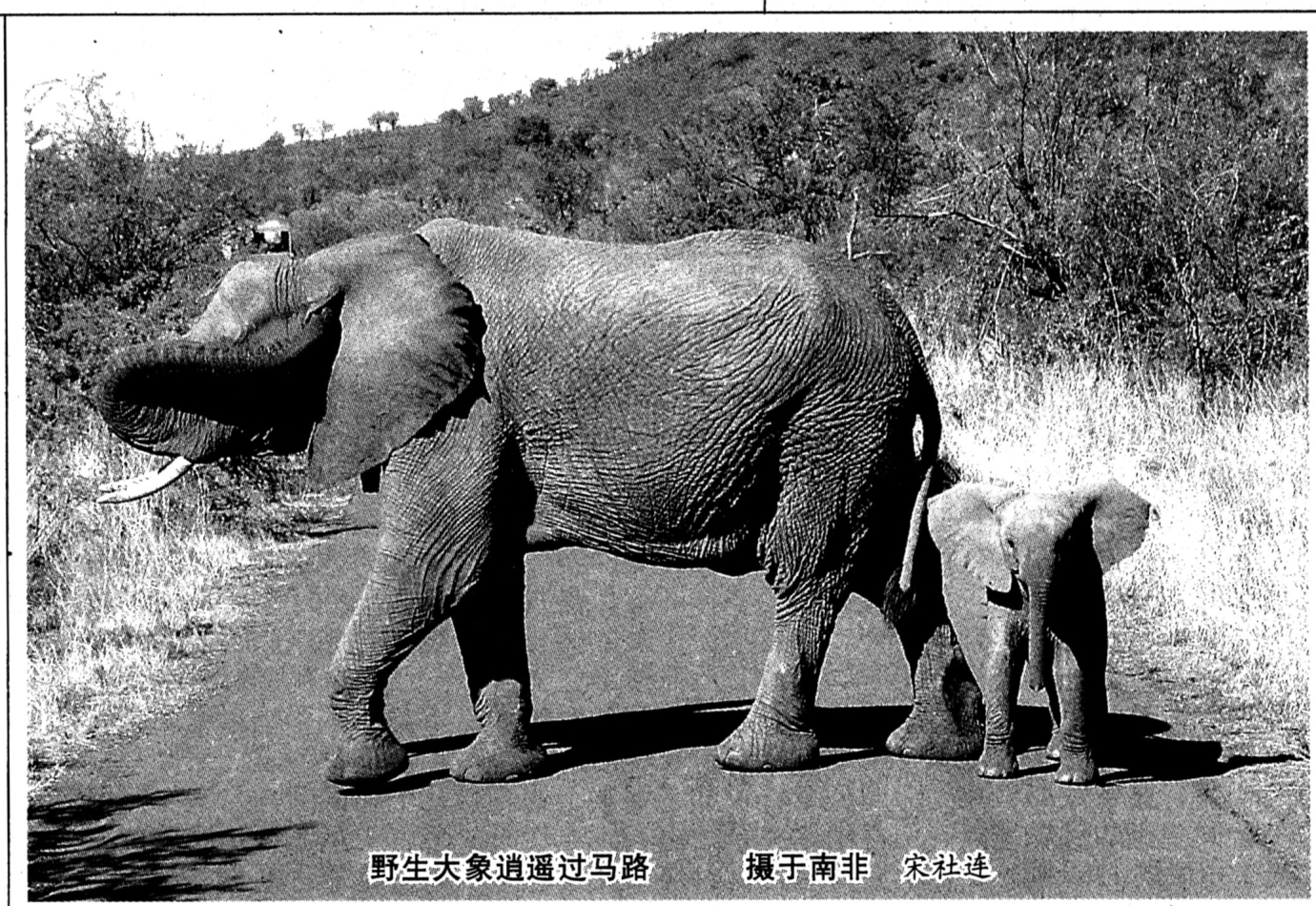文/王玉信
1980年秋的一天,听朋友介绍说,他乡下的一个亲戚家里祖传有一套古式家具,让我去看看是否有收藏价值。到了星期天,我就急不可待地和朋友一起骑车赶到离县城100多里的乡村。在朋友的引荐下,主人才让我们观看。不看还罢,一看令人拍案称奇。这是一件明代黄花梨条柜,这在当时能和一座四合院等价。我压制住内心的激动且不露声色。听主人介绍说:“‘文革’时‘破四旧’,此条柜险些被造反派抬出去劈掉当柴烧,能保存到今天实属不易。现在孩子考上了大学,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所以想卖几个钱供孩子上学,如果你想要,就看着给几个钱吧。”我说:“给你2000元咋样?”“行、行、行、不少、不少,这钱够给俺孩子报名了。”
在往外抬条柜的时候,主人又从里面掏出一只紫砂壶来。老人说:“俺们农村也没有喝茶的习惯,就送给你留个纪念算了。”我不住地点头说:“谢谢,谢谢!”但就是这把在外行看来不起眼的宜兴紫砂壶,没想到前不久却让我有一份意外的惊喜。
那是2001年10月的一天,天气很冷,小雨夹着雪花,也就是这一天,一个专做紫砂生意的台湾老板在友人的引导下直奔寒舍。双方寒喧几句后,这内行一眼就看到我放在收藏柜里的那把紫砂壶,拿在手里把玩时有点爱不释手的感觉,壶底写有“杨彭年制”铭款。这位老板问我要多少钱出手,我说随便,想着本来就没掏一分钱,是人家搭给的多余货。这位老板说:“两万元可以吗?”一听两万元吓出了我一身冷汗,这把小小的紫砂壶能值两万?我虽然对紫砂壶外行,但此时我也得打肿脸皮充胖子,随口道:“别开玩笑了,少说也得5万,你看好了,这可是时大彬制作的宜兴壶啊。”经讨价还价,最终以38000元成交。事后,当我把这一事告诉行家刘某时,刘某长叹一口气说:“老弟,你又上当了,你道这时大彬是何方人也?实话告诉你,杨彭年是清代制壶名师,与邵大享、陈鸣远齐名,用此壶泡茶,色、香、味俱佳,且隔夜茶不馊不霉,即使是无茶空壶煮沸水也有茶香。前几年有一外商想以一辆豪车交换一把壶,都被拒绝了。可现在仅给你3万多块钱你就满足了。”他的一席话说得我目瞪口呆、懊悔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