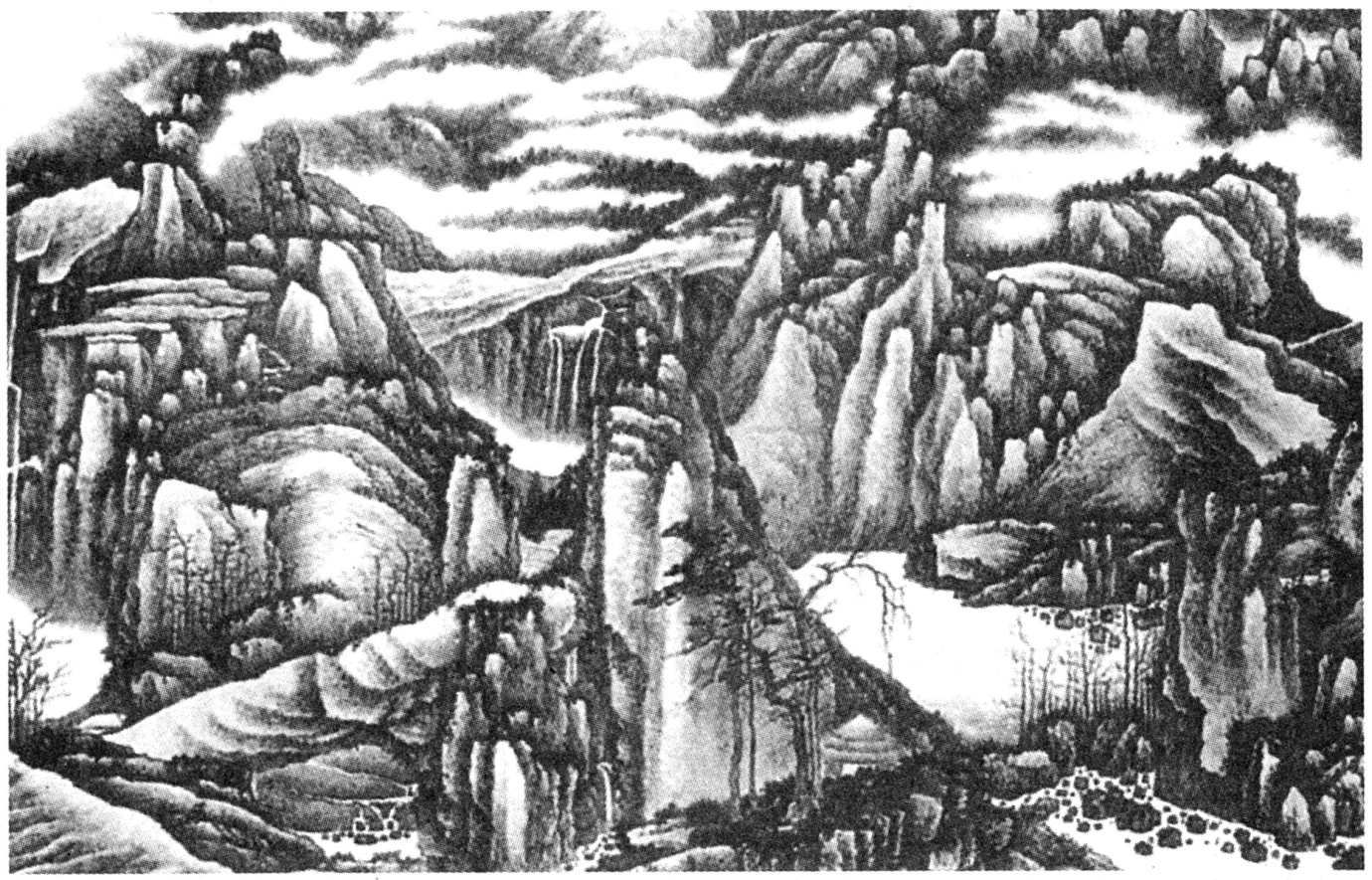老柯
喜欢看书,便与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
自小到老,一直生活、工作在小县城,也就成为县图书馆的常客、熟客乃至“特权读者”。“特权”者,其实便是无须经过翻索书目卡手续,能够直接进入书库,在一排排书架上随意搜寻自己中意之书(当然,彼一时,此一时,现在这种“特权”,读者无论在图书馆或书店,皆可享受了。)图书馆地处老县城。老县城座落在一兀自孤立的塬台上,其四面断崖,即形成天然城墙。大约因其断崖陡峭,势若刀斩,建于此上的老县城,遂亦被称为“斩城”——据说目前国内仅有此一处了。这个按下不说;单以县图书馆此处形胜之地而论,倒是颇与中国悠远苍古文化相契相合的。惜乎随着新县城的建立和发展,老县城日渐冷落遭弃,县图书馆亦迁至新城。所谓大势所趋,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不过,资金不足,拖了一二年建成的新图书馆却令人大失所望:少了老图书馆古色古香幽邃儒雅的历史感自不消说,地盘也小得可怜。除了一个黄土朝天不见片绿的小院,便是那栋毫无特色挤在一片商业区的灰头灰脑的楼房了。更使人尴尬的是,挤在小院一隅仅有两间平房的阅览室,报刊虽不多,管理人员却不少:或老或少居然有三个女同志。我不知这种不合理安排,馆方是否另有苦衷;但作为读者(往往只有我一人),在这不足二十平米局促环境和六只目光笼罩下,自是极不舒服甚至如芒在背了。故而去了几次,便再无勇气受那份罪了。
年前到广东一城市小住,闲逛时竟与该市图书馆“不期邂逅”,不禁老毛病发作,拾级而上,轻踱而入。从外观端详,整个图书大楼是呈“丙”字结构的一组白色建筑。主楼楼顶被别出心裁地建成打开的一册书卷状(我猜度从空中俯瞰此“书”,当更逼真、诱人)。环绕这一知识圣殿的,是大片大片的草坪,一排排高大的椰树,以及精心布置的假山、水池和可供人小憩的赭红色巨石。从三面通往图书室和阅览室(在二楼)的石阶两侧,摆着一盆盆时令鲜花。倘是铺上红地毯,读者简直就是享受“元首级”待遇了。当然,红地毯是没有。有的,是那种对知识(包括读者)的尊重,或是说与知识殿堂相匹配的庄重、幽美乃至舒服环境。
足有上千平米的阅览室(该称“大厅”才是),不仅配有电脑、复印机等现代设施,全国各省的主要报刊也应有尽有,其中多数报刊,对我都是首次接触或久违了的。阅览室对读者的考虑亦颇周到,通道两边,间隔摆着一张张配有两把高背椅的棕色小桌,头顶圆筒状的灯光柔合地落在桌面上,极其方便阅读或摘抄资料。刊物、报纸任由读者自取。刊物阅后亦可放在桌上走人:盖贴在桌上的小字条告诉你,刊物将由工作人员收拾送回原处。时下进阅览室都须办证的。“混”进去几次后,我发现工作人员对无证读者亦颇宽容。尤其对放学后来此随便翻翻的中小学生,有证无证,都大开方便之门,只要不大声喧闹即可。至于对我这个外地游客,大约看在年老份上,则从来没要过证的。遗憾的是,我终于要离开这个城市了。走前,特意又去了趟图书馆,算是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