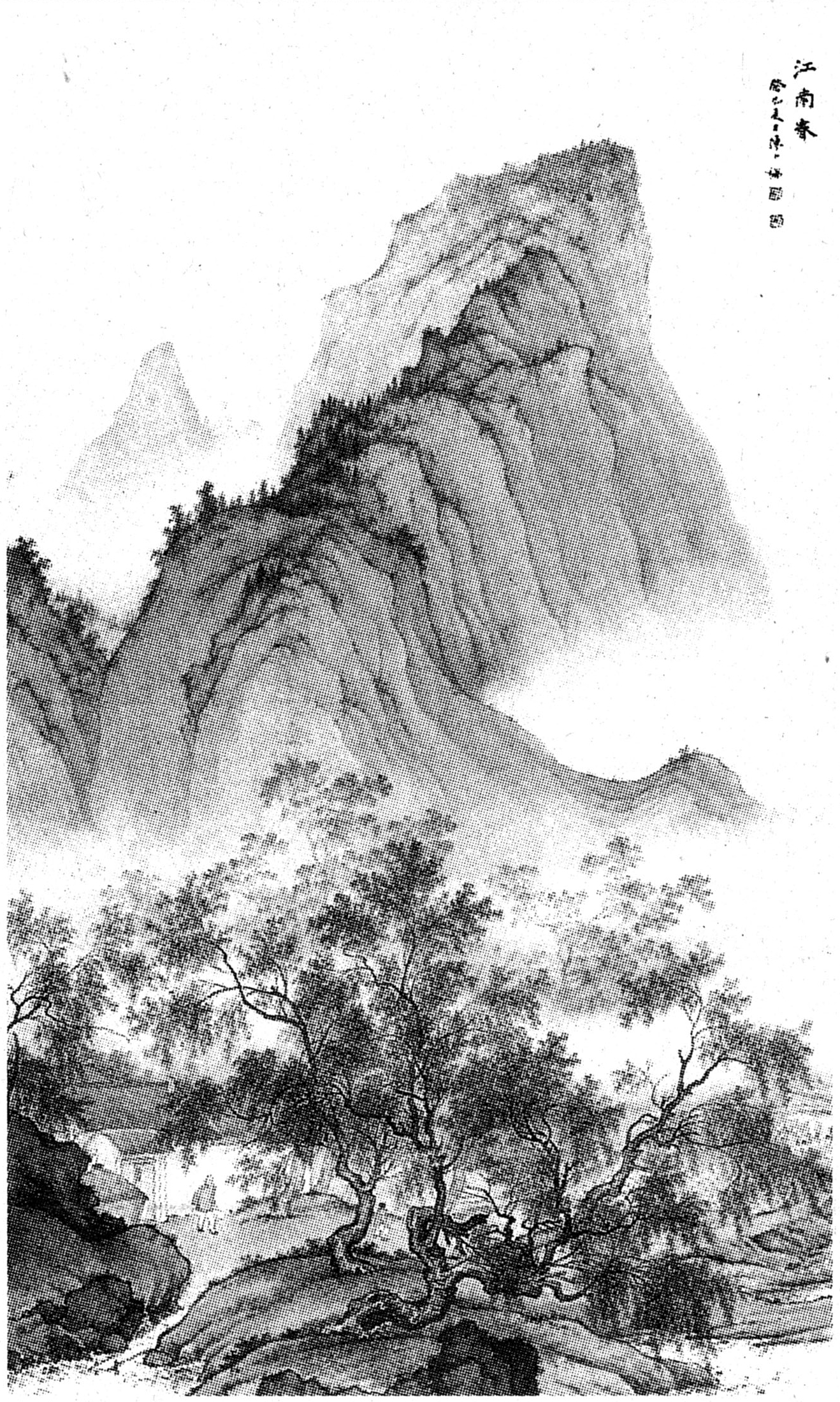李业成
鲁迅从文,本有深义,他是想用笔来医治国民精神上的病。这种文章的使命是神圣的。鲁迅一生的写作,没有违背这个使命。但在现实面前,鲁迅又充分估价到文章的分量和文章在社会中起到的真正的作用。
鲁迅在香港的一次演讲说,“一首诗吓不倒孙传芳,一声大炮就把孙传芳给吓跑了。”正像他说“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一样,这就是现实。鲁迅弃医从文,抱着一种使命,那也不过是他的愿望。虽然他始终没有放弃这个初衷,但他实际上并没有把一篇文章看得那么神,一定要有救世疗疾的功能。首先写文章是一个很苦的行当,即使像鲁迅这样的天才,也不能文思泉涌,摇笔即来,他自己说“我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是挤出来的。”鲁迅在当时被人称为“中国的尼采”,但鲁迅并没有把自己的文章看得那么重要和神圣,他期望他的文章“速朽”,在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时,他断然拒绝,他觉得自己不配,中国还没有人配领这笔钱。鲁迅是明智的深刻的。
对于文章,鲁迅有一个非常朴素的亲切的观点,“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但有时只要有一个人看便满足:好友,爱人。”这就是说,有自己满意的文章,首先由亲近的人分享就满足了。而没一心一意地“为读者写作”“为读者活着”。鲁迅的文章,为了便于发表,一生曾用过150多个笔名。鲁迅后期住在上海,实际上是以写作谋生。中国的稿费那么低,靠写作谋生是很困难的。鲁迅曾慨叹:“中国最不值钱的是工人的体力了,其次是咱们的所谓文章,只有伶俐最值钱。倘真要直直落落,借文字谋生,则据我的经验,卖来卖去,来回至少一个月,多而一年余,待款子寄到时,作者不但已经饿死,倘在夏天,连筋肉也都烂尽了,哪里还有吃饭的肚子。”
鲁迅虽然深知文章的实际作用,但他始终没有丢弃“弃医从文”的那个初衷。这样的作家以文谋生就更困难。做人最起码的标准是与人为善,为文要有为文的良知。鲁迅在《坟》的后记中说,“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的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章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样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鲁迅为文又是那样的小心翼翼,这是为文的良心。鲁迅被人称为“战士”,他的笔被誉为投枪和匕首,这是鲁迅的风格和胆气,与鲁迅的文章观实际并不是一回事。鲁迅在临终时的遗言里写道:“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道尽文章艰辛,这一行是不可勉强为之的。
鲁迅是站在批判的立场上写作,他说中国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那种传统的“文以载道”、“文章是经国之大业”、还有那些“帮闲”和“帮凶”,把文章捧得那么高,不合实际,自然会受到鲁迅的批判。鲁迅那么热心扶植帮助文学青年,多处于热爱青年,没有以导师自居,也没按自己“弃医从文”的那种愿望来灌输青年,有的只是对艺术的真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