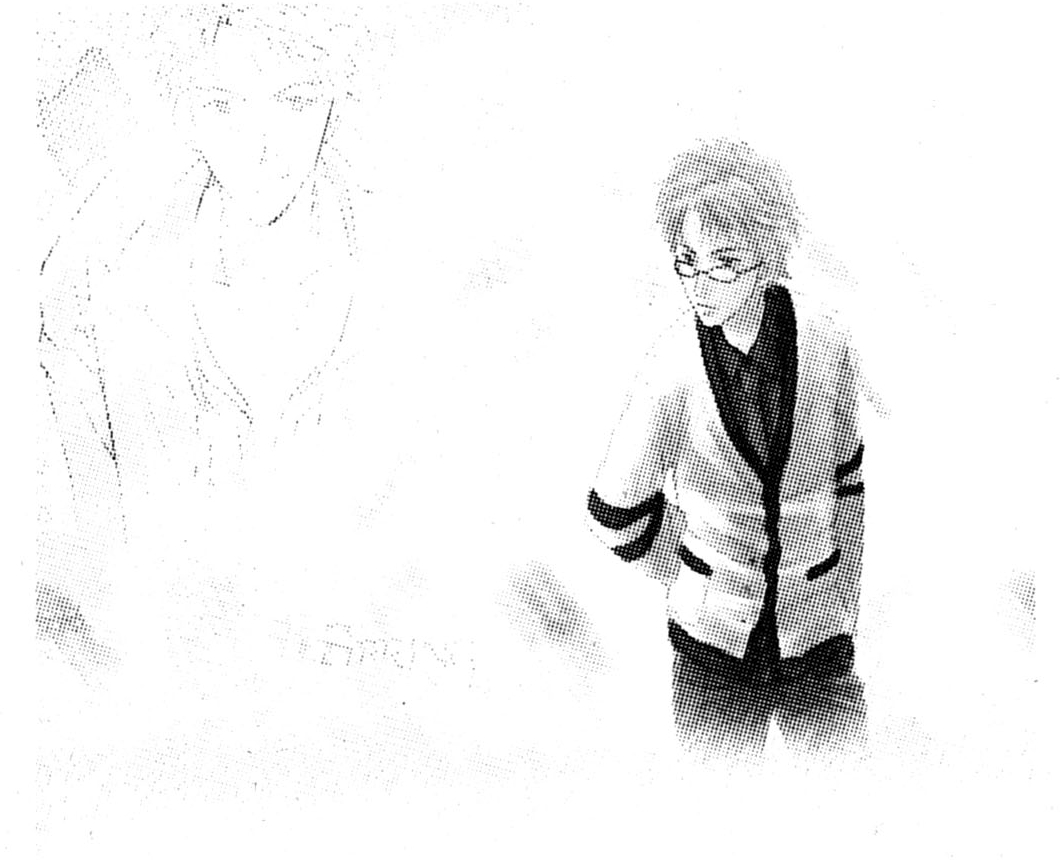[安康]彭东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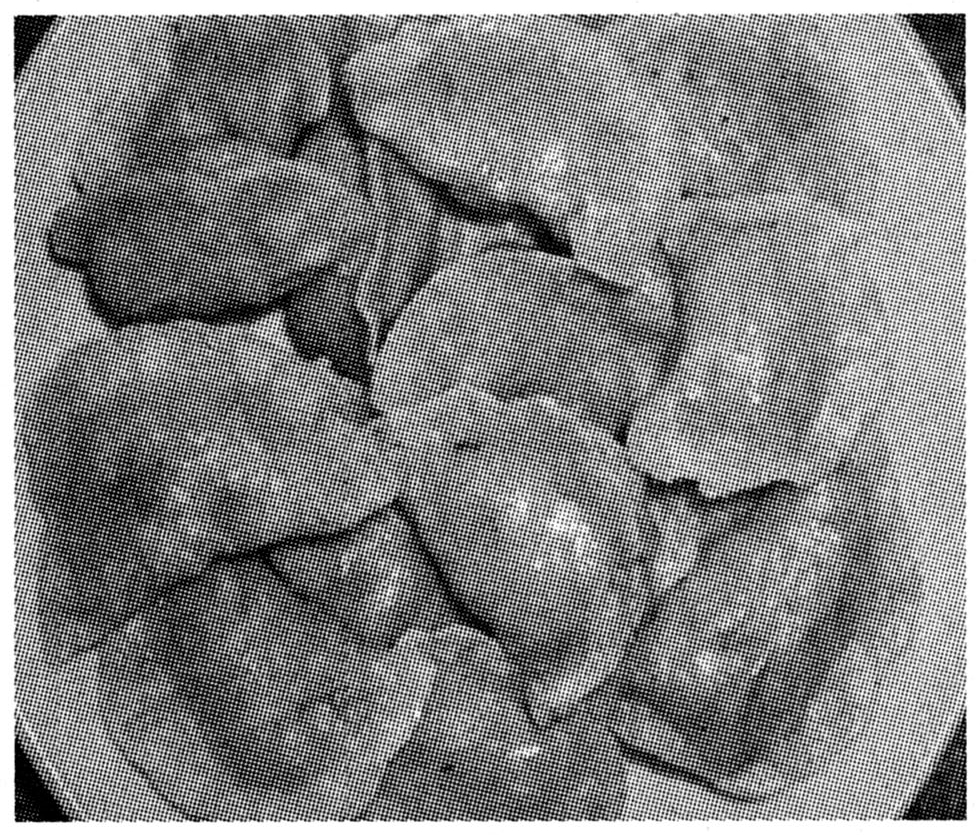
前几天上街买枕心,商家不住地介绍:“这是用荞麦壳做的,可清热、下火、明目……”这让我想起一段与荞麦有关的往事。
30年前,我家住在宁陕最南边一个叫铁炉坝的小镇上。外婆家离小镇有10里路,那里有高大的柿树,连片的桃树、杏树,还有一段宽而平坦的河湾,风景如画。假期里,我便成了外婆家的常客,一会儿爬上树摘果子,一会儿跳进河潭里洗个痛快澡。
那时候的村庄还叫生产队。粮食种的都是些老品种,产量不过关。惟一的增产渠道就是开荒挖火地,扩大播种面积。由于山高坡陡石头多,土地的肥力有限,往往是头年种了苞谷、洋芋,二年就撂荒了。为了填饱肚子,村人很勤劳,就在稍好些的二荒地撒上荞麦、燕麦等一些产量极低但能耐贫瘠的杂粮。于是,在阳春三月整个山坡上都开满了淡紫色的荞麦花。
秋天的时候,外婆家也分到了两斗荞麦,其色黑灰,菱形,紧握会扎手。像磨麦面一样,将其淘净晾干就可上石磨了,箩出来的荞面也带深暗色。可做成荞面发糕、荞面杠子、荞面片子。一次,外公要出远门,头天晚上外婆做了十几个豆腐馅的荞面饺子,个头有拳头大,看上去乌里发亮,让外公带到路上做干粮。还特意给我留了两个,在火塘上烤黄后,其味甚美。外公不是经常出远门,外婆也不是经常做荞面饺子,即便是包酸菜的馅,也因为那是干食而太浪费金贵的粮食了。
外公外婆早已作古,30年了我也没有见过荞面饺子。荞面是那时的粗粮,如今反倒成为稀罕物,其吃法也早已花样更新。尽管现在顿顿吃白米细面,但荞面饺子的形、色、味和相关的往事,却被陈封在心中总也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