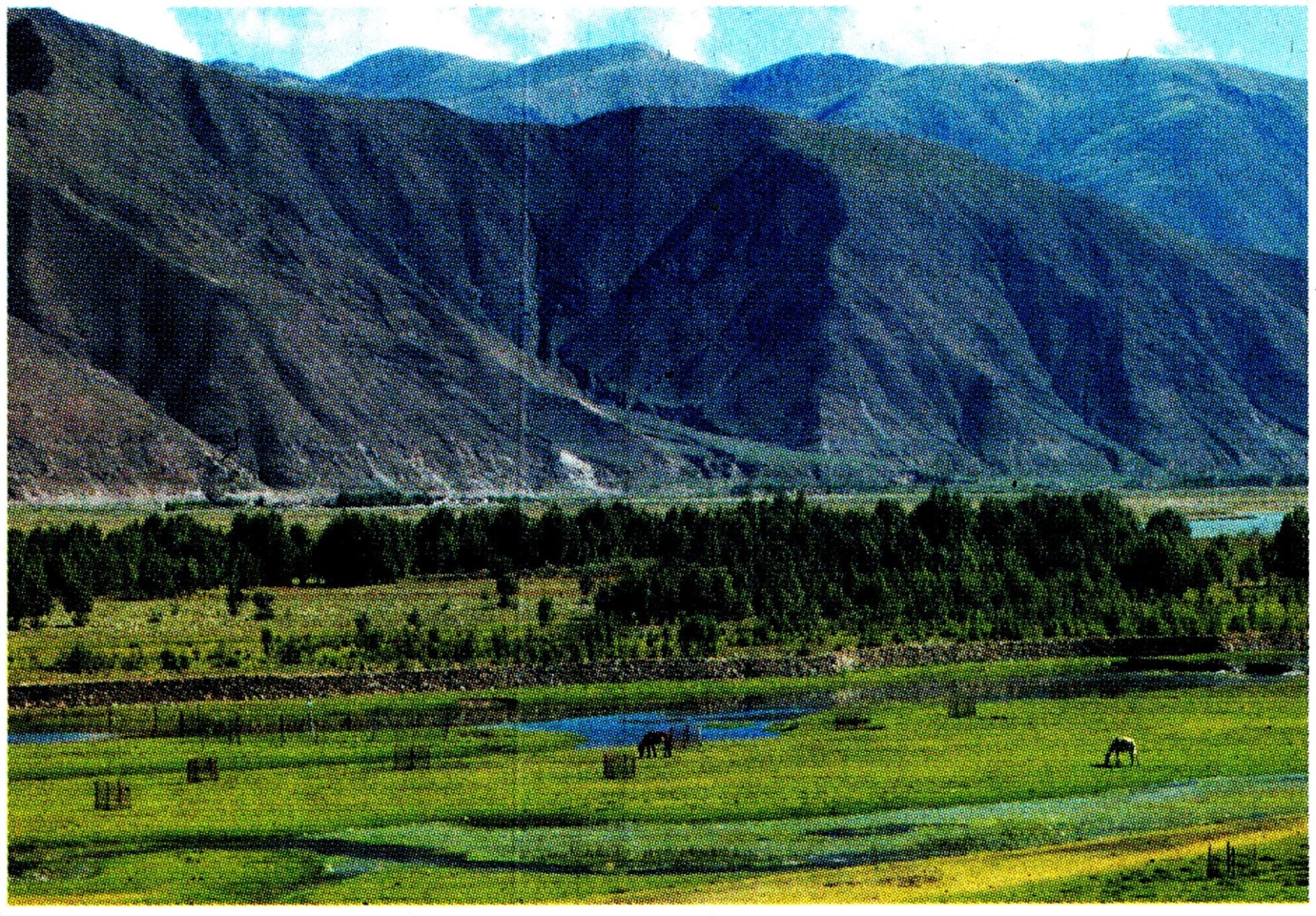文/周荣光
关中人喜面食,尤喜面条,以至于似乎山珍海味都比不上那碗面对自己的诱惑。
关中面条的特色是薄筋光、酸辣香、煎稀汪,用韭菜、葱花、木耳、黄花、豆腐、肉丁等炒成臊子与面相拌(或浇汤),色泽鲜艳,香辣可口,看一眼就食欲大增,不吃上三碗两碗就不算吃饱。有句顺口溜道: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儿女高唱秦腔,吃一碗黏面喜气洋洋,没有辣子嘟嘟囔囔。话未必全面,但足见面在关中人心中的地位之重。
关中乡间讲究无面不成席,有面好待客。红事白事,一碗面可以让亲戚朋友、全村老少吃个痛快。老辈人的话讲:娶媳妇要会擀面,说的是本色;送行的饺子接风的面,说的是惦念;祝寿要吃面,结婚要吃面,过节要吃面,大年三十要吃面,表达的是情怀;甚至小伙子感冒了都不吃药,吃一老碗酸汤面,再盖一床厚被子,美美睡一觉,捂上一身汗,起来就活蹦乱跳了。
面食的历史悠久。相传始皇帝灭六国统一天下,秦兵远征时背的干粮就是面做的锅盔;而大战凯旋,犒劳将士们的主食就是面条。自后稷教民稼穑以来,小麦一直是北方粮食的当家品种。在八百里秦川,小麦秋播夏收,冬去春来,历经四季风霜,吸纳天地精华,装点大千世界,滋养芸芸众生。可以说面食养育了北方,也养育了华夏民族。
对笔者,吃面则更有点特殊:当年成婚时,身为“老知青”,已经历了十年孤独。日日夜夜在广阔天地里劳作,无情的风雪吹硬了筋骨,简约的生活损坏了健康,时不时作痛的肠胃伴随着低血压和贫血。面对生活拮据,心灵手巧的妻子就把再普通不过的面条,当成我最基本的药物和补品。
至今忘不了那一幕:晌午,我拉着风箱,妻子忙碌在案板前,她右手和着面粉,左手端着碗清水,清水一点一点地往面里倒,手中的面粉也慢慢地成絮成团。面是揉出来的。妻子使劲地揉,汗水流下来顾不上擦,头发落下来顾不上撩,终将一团硬面揉软,擀薄。我最欣赏妻子切面的情景:她不是把擀开的面片叠起来切,而是把擀开的提起来能看过影子的薄面片摊开在案板上,再四折叠平,一手压着擀面杖,一手用刀沿着擀面杖来回划切。那切出的面条绵长、均匀,薄如蝉翼,细如丝线。滚水下锅,沸后捞出,入碗后调进葱花、香醋、红辣子油,吃着光滑、柔软、热火、有筋性,香极了……
吃着这面,不知不觉中胃病痊愈了,低血压、贫血消失了,面也由此成了我饮食中的最爱。以至于因事外出几日、几十日归来,哪怕是深夜,都要央求妻做碗面。如此,我才会真切地感受到:这是回到了自己的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