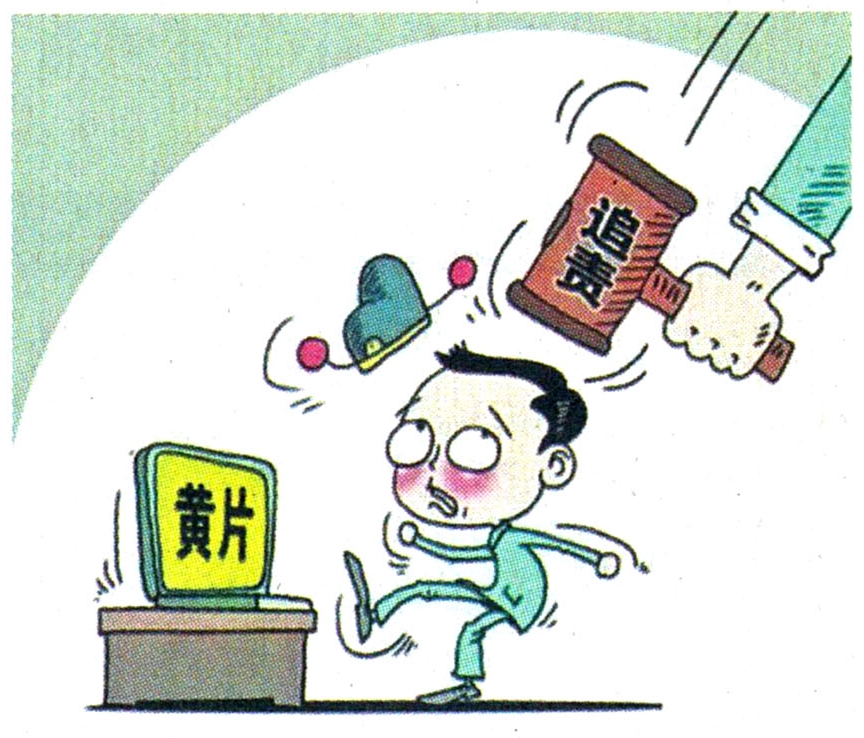1994年,莫言在北师大的硕士论文《超越故乡》中提出要建立高密东北乡的文学王国。他历数了许多作家关于故乡对创作的非同小可的意义,譬如海明威认为故乡是作家创作的“摇篮”,康·巴乌斯托夫斯基认为故乡是每个作家收到最重要的“馈赠”。但这些提法都没有莫言自己对故乡的感受那样富有感情内涵。他在论文中说:“作家的故乡不仅仅是父母之邦,……这地方有母亲生你时流出的血,这地方埋葬着你的祖先,这地方是你的‘血地’。”
真是一针见血的表述。
当然毋需说明,对于以再现人类感情和精神世界为己任的文学创作,这“血地”远不止是空间的、生理的概念,更是作家感情、个性、艺术视角和创作特色的“血地”,是作家整个精神生命和内部世界的“血地”。每位作家从自己的“血地”出发,此后无论行走多远,也许终生漂泊异乡,故乡都如血液永远流动在他的血管里,挥之不去地萦绕在他作品的字里行间。
陕西许多作家从故乡走出来,有的一直执着地写家乡这块土地,如陈忠实。有的,他们的人生,他们的作品也许早就超越了故乡,但只要稍稍究其故里,就无不可以感到“血地”执拗地存在,如贾平凹,如高建群。还有的,命运早就将他们和故乡剥离开来,在异乡生活了终生,他们在创作的初始曾经热忱地写过自己栖身已久的异乡生活,也写出了影响,到最后,当创作臻于成熟,却鬼使神差般殊途同归,重又“归家”,回到文学和人生的这块“血地”上来,精耕细作自己的家族和家乡。叶广芩由写秦巴山民到写京华的皇城望族,走的就是这条路子。此刻,摆在我们面前的《书香门第》,宣告了又一位老作家周矢也选择了这条路子。他们和其他走这条路子的作家们一道,实际构成了陕西作家队伍中一个还未被称为群体的群体。
我与周矢是几十年的老朋友,我知道他是旅居西安的江苏人,也知道他栖身于一个极有历史信息量和文化承载力的大户望族。因了同样长期生活在异乡文化之中,因了同是异乡游子,对他便一直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天然的亲切感。只是在匆匆交往中我们更多谈论的是彼此当下的生活状况和创作状况,也就多少忽略了对周矢异地生存心理和怀乡情绪的开掘、探究和感受。惭愧,我对他的内心世界其实是知之甚少的。
是《书香门第》这部作品打开了周矢,让我看到了秘不示人的另一个他。原来这个人(也包括我在内的这么一群人),可见的一面是在异乡的现实生活中为生存、为事业劳作拼博,不可见的一面,却是在思念中,在骨子里,在灵魂中,终生对他生命的原生“血地”不离不弃,终生在和那些记忆中的人用地道的乡音交流对话,和那些记忆中的事在灵魂中缠绕纠结。
现在时的异乡生存和过去时的原乡记忆终生切割着、撕裂着这群人,使他们比本土作家多了一层精神痛苦;当然也就多了一份文化感受和创作资源。游走于现实和忆念之间,多少会影响他们圆通无碍地介入当地生活,会影响他们感知遥远家乡鲜活的生活进程;但是异乡与原乡在比较中的融通,往往又能够构成创作中新的视觉和体验。在进行文化积累与审美表述时,他们可能部分地缺失了乡情、亲情和文化语境的依傍,这会增加创作的障碍;殊不知也往往会使记忆中的生活更个性化,更情绪化,更有距离所产生的美。
这是我读《书香门第》最强烈的感受。我发现了一位老朋友、老作家内心隐秘的归家情结和恋乡世界,其中有痛苦失落,也有自豪和自足。到了晚年,这块隐伏在记忆中的“血地”终于从血管中喷薄而出,以一个文字书写的艺术世界,展现于世人面前。这种发现兴奋着我的审美情绪。一路读来,痛苦着他的痛苦,失落着他的失落,也满足着他的满足。而且由不得从这个角度去探索作品的成败得失。
《书香门第》的结构很像周矢家乡小舟上抛出的渔网,从束在渔夫手里的一个网领,即三太太的晨骂,向生活的河面宽阔地撒开去。然后,细腻而有几分唠叨、自得中显出一点卖弄地开始铺陈苏北小城的民俗风情,鱼香,粪臭,市声,不离手的水烟筒与“纸芒子”,闹市般的刷马桶声,晨起必吃的鱼汤面和养油蛋,左手渔鼓右手锣、被小童用竹棍索引着穿巷而过的算命先生,节前少不了的祭祖、画糕、呈饭、锡箔“包子”……作者在描述中不能自己,我们也为作者的描述而陶醉。
在小城风情的展开中,那张结构性的渔网在水中渐次张开,情节、人物、背景从三个板块、两个层面向前推进。三个板块大致是石城家族、上海的匡仲非和军阀游勇杨家舍驻地这三地故事,传统家族、沪上生活和军阀混战在这三个板块中穿插展现。两个层面则是家、国相交错,时代风云、命运纠葛相纠缠。既在历史景深中浮现出匡家家族与抵抗扬州屠城的英雄史可法的血缘联系,又在三爹匡旭昌从军阀孙传芳残部手里义救小城的行为中,显示了匡家与史家相呼应的血性。
而当生活河流中鲜活的鱼儿纷纷网罗到这个结构中,作者开始收网了。在大年前大约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各条线索逐渐收束,终于在年关重又交织到了石城匡家大院,交织到了以晨骂开篇的三太太身边。这时,各路故事都临近了尾声,三太太最终停止了她的晨骂,驾鹤西归而去。留下的是历历在目的一群人物,一段传奇,还有无边的沧桑。
将“血地”话语作精深的文学性转化,以老到的文字从容地叙事、简约地点染心理,形成一种自如而又成熟的文学铺陈、晕染;却又组装进有起伏、有高潮、有悬念的戏剧之美中——周矢着实让我们领略了一回“姜还是老的辣”。他对这个家族哀其不幸、憾其不争却又炫其终于有为的复杂感情,对原生“血地”在心中压抑了一生又酿造了一生的爱恋,终于在审美层面得到了尽情倾诉。作者在这种倾诉中是那么舒心畅意,读者在领略审美愉悦的同时,也收割了一份沉沉的历史悲凉。
触接、辐射小说三个板块和两个层面的,主要是三个人物,这便是三爹、三太太和儿媳妇姜含之。三爹匡旭昌纵向承接了匡家、亦即史可法家族的精神,虽仍有一股血性,却因历史的远行,少了一点英雄气,多了一点乡绅味,很有点强弩之末了。三太太是横向辐射小说各个板块的人物,她处在转接各个场景、各个故事的三叉路口,像“交通警察”那样维系着小说的起承转合。
而作品最有活力的融接者,我以为应该是姜含之。她从精神和行动上传承了匡氏家族的内在力量,她的主见、泼辣、干练和担当,是那段混乱历史和那个破败家族难得的一抹亮色。她让我们感受到时代将变,家乡将变,传统家族形态将变的新信息,以及在这些变化中传统家族内部潜藏的更新自身的生命力。这时候,一种历史乐观主义和生命乐观主义油然在心中升起。 □肖云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