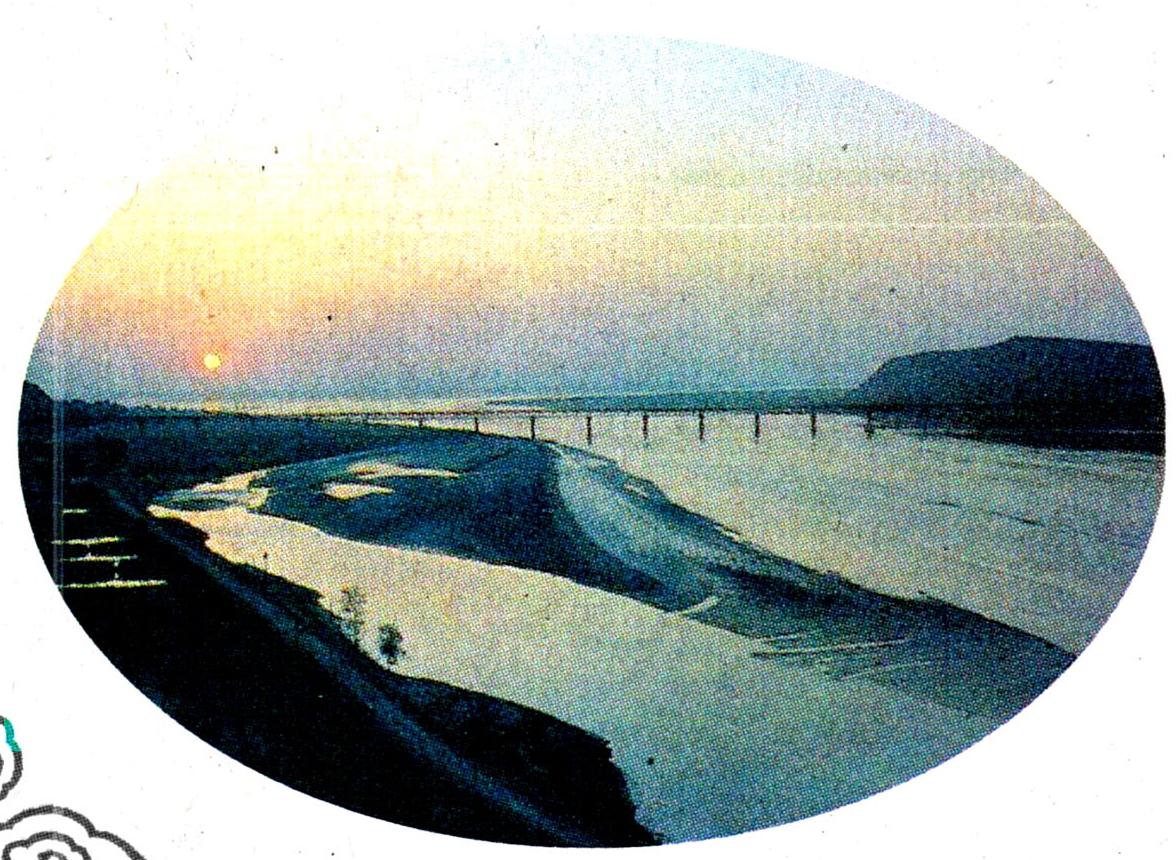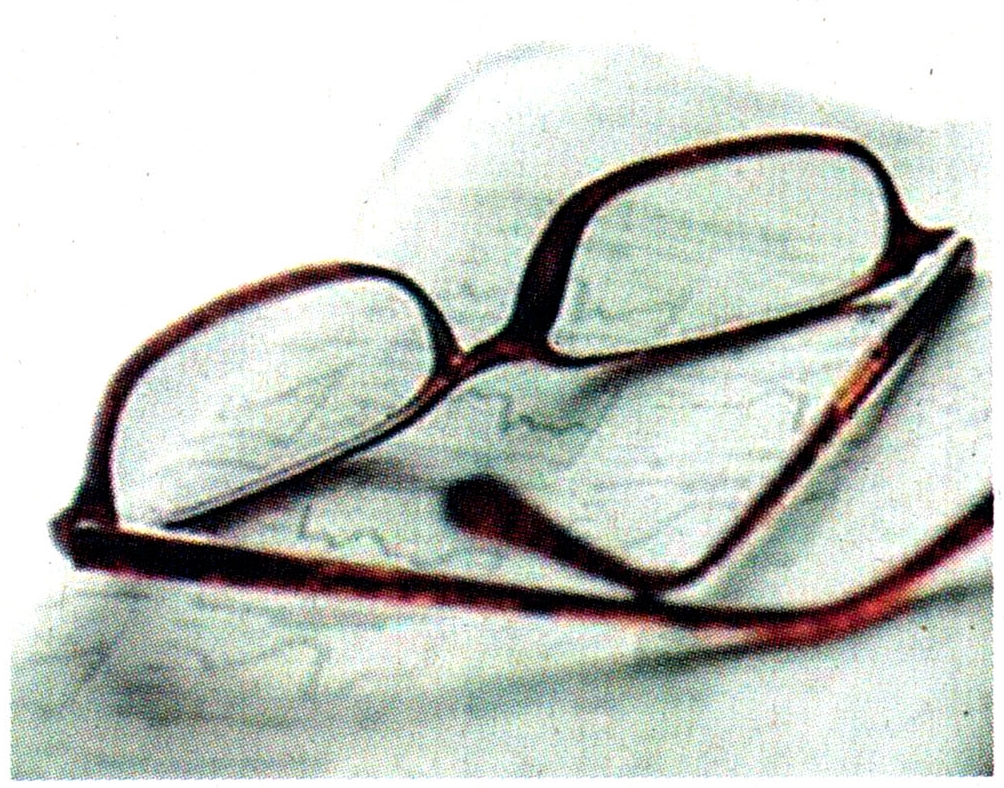◎张岩
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人们出入秦晋,要过潼关黄河,除了木船摆渡,再无其它逾越之方。1969年隆冬,刚满12岁的我,随全家响应政府号召回晋南老家时,就曾尝了一回“过潼关”的滋味。
那时,由西安到运城不通直达车,得先乘火车到潼关,下车后走一段路到黄河渡口,坐木船摆渡到对岸的风陵渡后再赶汽车到火车站,然后才能乘火车到运城。
那是我此生刻骨铭心的第一次乘火车、见黄河、坐木船。
绿皮蒸汽式火车,慢腾腾地跑了近5个钟头才到潼关。车还没有停稳,乘客们就争先恐后地往门口挤,我背着包袱领着弟弟,挤下火车出了站口,又紧随着母亲、姐姐急匆匆地往汽车站赶。走了不到二里地,六岁的弟弟就跑不动了,坐在路边耍起赖来,姐姐见状,忙将肩上的包袱交给我,背起弟弟往前赶。到了汽车站,只见停车场里几台绿颜色、高车帮、带布棚的卡车已发动起来,在一辆车跟前,母亲买了票,在工作人员帮助下,全家人爬上了拥挤的、开往码头的汽车。
码头上人头攒动,一片嘈杂。因为冬季是黄河的瘦水期,渡船靠不了岸,一艘大木船,远远地停在距岸边还有二三十米远的河面上,要由“背河人”把乘客一个一个背到渡船上。
船舱里人坐满了,老艄公站在船头手扶舵把吆喝一声“开船了!”随着一蒿一蒿的下水声,木船缓缓驶离了岸边。坐在船舷边的母亲,抱着三岁大的小妹,把她紧贴在胸口,生怕被风儿吹着,被水花溅着。我扶着船帮向外张望,只见浑黄的河水打着漩涡,一个接一个向后退去,心里虽然又惊又怕,却又觉得十分新奇刺激。
下船后,母亲又领着我们朝还有五里多地的火车站奔。崎岖的土路上,积满了黄尘,人走车碾过后铺天盖地般飘散开来,把人呛得喘不过气。到了风陵渡车站,都成土人了。全家人顾不得歇息,也顾不得拍拍身上的尘土,又赶紧挤着去买火车票,若赶不上这趟火车,下一趟就得到后半夜才有。等拿上火车票坐到车厢里,心里才踏实了,因为再过几个小时,火车就到运城了!
1970年6月潼关黄河铁路大桥建成以后,河面上再也看不见昔日那载客的小船和站在船头撑篙摆渡艄公们的身影,潼关古渡口随之消失了。再后来,风陵渡黄河公路大桥的建成通车,使秦晋两地人们的出行更加便捷,从西安到运城只需四五个小时,人们再也不用受当年那番旅途之苦了。
这些年,每当我一次次乘火车或坐汽车从黄河越过,儿时过潼关的情景总会在我的眼前浮现。作为一幅昔日的时代画面,它给我留下了无尽的回忆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