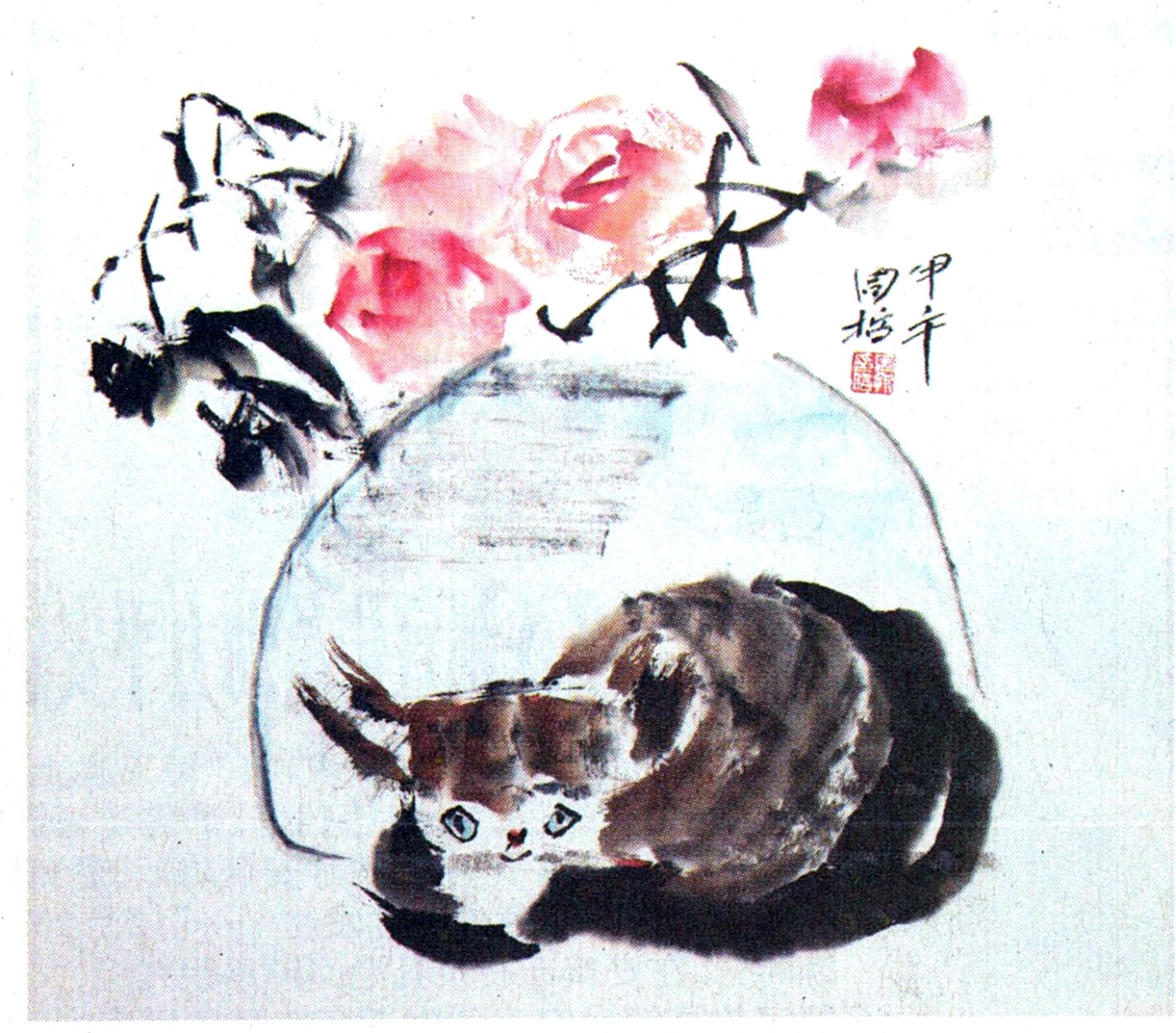□李思纯
我之所以一直称这小东西为小菜瓜,是因为小时候每每见到它都要问一遍父亲“这是什么?”他每次都不厌其烦地告诉我,“那是菜瓜子!”然后眼睛定定地看着小菜瓜,透出少有的喜爱,但在继续弯下腰之前却会补充一句:“没啥用!”
说是菜瓜,却怎么也没有瓜的样子,在我眼中顶多算个果球,甚至不及皮球大小。可是,我不知道为啥父亲看菜瓜的眼神比看我还多一份怜爱,不是没啥用吗?
多少年之后,当我领着女儿散步,无意中发现路边一株藤蔓上挂着几个黄澄澄圆溜溜的小东西时,面对自己莫名其妙的雀跃欢欣我才明白,作为一种没啥用的果实,它确实招人怜爱。
父亲还健在的时候,祖屋前后的苞谷地每年都套种着绿豆,有时也顺便给撒上一些黄瓜和南瓜的种子。第一次我发现这有趣的小东西时,父亲正躬身躲在苞谷叶子下面一边薅草一边给一个个硕大的南瓜翻身子。我惊讶地在父亲身后大叫:“你看这是啥?黄黄的,好好看!好像小西瓜哎,能不能吃?”父亲转过身来,微笑地摘下这个小东西放到我手上。“去耍!没用!菜瓜子!”说完,继续摆弄那些看起来比这小东西大很多很多倍的大南瓜。
黄黄的小东西躺在我小小的掌心,散发着诱人的光泽和淡淡的甜香。我伸出舌头舔了舔,一股和黄瓜差不多的味道直窜进鼻孔。但这么美的小东西让我实在不忍心咬破它。握着溜光椭圆的果球像得了天赐的宝,我对它充满了好奇,忍不住捏在手心里反复揉搓。小东西极具柔韧性,越搓越软,越搓香味越浓,搓到最后,它只剩下薄薄的一层带着脉络的皮肤,像是润湿了一般失去了刚刚的鲜色。隔着那一层衣,里面饱满的汁液和籽熟得快要迸裂出来。
而最终,我闻着满手的盈盈清香,把捏得蔫蔫的小东西当礼物送给了邻院的孩子。
小菜瓜青涩的时候,一枚枚裹着一层雾蒙蒙的绿,像极了冬瓜刚生出来的小弟弟。有纯的颜色,也有形同西瓜花纹的纹理,少了成熟果实的灵气,却也呆板得可爱。可是,如我一样的小顽童们通常也不会等到它长熟,只要看见,准是摘上一两个来带回家扔在屋角,想起来的时候顺便拾起来攥在手心里把玩。
这小东西仿佛很贪恋旧地,它第一年在哪里生长,第二年第三年过去,它还在同一个地方牵着长长的瓜蔓。虽然屡屡说它没用,但父亲除草时却并不拔掉它的根叶,不晓得是因为我们喜欢玩它的缘故还是父亲对土地上一瓜一果的怜惜。直到现在,苞谷地早已荒芜,父亲也已去世多年,我犹记得向晚的屋檐下最温情脉脉的一幕——他颤巍巍地摊开沾满泥巴的手,掌心上躺着两个澄黄的小菜瓜。一抬眼,是他慈爱的同我一样欢喜的笑。
后来有一次,我在书上看到小菜瓜的图片,分明就是它,却又分明有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名字——马匏。在我的感觉里,小菜瓜和马匏风马牛不相及,我根本接纳不了它有这么洋气的名字。可终归,我还是寻到了它的踪迹。水浒诗词《黄泥岗上卖酒肴》曾记载:“宋江河,浪滔天,打鱼的艄公把船翻,要问翻船咋回事,宋公屈死成神仙。梁山顶上挂乍草,金线岭上结马匏,黄泥岗上卖洒肴。”
在脑海里把这几句颠三倒四咀嚼多遍才猛然发觉,这哪是什么诗词呀,分明是山里顽童的歌谣嘛!“梁山顶上挂乍草,金线岭上结马匏”和我们当年吟唱的“凤凰山上野猪多,爬到树上摸雀雀”不就一个味儿吗?这点小小的发现,让我的童心重新定格到某个已经逝去的遥远年代,心想,这欢乐的小东西,顶着一个不沾边的洋名,还照样那么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