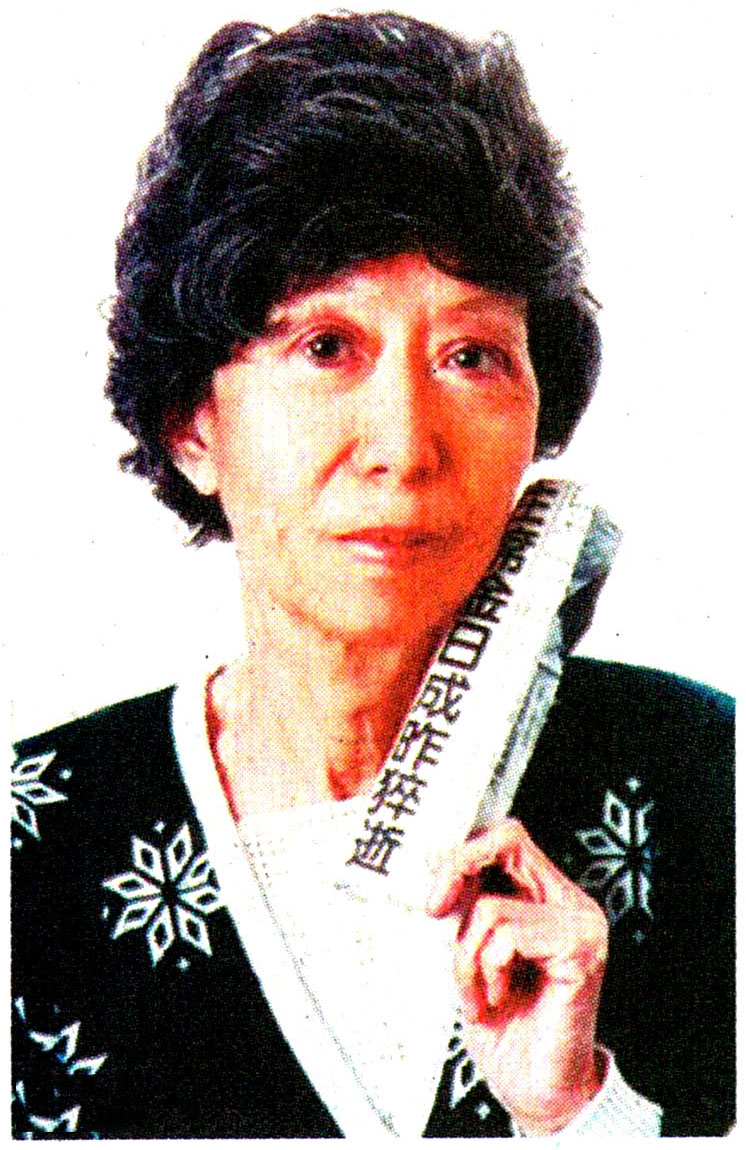
读张爱玲的小说时,不要在她小说中人物身上寻找作者的画像,不要在她的话语中寻找神秘的信息代码,相反,认认真真地追随着人物的行为举止、他们的言语、他们的思想,想象他们在眼前的模样。这其实也揭示了很多文学研究越来越无趣的缘由,他们将工作的研究中心放在了作家的私人生活中,而不是文学本身。电影《色,戒》上映后,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对剧中的人物角色对号入座。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恋爱史是文学研究者撰写八卦专栏的最佳谈资。张爱玲去世前的状态有着无数想象的版本。在我的印象里,至今为止,有关张爱玲的八卦和爱情史是众多《张爱玲传》版本的重点所在。而关于文学传记的写作,迄今为止并无一个靠谱的版本。
张爱玲的小说是华语写作的一支标杆,也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巅峰。二十世纪的小说家中,无论是论文字的雍容华丽,还是平淡自然,亦或人生苍凉,鲜有人能与其比肩。百年之后,只要还有中国文字,还有人欣赏文学,张爱玲就不会被人遗忘。
这绝非笔者个人的偏见,从夏志清的《现代小说史》开始,张爱玲的地位之尊彰显无疑。她也许有很多败笔之作,《小团圆》也罢,《少帅》也罢,但她的天才绝不会因为几篇败笔有丝毫影响。张爱玲作品之所以无人能够模仿和替代,首先是源于她独特的浸润中西文化的背景,其次是她独一无二的题材敏感度,她涉猎的题材大男性作家不会涉足,大多数女性作家嫌弃这种鸳鸯蝴蝶的模式,弃之唯恐不及。有评论家考证张爱玲阅读过丁玲的作品,那又怎么样呢?张爱玲绝对不会用丁玲的思维和语言写作,“革命加恋爱”,张爱玲只关心后者,而恋爱不是浅薄,是人生苍凉的底子。她说最妒忌的是林语堂:“从小妒忌林语堂,因为觉得他不配,他中文比英文好”。能够这样傲气点评别人,又不惹人反感让人说她小肚鸡肠的,也只有张爱玲了。张爱玲的好在于她把一个别的作家都写烂的恋爱题材化腐朽为神奇了。她的语言,她的思维方式,她对人心和人性的揣摩之细,让著作等身的作家也会感叹不已。
对一个作家而言,生活重要,还是写作重要?是否两者就无法取得平衡?根据宋淇的回忆,张爱玲在香港以翻译和写剧本为生,遇到翻译好的作家比如海明威还能享受一种类似写作的乐趣,但是遇到那些自己不喜欢的作家,硬着头皮翻译也是有苦说不出。比如翻译华盛顿·欧文的书,她就说:“好像同你不喜欢的人说话,无可奈何地,逃又逃不掉”。她后半生的写作并不顺利,远离了自己熟悉的世界,失去了自己的读者圈,张爱玲日益变成了一位西方文学圈的无名者。
无名者并非就是穷困潦倒的代名词,无名者有别人感受不到的快乐。张爱玲逝世后,很多人都觉得她在美国的晚年生活晚景凄凉,无人陪伴、家徒四壁。但宋以朗在《宋家客厅》中做了解释,张爱玲去世前在美国的银行账户中大概有28000美元,大概是20万港币,除去这些美国的账户。宋淇夫妇在香港一直帮她打理投资,大概有30多万港币,这笔钱当年并不是个小数目。所以说张爱玲晚景凄凉的人,大概是以己度人。
前不久读到一篇传记作家詹姆斯K·莱昂写的拜访张爱玲的文章更加佐证了这个想法。那是1971年,当时他对这位中国才女并不熟悉,拜访也是因为求证张爱玲的美国丈夫赖雅的一些生活片段。没想到张爱玲几次跟他提供赖雅的信息和书籍,他们几次亲切的交谈有效地打破她孤僻难缠的恶名,她给他留下了“一种与人为善、有高度社交经验的人方有的慷慨”的印象。在文章最后,莱昂总结的一句话让我印象难忘,他说张爱玲之所以离群索居,从人际关系中退出,是因为“她的挫败正在于无法找到能谈话的对象”。
写评论文章的,容易把习惯性吹嘘变成陈词滥调,天才就是最烂的词汇。尽管如此,在笔者心目中能够担当得起天才的华语作家也只有张爱玲。正如苏珊·桑塔格的说,阅读张爱玲,首先要反对阐释,因为阐释仅仅是庸人献给天才的恭维之辞。 □奋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