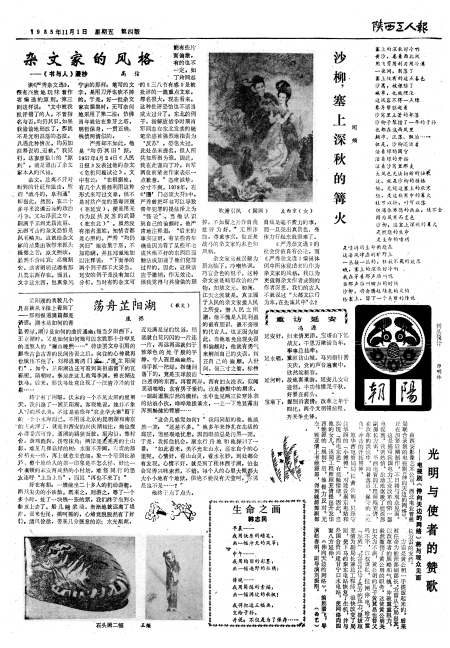杂文家的风格
——《书与人》漫抄
高信
读《严秀杂文选》,很有兴致地玩味着作者编选的原则。第三则这样说:“文中被我批评错了的人,不管指名与否,均仍其旧,如果我偷偷地删改了,那就不是光明磊落的态度。凡遇此种情况,均另加注释说明、道歉。”我觉得,这寥廖数行的“原则”,确是道出了杂文家本人的风格。
杂文,总离不开对时弊的针砭和狙击,所谓“战斗的、阜利通”即指此。然而,在三十多年来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文坛浮沉之中,圆满平正到光昌流丽、无懈可击的杂文恐怕是凤毛鳞角。这就给杂文家的结集出版带来抓头搔腮之苦:原文照收,显然不合时宜;忍痛割舍,读者明明记得有那儿篇东西存在。而且,文字这东西,也真象列宁讲的那样:笔写的文字,是用刀斧也砍不掉的。于是,好一批杂文家在编集时,无可奈何地采用了第二法:仿佛当年就钻在象牙之塔,明哲保身,一贯正确、钱债两清似的,
严秀却不如此,他是“均仍其旧”派。1957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过他的杂文《危机问题试论》,文中有云:“在根据地,有几个人曾经利用这种形式来写过文章,但不是对共产党的恶毒诬蔑(在延安),便是用来作为反共反苏的武器(在东北)”。虽然没有指名道姓,知情者都是心照的。严秀“均仍其旧”地收集于斯,不加隐瞒,并且郑重地加以注释说:“下面举的两个例子都不大妥当。延安的例子是没有加以分析,当时有的杂文可能有些片面偏激,有的也不一定,如丁玲同志的《三八节有感》是被批评的一篇重点文章,罪名很大,现在看来,这种批评恐怕也不适当或太过分了。东北的例子,指解放战争时期肖军同志在东北发表的随笔杂感被强烈地指责为
‘反苏’,恐也太过。此处虽未提名,但人所共知所指为谁。因此,我在此谨向丁玲,肖军两位前辈老作家表示一点歉意。”态度诚挚,分寸不爽。1979年,在《‘围’门必须大开》中,严秀曾把坏书可以导致青年犯罪的提法斥之为
“怪论”。当他认识到自己的偏颇时,他严肃地注释道:“后来的事实证明,有某些青年确是因为看了某些坏书或其他不好的东西后而触法或加速了他们犯罪过程的。因此,这段话应予撤销,作无效论。但我觉得与其偷偷的删掉,不如留之并作自我批评为好。”无所讳饰,尊重事实,也正是战斗的杂文家的本色和风格。
杂文家常被误解为居高临下,冷嘲热讽,巧言会色的棍子。这种杂文家是畸形政治的产物,如姚文元、初澜、江天之流就是。真正属于人民的杂文家爱人民之所爱,憎人民之所僧,他不愧是人民利益的最有胆识、最不旁顾的代言人。也正因为如此,当他难免出现失误和偏颇时,他就有勇气来解剖自己的失误,纠正自己的偏颇。人世间,借三寸之管,标榜自炫是毫不费力的事,而一旦亮出真货色、身体力行起来就很难了。
《严秀杂文选》的社会价值自有公论,而《严秀杂文选》编辑体例中所体现出来的作为杂文家的风格,我以为更值得杂文作者或别的作者深思。我们的古人不就说过“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么?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