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日本话今昔
陕西师范大学教师 阎明
一九八五年六月三十日,东京湾沿岸刚刚刮过一阵台风,接着是细雨潇潇。到了下午三时许,天气突然晴朗。中国民航国际航空班机载着三百二十多名中外旅客,徐徐地降落在日本东京成田机场。正当乘客们纷纷收拾行装、准备下机的时候,机舱内忽然传来机场事务室的日语广播: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阎明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阎明先生!欢迎您相隔四十八年再来日本。请您最后下飞机,东京电视台和各报社新闻记者以及您的新老朋友们在机场外迎候您。”
我大吃一惊!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可是,广播反复了两次,同机的乘客先是相互观望,最后一致把目光转向我。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啊!真没有想到,像我这样一个极其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师,此次白发盈颠,旧地重游,竟会受到这样的重视!我抑制住内心的激动,穿好出国前新作的中山服,佩戴着“陕西师范大学”校徽,紧跟在全机乘客之后,走出了机舱,脑子里却不由得回忆起许多往事……
(一) 那是在半个世纪以前,我还只有十八岁的时候,怀着青年人的雄心壮志,从上海登上日轮,去日本留学。我坐的是统舱,和二十多名中国学生躺在一起。只有三千吨位的“长崎丸”,迎着太平洋风浪,左右颠簸。我不停地呕吐,整整两天,凡乎咽不下一口饭。记得就在下船的时候,也传来过日语广播:“中国的罗集贤君,中国的罗集贤君!”我惊奇了,因为这位罗先生正是和我同去日本的陕西岐山县人,他的哥哥还是当时中国驻日本函馆领事馆的领事。然而,广播上呼喊他的名字,不是为了欢迎他,而是经船上登记检查,他的手续不全,不准入境。
在那个年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国家受人欺侮,个人也处处遭到卑视。在东京租房子住,很多出租房子(贷间)的挂牌上,常常附一句“内地人限”。所谓“内地人”,是指除了朝鲜、台湾等当时的日本殖民地以外的真正日本人。中国不是日本的殖民地,但中国人(当时被叫“支那人”)在日本所受的岐视,也基本上和朝鲜、台湾人差不多。“内地人限”就是只租给日本人,不租给朝鲜人、台湾人和大陆人。我幸而找到在东京杉并区阿佐谷一位叫柿崎的人家,将二楼六铺席子的房间租给我。
当年我去日本,投考了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我一面上学,一面和裘进、李肇嘉、李哲愚、李春潮、王克西、潘宗周、刘北天、黄一环(回国后改名黄鼐,是民主革命家黄兴最小的儿子)等数十名思想进步的留日同学,秘密组织“现代问题座谈会”(简称“现座”),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研究国内局势,在留日的中国学生中发展组织。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东京的左派中国留学生会,经过激烈辩沦,形成决议,号召全体留日同学,迅速回国;参加抗战。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我匆匆整装,由横浜乘美轮“日本皇后号”回国。船过长崎,我突然在甲板上发现由横浜秘密上船的郭沫若先生。那时候,他还只有四十开外,神采奕奕。在船上,郭沫若先生对我们说:“人常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而我是长期身陷虎穴,却丢下自己的几个虎子。”又说:“回国以后,我要放下笔杆,拿起枪杆,走上前线,我也可以打死几个敌人。”我们站在甲板上,瞭望就要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参加神圣的抗日战争,不由得心潮澎湃……
(二)
一别四十八年,经过漫长、艰难而又坎坷的道路,国家由受人侵侮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变成社会主义强国,个人由热情精壮、二十出头的青年变成白发苍苍、年近古稀的老人。今天,我还是穿着近似当年学生服的中山装(日本人叫“人民服”),又登上日本的国土……
在日本人看来,半个世纪前的老留日学生,再访故地,是一件带有历史性与故事性的社会新闻。一位很年轻的记者问我:“当年正在求学时期,为什么要中途辍学回国?”面对这位不到三十岁的记者,我笑笑说:“你是战后出生的,大约你的历史老师没有详细讲给你。当时的日本是帝国主义国家,对外实行侵略政策,强占我们的国土,屠杀我们的人民。芦沟桥事变以后,我国人民为了救亡图存,奋起抗战。我是中国青年,当然要辍学回国,保卫我们的国家。”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我说:“你们把这场战争笼统地叫‘日中战争’,这是不对的。从战争的性质来说,日本方面是侵略者,是非正义的,是只代表一部分军国主义者的利益而不代表全体日本人民利益的。战争对于日本来说,应当叫‘对华侵略战争’,而中国方面是被侵略者,是正义的,是代表全民族的利益,战争对于中国来说,是‘全民抗日战争’这才是实事求是的。”“现在,这已成为历史了,中日两国结为友好的邻邦,而且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三)
当年在东京求学时,我曾得到柿崎政信家和邻街住的风间家(柿崎政信的姑母家)很多关照,这次我即将去日的消息传到日本,柿崎政信抛开他正忙于筑波万国博览会上展销作品的工作,也赶到距东京市中心七十五公里外的成田机场来欢迎我。我们分别时,他才七岁,但从面貌上一看,他还是四十八年前那副样子,我们在机场上拥抱了。
一天,我回到四十八年前居住的阿佐谷。这里在战争中遭到严重轰炸,新建的街道己经完全变了样。但,阿佐谷车站的位置却仍在原址,只是比当年阔气多了。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忽然发现了紧靠车站旁的一所警察亭子(日语叫“交番所”)。啊!这不正是当年那所警察亭子吗!记得每天经过这个地方,我都有点心情紧张。因为那时坐在亭子里的警察,从早到晚老是面孔朝外,瞪着眼睛,注视每一个过路行人,行人随时都会被叫进去盘问。有一次,我手里拿着一卷日本报纸,里面却夹着从国内偷偷捎来的救国会抗日文件,经过这所警察亭时,也许心里有些紧张,竟然被“喂,喂”两声,叫进去盘问。情急生智,我把手中的报卷轻轻放在警察办公桌上,从口袋里取出贴有像片的明治大学学生证,简单回答了几句,警察放我走了,我又从容检起报卷,走进了阿佐谷车站。今天,我站在还是这所警察亭外的老地方,沉思良久……亭子里,穿着灰色警服,身挂报话机与手枪的年轻警官(比当年那个家伙漂亮得多)站起来了,他感到奇怪。这时,柿崎政信及T BS电视台的记者赶忙上前,向警官说明了我的身份及原委。于是,这位威风凛凛的警官立即露出笑容,很客气地请我进去休息,毕恭毕敬地向我敬礼。啊!时代不同了,我再不会受到欺凌和侮辱了,因为我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宾呵!
柿崎政信家的房子早被炸毁,地皮也转让给别人了,而风间家的房子却是这一带唯一幸免的。
我又来到这座日本式房子门口,按照日本习惯脱了鞋,通过走廊,进了我熟悉的那间“应接室”。一眼看到,老人家孤伶伶地坐在塔塔米(日本式房内铺的草席)上。我当学生的时候,她经常亲自作饭请我吃,我生病的时候,她的丈夫风间医生免费给我治疗。当年的风间大婶只有四十开外,看上去也还有些风韵,而现在却已经是九十二岁高龄的老人了。我急步上前,不由得用日语说了一句:“窝巴桑,塔达依马(大婶,我回来了)!”九十二岁的风间久老夫人,脱口而出回答了一句:“窝开爱利那塞(你回来了。”她流着眼泪,慈祥地拥抱着我,还用消瘦的手掌抚摸我的头发,仔细端祥着我的面孔说:“你也老了,可鼻子和眼睛还和当年一样。”老夫人的大女儿保志美代子比我大三岁,当年我离日时,她也只是二十多岁未婚的漂亮姑娘。现在,她满头白发。匆匆走来,竟然伸开双臂,流着热泪紧紧和我拥抱。在旁的新闻记者低声说:“这俩恐怕当年……”其实,在那个时代,我们青年男女,见面时多说几句话,彼此都害羞,谁还敢伸出手来握一握,远不像战后日本青年男女这样自由啊!
饭端上来了,几乎尽是生鱼片。四十八年了,我的胃口已不善于容下这些东西。然而,盛情难却,我还是以怀念的心情,一口一口咽了下去。老夫人还和当年一样,坐在饭桌旁不断地问:“怎么样?合你的口味吗?”我频频点头说:“好吃,好吃。”这一天,连跟踪前来的TBS电视台六、七个工作人员也都沾了光。
四十八年前,在日本这片土地上,我们被称为“支那人”而屡遭白眼。四十八年后,还是在这片土地上,我却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在我访问母校明治大学、京都教育大学、国学院大学及国立国语研究所、日本对华赠书会等单位时,处处受到远非昔比的礼遇。这使我深深体会到,个人所受到的荣誉,实质上是分享了国家的荣誉。国家的盛衰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血肉相连。
在我们重访日本归来、踏上国土的时候,面对庄严的五星红旗,我心海翻腾,思潮奔涌,我更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和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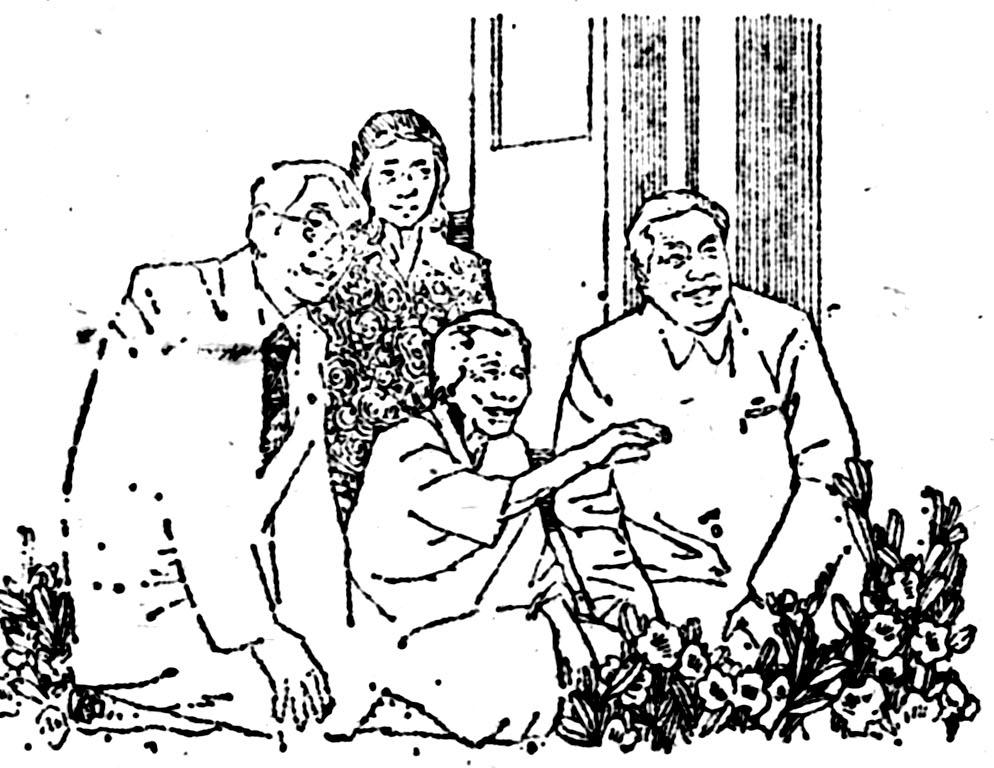

本版题图 插图 弛张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