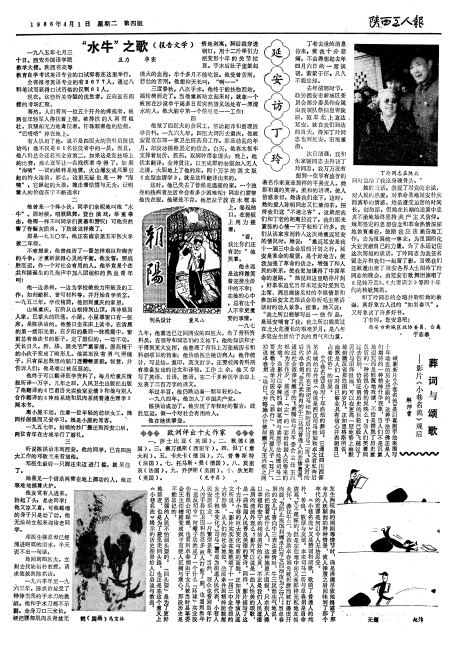“水牛”之歌(报告文学)且力 华实
一九八五年七月三十日。西安外国语学院教学大楼。陕西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英语专业的口试即将在这里举行。
全省报考英语专业的有2677人,通过八科笔试而获得口试资格的仅剩61人。
现在,这些斩关夺隘的优胜者,正向设在四楼的考场汇聚。蓦然,人们看到一位五十开外的瘫痪者,被两位年轻军人搀扶着上楼。被搀扶的人两臂粗壮,双腿却无力地耷拉着。汗珠顺着他的脸颊,“巴嗒嗒”掉在地上。
有人认出了他:这不是四医大的资料员陈拱诒吗!他不仅是61名佼佼者中的一员,而且,他八科总分还名列全省第二。如果这是竞技场上的比赛,那么亚军让一名残疾者夺得了。如果“海啸”一词的解释是地震、火山爆发或风暴引起的特大海浪,那么,这里无疑也是一种“海啸”,它掀起的大浪,撞击着怯懦与无为,证明着人的价值在于不断追求!
他曾是一个棒小伙,同学们亲昵地叫他“水牛”。那时候,唱歌跳舞,登台演戏,举重拳击,他哪一样不叫同学们羡慕和赞叹!可他突然害了脊髓灰质炎,下肢就这样瘫了。
那是一九五〇年,他正在南京第五军医大学读二年级。
不难想象,他曾经历了一番怎样艰巨和痛苦的斗争,才重新获得心灵的平衡。他发誓:要战胜厄运,作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他毕竟是个在共和国诞生的礼炮声中加入团组织的热血青年呵!
他一边养病,一边为学校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刻蜡板、誉写材料等,并开始自学俄文。一九五三年,学校精简,他回到重庆的家里。
山城重庆。石阶从山根排到山顶,再伸展到人家。巴掌大的院落。小屋。小屋靠窗口有一张床,是陈拱诒的。他整日坐在床上读书。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在夕阳的最后一抹晚霞中,窗前总有他读书的影子,定了型似的,一动不动。天长日久,胯、膝、踝关节严重挛缩。漂亮精干的小伙子变成了畸形儿。他甚至没有勇气照镜子,只有深思默想的脑门透露着坚毅,智慧,并告诉人们;他是难以被征服的。
他终于可以翻译医学资料了,每月给重庆情报所译一万字。几年之后,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他翻译的《巴甫洛夫实验室业绩》和他与别人合作翻译的《神经系统和肌肉系统普通生理学》两本书。
离小屋不远,住着一位年轻的纺织女工。她同样倔强而又爱学习。她是小屋的常客。
一九五七年,姑娘的纱厂搬迁到西安以后,两位青年在古城举行了婚礼。
三
听说陈拱诒来到西安,他的同学,已在四医大工作的邓敬兰来看望他。
邓医生最后一只脚还未迈进门槛,就呆住了。
她看见一个借助两臂在地上挪动的人,他正艰难地捅着火炉。
他发觉有人进来,抬起了头:是老同学!他又惊又喜,可他蜷缩的身子只是动了动,他无法站立起来迎接老同学。
邓医生强忍着已经涌进眼眶的泪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她回到四医大,立刻去找陆裕朴教授,请求他救救陈拱诒。
一九六零年至一九六三年,陈拱诒接受了铮铮雪亮的手术刀的挑战。他和手术刀都不示弱。全身刀口三米长,硬把腰部肌肉从骨盆无情地剥离,脚后跟穿进钢钉,用十二斤牵引力把变形十年的关节拉直。手术后肚子里鼓起很大的血泡,半个多月不能吃饭。他受着苦刑,悲壮的苦刑。他想仰天长叫:“啊——”
三度春秋,八次手术。他终于能扶物而站,摇轮椅而走了。当他重新站立起来时,就象一个被困在沙漠中干渴多日而突然望见远处有一潭清水的人,他大脑中第一个信号是——工作!
四
他做了四医大的合同工,帮助翻译和整理医学资料。一九六九年,四医大调防去重庆,他被安置在东郊一家卫生院药房工作。那是动乱的年月,却没动摇他坚定的信念。白天,他靠木框车支撑着划价、抓药,双脚肿得象馒头;晚上,他伏案翻译,全神贯注,以至成群的老鼠如入无人之境,大胆地上了他的床。四十万字的英文版《血型血清学》,就是这样翻译出来的。
这时,他已失去了曾经是温暖的家。一个独身的残疾者生活中会有多少困难呢?同志们要帮他洗衣服,他硬是不肯。他把盆子放在木框车上,卷起袖口,在搓板上用力搓着:
“看,我比你们还有劲!”他笑着。
他永远是这样微笑着迎接生活中的不幸!在他的心中,总有比个人不幸更重要的事情。
一九七九年,他重返已迁回西安的四医大,当了骨科资料员。在领导和同志们的支持下,他的知识和才干得到更大发挥,他整理了骨科上万张病历卡和科研项目的档案;他协助医生随访病人;他作统计、写总结、复印、英文打字,还要校阅骨科所有准备发出的论文和译稿。工作之余,他又学习了英语、日语、德语,在二十多种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三百万字的译文。
年过半百,他仍跳动着一颗年轻的心。
一九八四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陈拱诒成功了。他实现了年轻时的誓言:战胜厄运,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他在继续攀登。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