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在江岸
李佩芝
坐在岸边,一动不想动。岸在移、水在涌,心醉着。我觉出自己离水很近,很近,仿佛整颗心都浸透在江中,说不出的安然与妥贴。
岸呈出逶迤舒缓的曲线,上面绿的隆起,亦象天宇的岸。只是此刻,浓浓淡淡地暗了。
小时候,翻开地图,手指曾在那鸡冠上迟迟疑疑地移动,想不出大森林缠挟的江流是什么模样,如今,面对这条青黛色的大江,有种如愿以偿的欢乐了。
“为什么江水发黑呢?”
有人说河床下的泥沙是黑色的;有人说江水含有某种矿物质;有人说水深不可测……自已则以为,江水也同万种花木一般,造物主注入它灵魂的色泽后,显于人间的,便有蔚蓝、碧绿、清白、浊浑、黄褐与暗黛种种了。这条北疆的大河,另有一番钢铁般汉子的气概,在两岸苍苍的林木中,潇洒出一路的风流……朋友告诉我,黑龙江是铜帮,铁底,金镶边。我相信。看那岸上葳蕤的林木,淘金者的棚帷,我相信它是条宝河。它给这里的人们以财富,以精神,以寄托……
江水平静。漾出漩涡的波痕。船艇往来,呈扇形的浪花纹展开去,又互相撞碰,发出快活的絮语,荡到岸边的水波,润了五彩的卵石,又款款退去。
我到木排上去,放排的工人正围坐闲聊,木排边停着艘汽轮,显然已过了人撑篙子放排的岁月。和一老人拉起话,他说,收入是可观的,放一次排可收上千元。但从黑河市到上游呼玛县,往返半月余,如果现扎排,时间更长。江中日夜飘流,险滩、暗礁,还有难以预测的风暴,意想不到的事故……放排汉子难成家,女人不喜欢孤独与等待。他们高兴有钱花,但更注重感情,他们不愿担惊受怕,更忧心丈夫因寂寞而有了情人。老人现在退休了。“还上船么?”我问。“上惯了,总想江里跑……”这位二十岁时从安徽省乡间跑出来求生的放排人,击水几十年,他说,他离不开这条江了,当初乡里的恋妹子也是跟他几千里奔来的,如今都老了。“唉,不能上船了!”老人抽着烟,眸子盯在江面上,幽幽地叹道。我想,我理解这种痛苦,人生各有轨道,各有位置,不可偏离。
江岸愈发温柔了。夕照下,小城的人们纷纷涌向江边。江水晕着晚霞,泛出了半川的浓浓淡淡,深深浅浅的红色。女人们把江水搅得哗哗,象舞着他们人生的帆似的,把各色衣服都尽情地在江中洗,又摊晾在沙滩上,盘腿坐下,去望那水中快活的丈夫和孩子,脸上映出痴痴的笑来。我真羡慕他们,我以为这种江中洗衣的劳动本是女人的享乐呢,那岸上静静的凝眸,该是多么满足的人生……
黑龙江是不寂寞的。它是边陲的交通要道,江上常有客轮,货船往来,若与苏联的船相错,彼此也挥手致意一番。
说黑龙江是我们的内河,就是长长的历史了。复杂的史册上留下了民族的遗憾。听朋友讲,江两岸的村屯都相去不远,大小也不差上下。过去,从山东,河北一带闯关东的“盲流们”,常娶了对岸的俄罗斯姑娘,在江岸安下家,所以这一带常见些有异族色采的人呢。我心中充满了情感。闭上眼,能想象出一串串甜蜜又苦涩的故事,那是人类史上,民族之间不可或缺的心的相融。
江水拥着夕阳,红晕渗到岸边来。我想,只要跳下水去,一定能抚摸到她。我喜欢看日出日落。时间是立体的。几乎能触摸到。日出不常见,太懒。在泰山上,凌晨二点就披件大衣翘望,不谓不虔诚。但看见太阳时,她却在一片云海之上了。在戈壁滩上见过一次日出,天地一片火红,异样壮观。遗憾正坐在汽车里,变动的方向盘,使我能捕捉的光线有限。于是,我喜欢夕阳了,这里边有一丝享受,一丝安闲,斜依山亭,静坐村边,观望过多次暮色。在晚照里,静静地看那太阳,变得那么妩媚,新娘般,真的,新娘般,在投入大地的拥抱之前,显得异样甜美,羞涩…
江面上弥漫了一层柔薄的雾气,看不见云朵,太阳愈发红晕了。越落,越红,江水振颤,水中漾起一串火样的落影,漾起一串温存的诗句,大江燃烧了,举行了又一次辉煌的婚礼。
暮色深了,长长的堤上,闪出几星灯火了,那是临江的窗。其他地方渐渐沉入暗色里,做幽幽的梦去了。
对岸,路灯一盏盏地亮起来,桔红色,温柔地一排排映入江中,光柱长长地颤动着,象奇妙的琴键,无声的旋律在江中荡漾……江水绚丽而迷濛,仿佛融了两岸所有的光亮与天上的星辰,变得异常奇妙了。我突然悟到,人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能如此交融,如此和谐,应当感激这条青黛色的大江呢!
(题图 肖智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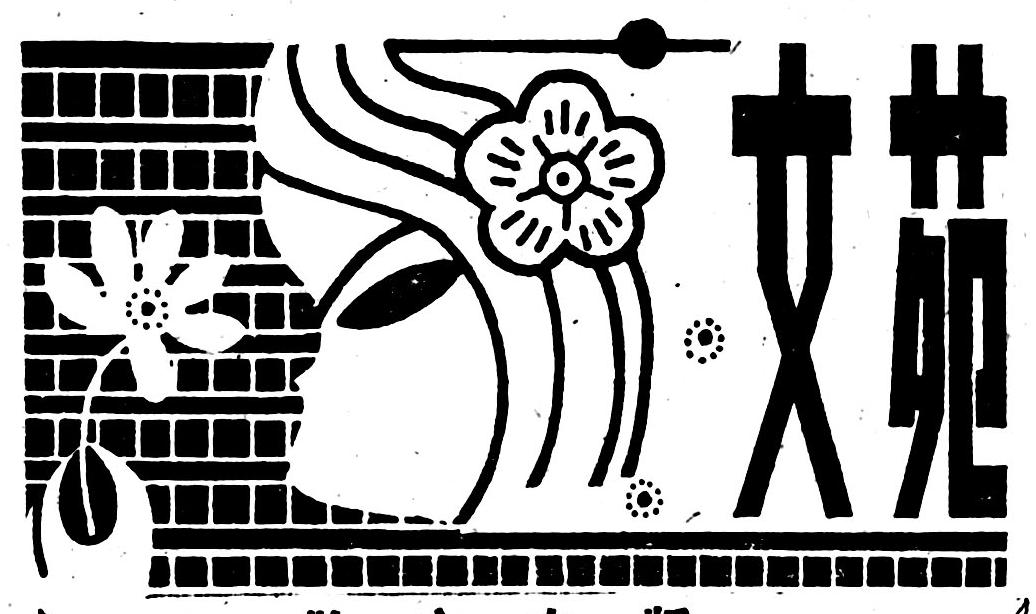
刊头设计武威 本版编辑叶广岑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