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陕北访油矿
徐岳
太阳在云里,云在树顶上,那么低,那么湿,那么冷,这是陕北十月的惯常天气。我被一辆越野车拉来了,
来了,也就来了,穿暖点,羊肉多吃点,一切也就平衡了。
黑色的油渣路,浑黄的延河水,总是相伴而行,它们的两边全是山。陕北的山,顶部是圆的,光秃秃的,或者全是石头,象绥德的油铉饼,一层一层。就在这样的路旁、河畔、山口子上,有星罗棋布的“磕头式”抽油泵,抽着那黑乎乎、粘乎乎的东西。那东西就叫石油,是从几百米,上千米的陕北土地下面抽上来的。油井旁有油池,池满了,有黄色大油罐车来拉。时有油罐车从我们的身边隆隆察过。 油矿的气氛已被这些东西渲染得够浓厚了。
西北有色金属公司是勘探有色金属的,在秦岭凤(县)太(白)地区,他们发现了大型铅锌矿,在潼关、洛南地区的小秦岭山里,又发现了藏量可观的金矿。那么他们为什么又参加到陕北的石油大战里来呢?难道石油也成了有色金属吗?不,西北有色金属公司在改革中开拓了第二产业,向延长油矿承包了打油井的任务,听这家公司那邓经理讲,“这是发挥我们的长处”。它们把三个队、四百多兵力投放到油井市场了。预计今年毛收入将达到三百多万,小车在延长县西门外的城关学校大院子里停下了。这里有“第一口油井”。它是1907年9月10日完成的,被称为“中国大陆上的第一口油头”。名日“延一井”。现在,雨雪霏霏中,磕头泵默默地立着,一动不动,象一位力气殆尽的老人,它的周围有绿色的铁栏杆保护着,成了游人望井兴叹、发端多种言词的对象。
我采访了另一个“第一口油井”、位于姚店镇,名曰“106”,它的年龄比“延一井”整整小了八十岁,磕头泵刷了新绿,正不停地,有节奏地向上抽油。
年轻的“106”井是怎样诞生的呢?
1986年6月,西北有色金属公司正在为开拓第二产业寻找项目,得到一个信息:延长油矿要对外承包钻井工程,公司便派人经多方考察,分几次与延长油矿管理局签订了十七万米的钻井合同。1987年8月,调了三个队的人马开赴陕北石油战场。从前,搞有色金属,他们是一支长着火眼金睛的硬汉子队伍,可是要搞石油,技术规模不一样了,还能硬起来吗?24米的井塔,象一个“铁睡佛”谁能让它立起来?270毫米的大钻,又有谁见过呢?就算这一切技术问题都不存在,那么,钻探石油的设备又在何处?资金又在哪里?就算有了钱,可是牛年马年才能拿到设备?“我们打过金,我们打过银,我们能打石油吗?”
公司派到这里的刘指挥、米指挥说,“陕北地下有油,地上有延安精神。我们靠自己,靠自己打第一口井。”“金打过,银打过,不信石油就打不出!”职工情绪活跃了,办培训班是一条,“偷技术”也是一条,这里有几家外单位的钻井队,人家来得早,他们抽空就去“串门子”,顺手就学。三个队“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一队很快出现了四个能人。被大家誉为“二孙二虎”,可借我只见了“六下四川”的孙绍基,中等个儿。衣帽整洁,给人第一眼的印象:这是个精打细算的人!他买了川东油矿积压的旧设备,自己又设计制造了井塔。所以,在三个队中,他们投资最少,效益最高。
胳膊粗的麻绳,一头栓在24米高的A型铁塔上,另一头交给了他们的手和肩膀,四十多名黑铁塔似的壮汉,一个个虎视眈眈,按着统一的指挥,在钻机的配合下,去年8月23日在—阵生命的吼叫中,西北有色金属公司在陕北的土地上竖起了第一座井塔。
立起一座井塔,也立稳了所有人的心。
历经三十九天以后,“第一口油井”打成了,命为“106井”,它深250米,是“延一井”深度的三倍,日产油12吨,“延一井”的最高日产量是1250公斤。1949年,延长油矿产量是800吨。干枯的数字,却能引人深深地思索啊!有了第一口,也就有了第二口。有了一个三井队,也就有了许许多多个“三井队”。指挥部打井60多眼,共计32100米。1987年,给本公司上缴纯利润17万元,各队又还了25万元的贷款。
据记载“延一井”所产石油,当年运销西安后,炯微光白,一时“誊誉社会,振奋人心。”从那次“振奋人心”到于今,八十六年矣!由此,使我感到西北有色金属公司开发“二产”的意义更加深远,“陕北的石油,是振兴陕北的第一只‘拳头’。它是打掉贫穷这个恶魔的最有力的拳头。”车朝西安飞驰,我从车窗里望着刷了新绿的磕头泵,这么想,快到黄陵时,看见满山绿森森的松柏,我还这么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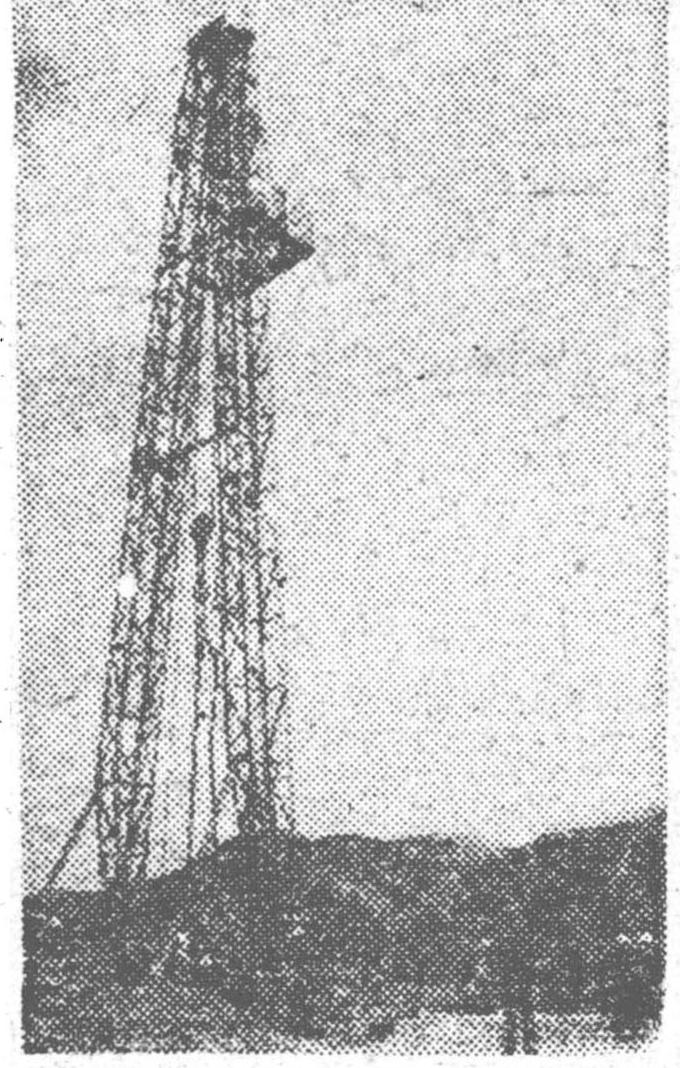
耸入云霄的石油钻塔
王军升撮
“精雕细凿”与“信手拈来”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