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班车临发(报告文学)
陈乃霞
报话大楼上的钟清脆地五响,西安城沉睡在温暖的被窝里。
住在电车一场职工招待所的董凤琴“啊”地一声爬起来,先敲李玲的门,又去喊贺景云,她们都是售票员。匆匆忙忙的脚步声,洗嗽声把一座楼惊醒了,
李玲当售票员一年多了,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早晨五点起床,真累,真想美美睡一觉,到我睡得不想睡的时候,然后,慢悠悠地去刷牙,去洗脸,去梳头,去喝一碗稀饭……”她的这点愿望不过分,但实现不了,在公共车上做售票员,一辈子也实现不了,在电车一场,起早摸黑已不惊奇,大家都惯了,开“交通车”的三点钟就发车了。场里房子少,司乘人员散住在西安市,最远的职工几十里,近的也在三、四站路之外。赶早班,交通车要把他们挨家挨户接进场里。
李玲、董凤琴、贺景云这些姑娘,是胆子小,还是责任心,都花钱在场待招所租一张床位,滚了一年,李玲也象电视上出现过的李苗、侯毅华一样,成了全省公交系统先进个人。
热情开朗的董凤琴比李玲早两年进场,是西安市公交公司先进,问她当售票员为了什么?她说不清楚,谁都说不清楚。她们的书记张志科有一句话说得还有些意思:“售票员,是受气员。”董凤琴她们也许就是为了“受气”来的。
瘦弱的张桂云丈夫常年不在家,上有公婆,下有孩子,大孩子一场脑炎,成了痴呆。她家离场远,在莲湖路的一条深巷里,赶早班车售票,她四点钟就起床,安顿了老的,安顿小的,火炉焖上早餐的稀饭,这才出巷。一下班便要去挑水,水管离家150米;要给老人和孩子看病;要上自由市场买菜打酱油醋……
也就是她,把车厢当成了乘客之家,去年六月的一天,外地一位残疾人上了张桂云的车,她在拥挤的人群里再三动员,给残疾人安排了座位;下车时,又扶他下去……残疾人感动得流泪了。“不容易,真不容易。”当过兵,当过售票员的司机高军攥着拳头说:“他妈的干售票这一行算是撞了鬼了!打不出名堂,就当孙子去!”
高军说的是气话,也是实话。系着红纱巾的桑兰英,在家是老小,爹妈护着,哥姐让着,要啥给啥,几分钱在她眼里算什么?可当了售票员,她就得与五分、一毛的小钱打交道。交道打得不好,得吵;吵得不好,还要挨打。
电车一场做为公交企业中罕见的盈利单位,就是靠姑娘们吵吵打打赢来的。
去年,司乘人员无辜挨打四十七起,司机陈学礼从火车站回返,到菊花园站,遭到路边闲谝的四个青年的围打。最要命的一拳,打碎了他的眼镜,玻璃碎片刺伤了眼睛,眼角膜也破了,进医院缝了十六针。可气的是打人者至今却找不到。
在这一点上,还是高军有办法,他认识三路电车线上的“大流氓”“小流氓”,这是“打”出来的。他当售票时不在班上,就一一去“拜访”他们。他打出了一条线。因此,和他在一个车上的女售票员就少了许多麻烦,当售票员还得练拳,什么事儿呀!
大概受这件事的启发,场部开展了沿途军、民、警、厂、站共建文明线路活动,收效是喜人的。有几家企业愿意出资修建候车亭十四座。
刚二十岁的贺景云也有委屈,不是挨打挨骂的事,她是个爱美的姑娘,哪个夏天,不买条裙子?裙子一一试过了,条条漂亮。但她不能穿,这是工作条例当售票员就得牺牲“爱美心”,这毫不含糊。
“309、出车”
调度室准时发出指令。“309”是张桂云的车,她急匆匆奔向车厢,脚步把纷杂的思绪踏在了地下。
李玲、董凤琴、贺景云向将发的384、382、329号电车走去,她们都年轻,脚步轻快富有弹力。
她们回头看见执外勤的张启成拿着步话机从调度室出来。他昨晚又没有回家。
早班车发动了,夜的宁静被雪亮的车灯撕开。 (摄影 柳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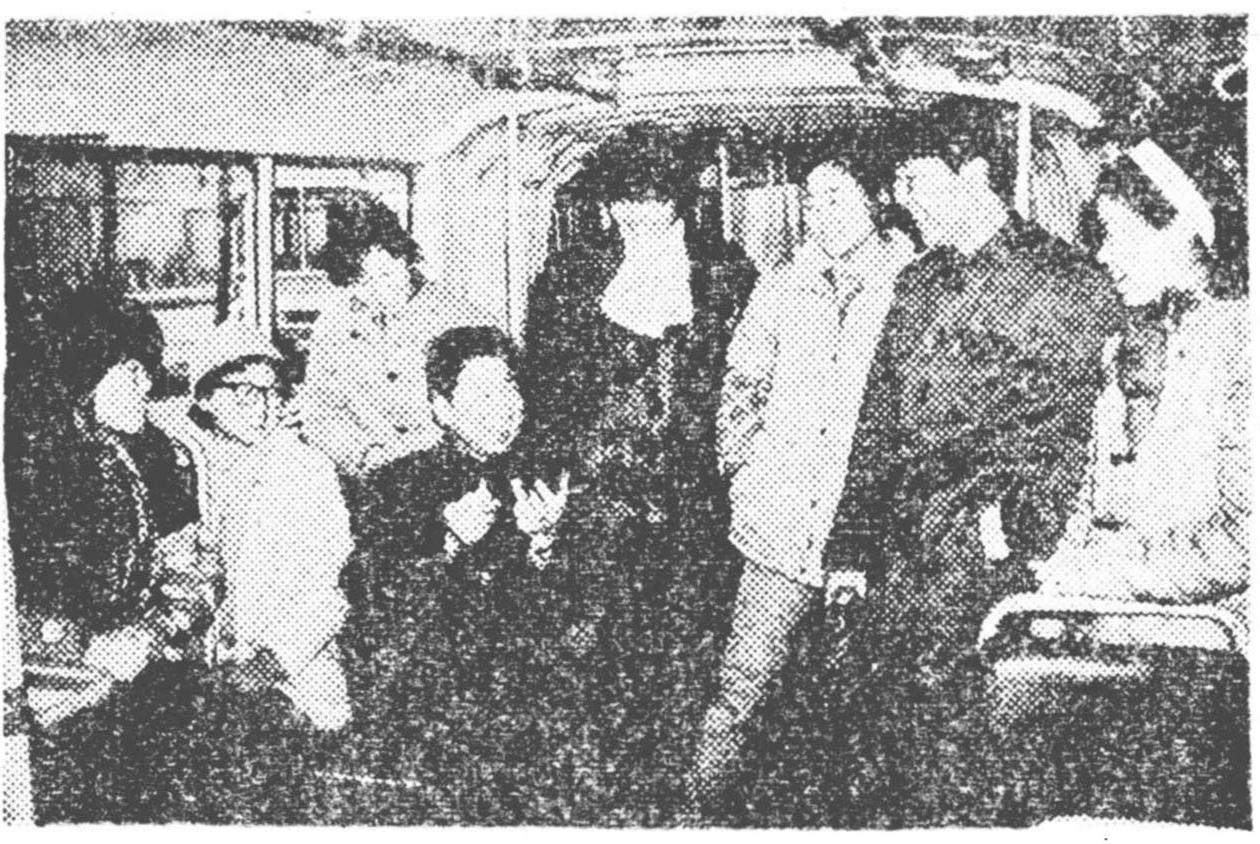
本版编辑 叶广芩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