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发室掠影
溪柳
说小,这地方确实小,整个房间仅有那么十个平方米不到;
说少,这儿的主人也确实少,在近五位数人员的大企业里,他们只给末尾数增添一个
“2”。
然而,这地方却又很大,《人民日报》、《工人日报》、《解放军报》,还有《环球》、《世界博览》等等,在这儿每天可以出入数千份。中央的、国务院的、机械委的函件,拉萨、深圳、香港乃至巴黎、伦敦、加里福尼亚的“青鸟”,都得在此“屈尊下驾”;
然而,这地方的人又很多,一封信权作一人吧,每天便少则数十“人”,多则上百“人”在这儿汇集,还不算那各部门取信报的文书。
“哎,收发室的!”有些人也许会不屑一顾。对喽,一辆闸不灵、铃不响的单车,外加一辆骑上就跳“迪斯科”的黄鱼车,每天两趟,厂门——邮局,邮局——厂门。风霜、雨雪、酷暑、严寒,乃大自然之变化也,与我何干?365天的日历牌上,在他(她)的眼里,全是黑色。“一车间,十五份”,“二车间,三十份”……声出手到,中药柜似的格子,闭着眼睛也投得准,就象闭着眼睛吃饭而不会喂给鼻子一样。
单调吗?年年、月月、天天、时时,收、发,发、收;
无聊吗?转一个圈是邮局,拧一下身是收发室,一刻也不许离人,一刻也不愿离人。
“多亏了您,要不是您将电报送到我家,母亲就见不到我最后一眼了。”
“请吃喜糖,我那该死的,信皮也写不清楚,若不是您寻问到了,准得吹灯拔蜡。”
单调、无聊、怨气、烦躁,在这诚挚的话语中,顿时烟消云散,并且愈加有滋有味地干着。
他是当过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的罗治全;他是走上收发岗位时间不太久的侯俊侠——恕我椤嗦,因为他俩虽未必认识全厂职工,但全厂职工却大都知道他俩。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两位人物平时虽不起眼,但若“停业”几天你想想是何情景。
(沈宇 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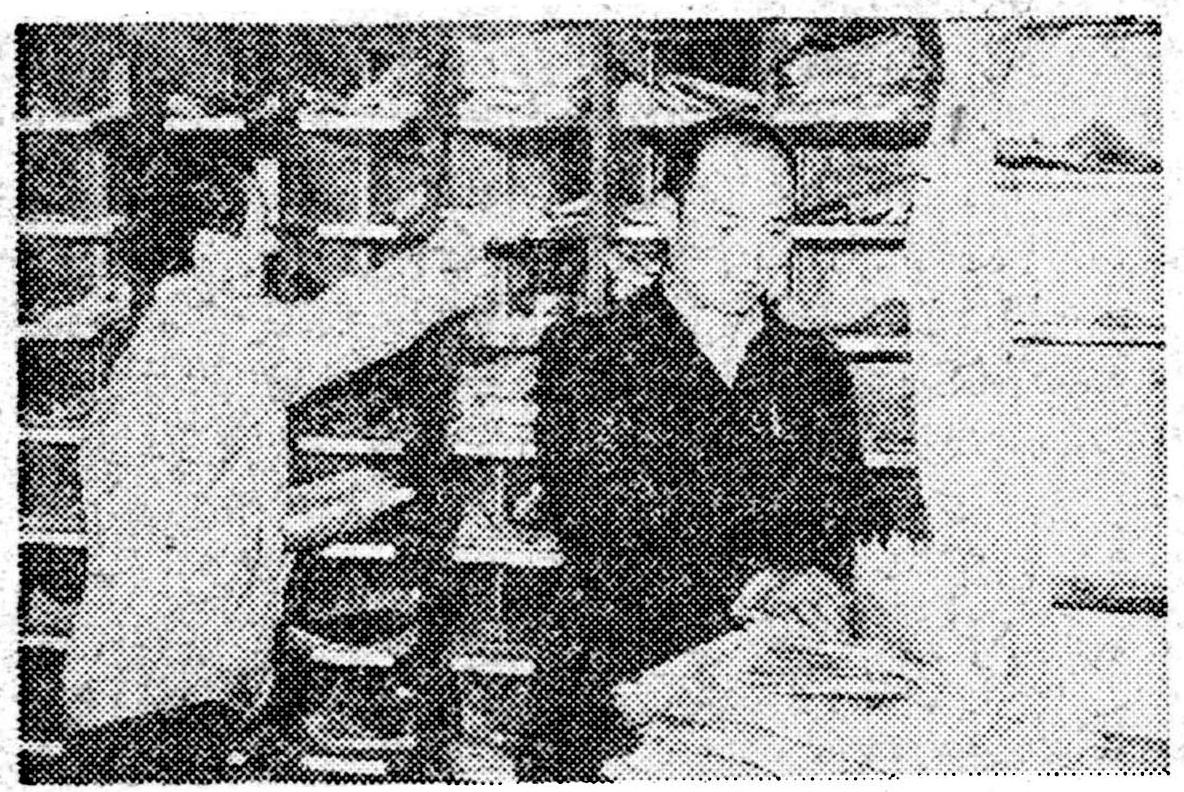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