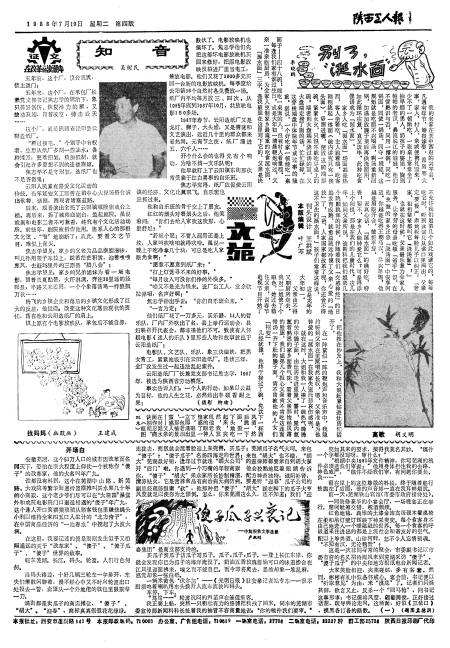别了,“涎水面”
李晓鹏
我的老家在关中西府的兴平县。凡遇有年节、婚丧嫁娶、盖房等大事,家人、村人、亲戚便携礼而来,少不了一顿面吃,一张桌上常常坐了抽旱烟的男人,奶孩子的婆娘,胸别帕帕的老汉,鼻流长江的娃娃。他们不管熟识与否,同用一撂碗,同吃一锅面,同使一锅汤,同守一规矩。这规矩就是吃面不兴喝汤,剩汤重新回锅,加温加放臊子菜后再供浇面用,如此循环往复,直至饭毕。此种吃食俚语戏为“涎水面”。
家乡人吃“涎水面”场面甚是热烈,客人坐着吃,主人跑着端。吃客刚刚挑起一绺面(碗内讲究只有一筷头面),吸溜进嘴,便放这碗端那碗,紧紧火火,只恨不能吃尽桌上的碗;端者则大盘端来浇过汤的面,又大盘端走捞了面的汤,忙忙碌碌,在这穿梭端盘中体味年节或过事的隆重。据说,一个好吃家一顿能吃一桌面子——四十八碗!能吃一桌面的人,很被村人看重哩,
每逢我们家有谁过生日,或是大年初一清晨鞭炮响过,父亲一准亲临厨房,为全家人烹制家乡最隆重的吃食涎水面,
“涎水面”三字,是我破胆在这里写下它的、父亲是决不允许我们姐弟几个如此戏谑它的。每每吃它时,听到这词儿从谁口里溜出,父亲定要极严肃地板着脸儿予以纠正:“老家,祖祖辈辈都叫它‘浇汤面’!”
也就在这时候,父亲最乐意为全家人服务,让辛劳的母亲吃顿“省手”饭,在他烹做的家乡正宗“浇汤面”中安享闲适。你越是吃得王朝马汉,尽兴尽饱,他越是眉眼开合,皱折平复。
说真心话,“涎水面”的确好吃,特香!要不,家乡人能钟爱它么?可是得添上个前提,那是在我们的儿童时代。这几年,如同父亲所说,迪斯科把我们姐弟几个跳颠跳浑的时候,伴随着我们“交感神经”的日趋发育成熟,就愈益疏远冷漠了父亲心爱的“绝技”了。“爸,人家国家都改革了呢,你还舍不得这不卫生的涎水面。”孩子们常常这样说。
这是龙年的大年初一。
父亲由不得又朝厨房走去。我对二姐使了个眼色,她过去稳住父亲,说春节电视节目开始了,把他按在沙发上。我和大姐赶紧钻进灶房忙活开了。
在一阵紧似一阵的鞭炮声和音乐声中,我隐约听到父亲在里屋喟然长叹。嗯,父亲准是为他钟爱的“涎水面”在我家失宠而悲哀伤感呢。
就在这时,大姐和我一人捧了一碗热气腾腾的关中臊子面,由灶房走进里屋。霎时,屋内氤氲着熟悉的家乡面香气味。看着父亲那饱经风霜的脸庞,我们姐弟几个担心父亲肯不肯吃这连面带汤一齐下肚的臊子面,肯不肯被他的儿女们“招安”?
几经犹豫,他终于接过了碗,先饮下一杯西凤酒,然后挑一下面,歪一下头地吃起来,突然,我发现他老人家的眼神惶惑了一下,眼里立即涌出一包老泪,那情景蛮感人的——父亲在对涎水面作忍痛诀别呢。
(题图双木)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