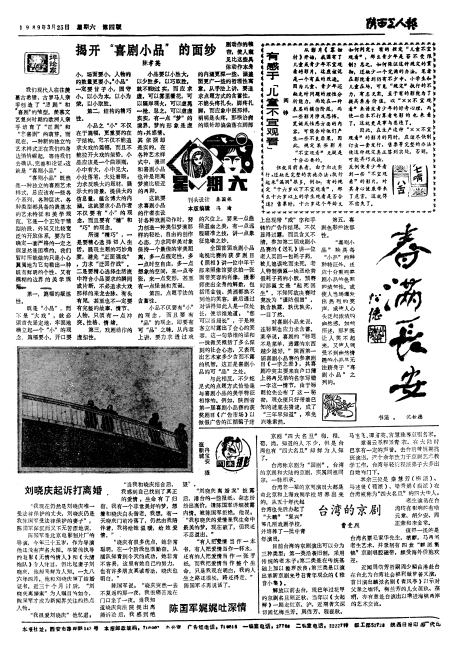揭开“喜剧小品”的面纱
陈孝英
我们现代人往往羡慕古希腊、古罗马人亲手创造了“悲剧”和“喜剧”的雏型,羡慕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亲手培育了“正剧”和“悲喜剧”的萌芽。而现在,一种新的独立的艺术样式正在我们的身边悄悄崛起,等待我们去确认、完善和论证,这就是“喜剧小品”。
“喜剧小品”既然是一种独立的喜剧艺术样式,总应该有一些各个系列、各种层次、各种类型都具备的最基本的艺术特征和美学规范。它是一个正处于雏型阶段、外延又比较宽泛的开放体系,要为它确定一套严格的一定之规显然是困难的,我们暂时所能做的只是小心翼翼地为它勾勒出一种既有鲜明的个性、又有模糊的边界的美学规范。
第一,篇幅的凝炼性。
既是“小品”,而不是“大戏”,就必须首先坚定地、牢固地确立起一个“小”的观念。篇幅要小,开口要小,场面要小,人物的的数量更要小。“小品”一定要甘子小,固守小,以小为本,以小为荣,以小取胜。
第二,结构的精巧性。
小品之“小”不仅在于篇幅,更重要的在于结构。它不仅不能追求大戏的篇幅,而且不能拉开大戏的架势。小品应该是一个曲颈瓶,小中有大,小中见大,小处落笔,大处着眼;力求反映大的题材,展示大的背景,提供大的信息量,蕴含博大的内涵,这就要求小品作者不仅要有“小”的观念,而且要有“精”和“巧”的观念。
所谓“精巧”,一是要精心选择切入生活,展现主题的巧妙角度,避免“正面强攻”,力求“迂回作战”。二是要精心选择生活流中符合小品要求的瞬间或片断,不必追求大戏那样的来龙去脉、有头有尾,甚至也不一定要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人物,只须有一点冲突、性格、情绪。
第三,戏剧动作的虚拟性。
小品要以小胜大,以少胜多,以巧取胜,就不能过实,而应求虚。可以雾里看花,可以隔岸观火,可以虚晃一枪。总之,可以虚虚实实,有一点“梦”的境界。梦的形象是虚的,其感情、其依据却是实的。在各种艺术样式中,漫画。和喜剧小品也许是距离梦境比较近的两种。
这就要求喜剧小品的作者在设计各种戏剧动作时,努力创造一种类似梦境那样的轻松、自由的创作心态,力求同审美对象保持一个最佳的审美距离,多一点假定性,多一点时空自由,多一点想象的空间,来一点夸张,来一点变形,甚至有一点怪诞和荒诞。
第四,点题手法的含蓄性。
小品不仅要有“小”的观念,而且要有“品”的观念,即要有可“品”之味。从内容上讲,要力求透过戏剧动作的帷帘,使人窺见比这些具体动作本身的内涵更深一些、涵盖面更广一些的哲理性寓意。从手法上讲,要追求点题方式的含蓄性,不能头疼扎头,脚疼扎脚,而应象中医那样,明明是头疼,那根治病的银针却偏偏落在脚部的穴位上,要来一点曲径道幽之美,有一点远程瞄准之技,讲一点象征隐喻之妙。
全国首届戏剧小品电视比赛的获奖剧目《照相》讲一位中年干部来照像馆要求拍一张面带笑容的肖像,摄影师使出全身的解数,包括用金钱、美酒都换不到他的笑容,最后通过对话得知此人是一位处长,便恭维地道:“您可以当局长”,于是顾客立时露出了会心的笑容。这一句恭维的话和一抹微笑概括了多么深刻的社会心态,又表现出艺术家多少含而不露的机智。这正是喜剧小品的可“品”之处。
与此相反,不少蛇足式的点题方式恰恰是与喜剧小品的美学特征相悖的。例如,陕西省第一届喜剧小品赛的获奖剧目《广告市场》以做假广告的江湖骗子背上出现带“戒”字和手铐的广告作结尾,不仅显得过露,而且含义不清。参加第二届戏剧小品赛的《送礼》讲一位老人买回一包耗子药,被儿媳误吃而未死,老人特制横匾一块送给卖假耗子药的小贩,预赛时那匾文是“起死回生”,不知何故决赛时竟改为“谨防假冒”,孰含孰露,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对喜剧小品来说,连标题也应力求含蓄。莱辛说:喜剧的“标题不是菜单,透露的东西越少越好。”陕西第一届喜剧小品赛的参寨剧目《一字之差》,其喜剧冲突主要来自户口簿上将两兄弟的名字写错一字这一情节,由于标题抢先公布了这一秘密,观众便只好带着已知的谜底去猜谜,成了“三年早知道”,难免兴味索然。
第五,喜剧色彩的浓郁性。
“喜剧小品”除具备“小品”的种种特征外,还应十分重视喜剧小品的色彩的浓郁性。或使人当场爆发出热烈的笑声,或使人心头泛起浓浓的幽然感,如前所述,那利既让人笑不起来,又使人领受不到幽然情趣的小品是无法跻身于“喜剧小品”之列的。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