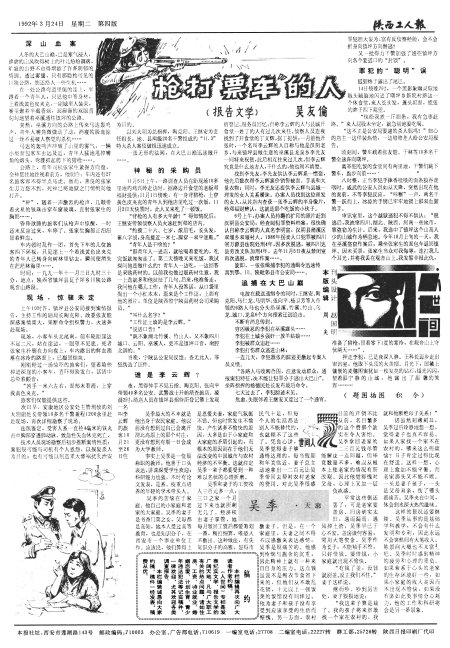吴季
天廓
吴季最大的不幸就是他出身于农民家庭。他以前没有想到过自己会离开渭北高原上的那个村庄,更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成为大学教师。
事实上吴季是一位很称职的教师,他善于口头表达,讲课深受学生欢迎;科研能力也强,不时有论文发表,是系、校重点培养的年轻的学术带头人。
吴季的苦恼在于家庭。他自己的小家庭和老家的大家庭。吴季的妻子是书香门第之女,父母都是高知,她本人受过高等教育,也是知识分子,在西安市一个事业单位工作。应该说,他们算得上是恩爱夫妻,家庭气氛挺不错。但也时常发生不愉快。产生诸多不愉快的原因,大多是由于小家庭和大家庭的矛盾引起的,而根本的原因则在于他们无法改变的中国城市与农村经济的不平衡。这就注定吴季一辈子都要受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心理折磨。
吴季和妻子的工资收入三百元多一点,三口之家一个月过下来也就所剩无几了。经济权由妻子掌管,她每月领回工资后都要筹划一番,精打细算,唯恐入不敷出。这种做法,有失知识分子的高雅,显得市民气十足,但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别人不能替代的,也就顾不了这些了。凭良心讲,吴季觉得妻子够通情达理的,每当假期和年关临近,妻子总主动地拿出一二百元让吴季带回去帮衬农村老家的费用。对此吴季很感激妻子。但是,在一个家庭里,夫妻之间不得不以感激来表达感情,吴季是很痛苦的。他感到怜悯与施舍的沉重,因此精神上就有一种来自自身的压力。这点钱虽说不是缩衣节食省下来的,但他们从不敢乱花销,十元以上一顿饭菜的饭馆没有问津过。他为妻子和孩子没有享受到应该享受的生活而惭愧。另一方面,农村目前的开销不比从前,名目繁多的这个费那个款实在令人害怕。吴季拿回老家的二三百元钱尽管能解决一点问题,但毕竟数量不多,难以从根本上使老家的情况有所改观。因此他觉得愧对父母,心理上又加一层负疚感。
平常这些倒还罢了,可是老家要盖房。旧房确实太旧,遇雨漏雨,遇风掉土渣,吴季早已于心不安。盖房谈何容易,需用大笔资金。吴季作为长子,不能袖手不管,只好借钱。要借钱,小家庭就出现不愉快。
“有钱了盖,没钱就别盖。反正我们不住。”妻子这样说。
继而吵。吵到厉害处,妻子狠狠地说:
“我这辈子算是栽了。我的孩子将来胆敢找一个家在农村的,我就和他断绝母子关系!”
话虽然刻薄刺耳,吴季过后冷静地想一想,觉得妻子也真不容易。如果人家找一个家不在农村的,哪来这么些烦恼?日子肯定过得比现在舒适。这样一想,心理上愈加不能平衡。而老家那头又不能不顾。一头是妻子孩子,一头是父母双亲,伤了哪头都痛苦。吴季夹在中间,体会到水深火热的滋味。
这样的景况还要继续。吴季从事的是基础学科教学,不会有什么发明和专利,因此永远不会突然间有大笔收入。陈景润大概也不太富裕吧。吴季时时感到精神的疲劳和心理的重负。如果萦系于心头的老家的生存环境好一些,如果小家庭的收入高因而不出现不愉快,如果没有诸如此类事情分心耗力,他的工作和科研将会是另一番景象。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