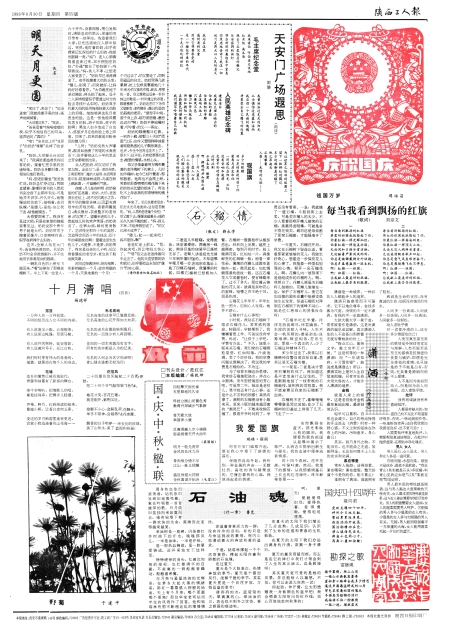
本版导读
明天月更圆
佚名
“来信了,来信了!”还没进家门我就扬着手里的信,高声地喊喊着。
“大伯要回来了。”我说。
“爸爸看着气喘喘嘘嘘的我,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连声追问:“真的?”
“啥?”坐在炕上听“戏匣子”的奶奶“喀嚓”关掉了收音机。
“奶奶,大伯要从台北回来了!”我满脸漾溢着笑容回答奶奶。接着忙把手里的信递给她。奶奶全身颤抖着,不相信似地盯着我。
“妈,您老别着急”爸爸急忙说,奶奶急忙夺过信,两眼直望着,像嗜好读书的人想把书完全吞下去那样专注,可是她并不识字,许久许久,她慢慢地把信放下,抽咽着,老泪纵横,“是健儿,是他,快让我下去,给他拾掇去。”
大伯要回来了。我没有见过大伯,只是在家里的镜框里看见过。奶奶说那个青年男子就是大伯。奶奶常常手摸着那像片,口里喃喃自语,似乎在祈祷什么似的。
这天,全家人站在大门外,爸爸搀扶着奶奶。只见奶奶不时全身微微颤抖,并不住地用手抹着湿润的眼睛。
一辆乳白色的小桥车飞驰而来,“嘎”地停在了那棵老槐树下。车上下来一位老人,六十开外,身着西服,黑白发相间,满脸急切的愁云,深邃的双目带有一丝浑浊。他看着我们大家,目光迅速地在人群中掠过。突然,他盯着奶奶,似乎在搜索记忆深处的什么似的,他忽然眼睛一亮,“妈”!老人心肺撕裂着直奔过来,双手拥抱住奶奶,“扑通”跪在了奶奶脚下,呜咽着说:“妈,孩儿不孝,让您老人家受苦了。”奶奶早已泪流满面了。双手抚摸着大伯的头发,“健儿,别哭了,回来就好,让妈妈好好看看你。”大伯跪在地下涕泪满面,将头抬了起来。母子二人深情相望似乎要透过对方的脸去寻找什么似的。奶奶双手托着大伯的脸用拇指抹着大伯脸上的泪痕。细细端详这张日夜思念的脸。这是一张饱经风霜的思乡的脸、游子的脸、孩子的脸啊!黑发人如今变成了白发人,悠悠岁月在他的脸上烙上印痕。回来了,回来的就是日盼夜思的健儿呀!
“儿呀!”奶奶突然大声嚎哭,眼泪如崩溃了河堤的水奔流而下,似乎要把这几十年的思念之苦全都倾倒出来。
众人把奶奶,伯父劝回了我家大院。走进大门,是一座四合院,正南面青砖门墙的大窑洞,东西两面是平房,院里绿树成荫,鸟雀在树上跳跃着,一片幽静的气氛。
夜晚,月儿挂在树梢,奶奶窑里的灯还亮着。奶奶、大伯、爸爸围坐在炕上,说不完的离乡之苦,倒不尽的酸甜苦辣,以及那充满艰辛的苦艰历程。看着两鬓斑白,满头银丝,衣着整齐的老母亲,伯父哭了。望着半老的儿子,想起他儿时的欢声笑语,奶奶流泪了。往事如烟,瞬间便消散了。怎讲得完那四十年的离愁,怎道得完那四十年的挂念,四十年的牵肠挂肚啊!望着这活生生的儿子,不是梦、不是梦、奶奶笑了。终究是母亲的儿子哟,伯父看着健在的老母亲,竟也孩子般地微笑着。
时间过得真快呀,骨肉相聚,形影相随的一个月,悲欢相融的一个月,天亲地爱的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了,伯父要走了,回到那遥远的台北。奶奶哭得几欲晕厥,炕上包袱里裹着她几十年来为伯父做的布鞋,新衣,厚厚的一沓。伯父摸着这母亲一针针纳过的鞋底,一针针缝过的衣服,眼睛模糊了。奶奶还在灯下为伯父做新衣,老花镜里,透出的是奶奶晶亮的老泪。“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啊!奶奶不停地嘱咐着、叮咛着,伯父——答应。
奶奶的眼圈整日红着。一别四十载,短暂三十天的“团圆”之乐,如今又要眼睁睁地看着刚刚熟悉的儿子飘然离去。也许,今生今世再也见不上了。留不下,拉不住,只有把厚厚的思念,酸楚的情感,永挂心头。
伯父手里拿着用方绸布裹着的老洋槐树下的黄土。儿时的洋槐树,如今已枝叶繁密,郁郁葱葱。他再也不会爬上树,笑着把那香喷喷的槐花摘下来扔给抬头乞望的姐妹了。再也吃不上母亲蒸的那香喷喷的槐花饭了。
车来了。伯父扶着老母亲,任泪水无尽地流淌,这泪是苦酸的。“妈,儿再给您老磕个头巴!”伯父跪下去,缓缓地磕着头,他的头久久地不能抬起。“妈,孩儿不孝,不能孝敬您老了。”伯父已涕不成声了。
“健儿,起……起来吧!妈不怪你,啊”
爸爸忙走上前去。“哥,你起来吧,别让咱妈太伤心了。”“嗯”伯父由爸爸搀着向车走去了。他的头直望着奶奶和我们,似乎要把这永恒的“像片”印在心里。
(请作者告知姓名地址)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