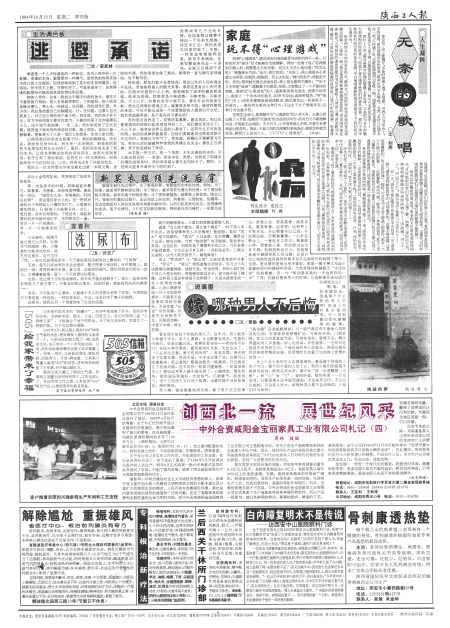
无奈的歌唱
□文/剑亮
单位有了间小歌舞厅,不免时常被人拽了去唱歌。可我兀立月形台上,手持话筒,面对熠熠闪光的荧屏,歌声总冲不出喉咙。当然,有时几位朋友在一起,几杯酒下肚,也敢纵情地用力狂吼一曲。唱歌带来的是痛苦还是欢悦,复杂得让人说不清总感觉这其中渗透着一种不可名状的东西……
那时上小学,最兴奋最守纪律的要算上音乐课。不是因为音乐的魅力和课程的轻松省心,而在于音乐课带给我们的意外收获。那时子弟学校没有科班出身的音乐老师,平日爱唱秦腔的焦老师便走上了我们的音乐课讲台。
焦老师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教语文,但他把学校交给他的音乐课颇当回事。上课铃一响,他总是把面部神经绷得紧紧的,昂首阔步地走进教室,又用极快的速度把歌词书写在黑板上,领读三遍,讲述歌词大意,最后,才落坐在那架斑驳陆离的风琴前,让我们听他弹奏。他奏得很虔诚,也还流畅,同学们却听得心不在焉,有的同学索性随着琴声学着老师偶儿流露出来的乡音,哼唱起来。也难怪,当时教唱的歌曲同学们已从路旁的大喇叭里听熟得不能再熟。
每有这种尴尬局面出现,焦老师又总是失望地摇摇头,只好组织同学们齐唱几遍了事。如遇下课时间不到,焦老师便施展文科老师的特长——讲故事。讲“王二小”讲“邱少云”;偶尔也讲“张衡”、“王安石”……
有一天,班长不知从哪位“作曲家”手中找来一首“语录歌”,请焦老师教给同学们,并郑重声明:此事不得泄露,这是班级赛歌的一枚“定时炸弹”。那时大凡劳动、开会之前或上街游行,都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前奏——拉歌赛歌,烘托气氛。歌声成了一种挑战信号,歌声又是力量和斗志的象征。唱歌的技巧并不重要,只要能扯起噪门吼出力量,吼得人沸沸扬扬精神振奋就行,因为歌唱是一种必须的集体活动。
焦老师望着满怀希望的同学,臂膀缓缓地垂了下来,隐隐约约地听到苍白的解释:“这首歌我没有听过。”一位同学迷惑地从地面上捡起了飘落的歌页,“不是上面有谱子吗?”焦老师没有言语。片刻,他抬起头,显得很内疚。“同学们,对不住大家,我不识谱……”学生们炸了营,寻到了“工宣队”。音乐老师不会教“语录歌”,在那个年代也算一个“重大事件”。从此,再没有听到焦老师的歌声,而我也再没有上过一堂音乐课。
事隔多年,有了诸多的经历,我渐渐便明白了当年焦老师流露出来的那一份无奈。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如今在歌厅的无奈可以追寻到焦老师的身影,而焦老师的无奈又是谁之过呢?以后,真想会会焦老师,一同吼段秦腔,可惜,路途遥远,况且连他的完整的姓名都不曾记下,似乎又给我的心中平添了一份无奈。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