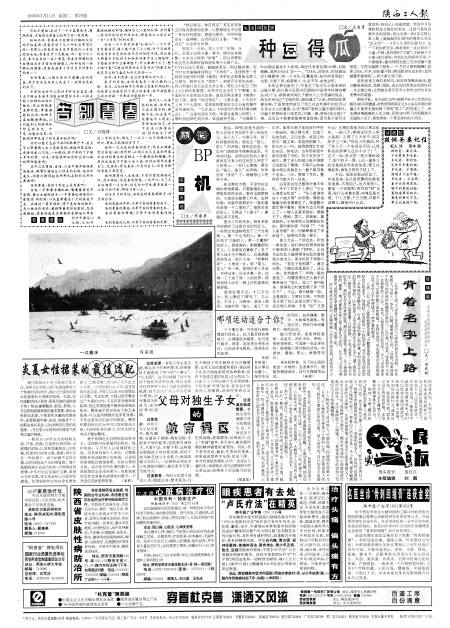
种豆得瓜
文/王吉彦
“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其实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律,心想事成也不过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愿望与现实,中间毕竟还有一道屏障。这世间歪打正着,“种豆得瓜”也是常有的事。
那是九一年秋,我上大学二年级。当时,恋爱正谈得火爆,情书、情诗往来频繁,女友为之倾倒“折服”,但从没想到将这些东西寄给报纸泄私情于大庭广众。9月20日这天看报,偏偏就看见一则征稿启事,而当时女友偏偏就肯转让“专利权”,支持我把一首特意为她写的诗歌《痴情》发射出去看看能击落几只傻鸟。既然女友“放权”,抱着开玩笑的态度,我立即就打发它去征文办公室,慌忙之中还忘了捎上5元钱的参赛费,玩笑开过全当打了个喷嚏,恋爱的日子依然如火如荼,谁也没再去理会《痴情》的下落。谁知“种豆得瓜”,小愿大遂。十天后天上掉下个大馅饼,居然收到那家征文办公室的稿件录用通知书:“大作选人《中国当代青年抒情诗精品》。”这馅饼品位不低、味道也蛮诱人的吧?哪料到馅饼吃到后来,味道就有些涩:“为确保大作如期出版并扩大影响,每位作者须包销100册,扣除稿酬,请将278元汇至……。”278元,好家伙,你站着说话不嫌腰疼,我一介书生,阮囊羞涩,如何消受得起?也罢,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生杀予夺,由他去吧。
本来这事也就完了,可是过了征文办公室承诺的出版日期,很久都不见那本所谓的《中国青年抒情诗精品》的下文,接着就风闻几个圈内人上当受骗的说法。我在庆幸自己“文网恢恢,疏而漏之”之余,怨愤却如骨梗在喉,于是悻悻然叙写了自己在这件事中的经历以及身边文人的遭遇,在为“落网”者树立墓志铭的同时,对骗子和帮闲者口诛笔伐,牢骚一通,寄给《杂文报》了事。此后也不曾奢望能够荣登报端,因为是不是写文章的料,咱自己心里最清楚。然而半月后竟收到杂文报社的来信。这回可是块货真价实的馅饼,里边夹着一张《杂文报》,第三版上就赫赫然印着咱的尊姓大名及“处女作”——《令人生畏的出版风》!这—下我如获至宝,捧着报纸一连反复读了三遍,不错,是我烧的“豆腐”,不缺辣子不少姜,原汁原味,传到女友和同学手里,个个都喝彩,激动得我发烧三天没有睡个囫囵觉。才把头脑降下温来,一个月后又接到稿酬汇款单,20元,不多,但份量不轻,瞧在眼里也觉亲热,直到储蓄所催领再三,我才拿它领了款。
尝到发表文章的美味后,我变得馋嘴而痴迷,整日整夜地构思、笔耕,报纸、杂志也时常宽容地赏给我一点立锥之地,让我能在受尽苦辛之余咋出丝丝甘凉而隽永的甜蜜。
朝花夕拾。如今追忆当年《痴情》与《令人生畏的出版风》的不同遭遇,忽然觉得那家征文办公室在有意的欺骗之中竟然无意地做了我的“恩人”,把我推上了一条充满诗情画意的人生之路,而我当时种下的那颗微不足道的小豆子,竟变异成一个莫名其妙的小西瓜。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