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位“休夫”的女主人,为了追求不该失去的东西,走上法庭——
她们为何休夫?
文/田萍
“是我的,走得再远也离不开;不是我的,再近也会分开的。”
丁丑年,一个春光明媚的中午,柳某象以前一样把他送上了远渡重洋的飞机,去追求他的“天堂”梦。
前年国庆,刚刚度过蜜月,他所在的电脑公司与美国一公司签订了一份培训合同,他获准去美国进修一年。这从天而降的好运气使他几乎高兴得发疯了,他抱住柳,欣喜若狂地说: “从今往后,你就有一个美国丈夫了。”他本以为会换来柳像往日一样的无限柔情,然而他从柳的眼睛里看到的却是几分迷茫,几分凄楚。不过,柳此刻尽量克制心头的震动,脸上堆满笑容,直到送他出境。
他走后不久,他的妹妹出嫁了,家中只留下一对年近六旬的老人:柳平静地生活着,尽力侍奉二老。
然而,半年之后他在信中越来越流露出不愿马上回国的想法,希望自己在美国呆的时间越长越好。
一年很快过去,电脑公司的另外5名进修人员都回来了,而他仍然留在美国。她几次去信、去电,催他回来,他依然我行我素——再干两年。
1997年春节前,他终于带着令许多人羡慕的超大彩电、多媒体电脑回到南京探亲。700多个日夜,700多个思念。她是女人,她不仅需要信纸涂满的爱和电话中的情语,更需要男人强有力的拥抱,让700多个思念,在瞬间化作动人心魄的暖流。可是,当柳什么都拥有的时候,突然觉得又少了什么,柳开始变得沉默了。
生活中,谁也不愿失去自己所爱的,正是这种情感支撑着柳和他久别重逢的日子。他们再没有像以前那样在黄昏时分漫步在公园的幽径,也没有为了渴望去看一场音乐会而兴奋,他们再不会因收看一场足球赛为各自的观点争得面红耳赤,又言归于好。失去了这些,犹如生活中缺少了热情和随意,仅仅因为他们生活在两个世界吗?!
20天的逗留是短暂的,他又要回到美国。回到家第三天,他就给柳定了3条“家规”:不交异性朋友,辞去工作照顾老人,不进舞厅美容院。受过高等教育的柳,终于在他临走前两天提出了“分手”。他一时难以接受,他说他富有了,可以满足她任何需要,可柳没有动摇。在征得父母的同意后,还是理智地办了离婚手续,他提出给柳两万元补偿,再照顾他父母两个月后,一套红木家具归柳所有。柳拒绝了家具,但整整照顾了他父母三个月,直到他妹妹生完小孩后才无声无息地离开这个生活了两年零3个半月的家。
他去美国不久,还给柳写过一封长信,希望柳能回心转意。但柳没有,她在回信中说:你比原来还要贫穷,你已经无法满足我一点儿爱的需要了。女人有她自己的信念、人格和思维方式,倘若她要依附于一个男人是容易的,但要真正得到一个男人的心,那就太难了,女人自会画她自己的“圆”
“该我得到的,却得不到;不该得到的,我反而得到了。生活为什么有时会种‘瓜’而得‘豆’呢?”
在人们的眼中,方女士和路先生是“天生的一对”。方在医院里当护士,路先生在文化馆从事专业创作,结婚8年有余,已有一女上幼儿园大班,小日子就这样风平浪静地过去了三千一百多个日夜,怎么会离婚呢?不知个中原因的人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离婚的原因说起来既简单,又平常。
原来,方女士每个星期要值一个小夜班和一个大夜班,为了不影响丈夫写作,女儿都跟她在医院过夜;路先生除了白天上班或外出采风外,夜晚回到家,就一人关在书房里埋头写作到深夜,经常通宵达旦,而上午则要睡到九点、十点钟。当初相爱时,他们都把未来想得很浪漫:路先生认为,方女士是一白衣天使,将来对自己肯定会像对待病人那样,既温柔又体贴,何况她也爱读小说,共同语言不会少;方女上则认为,路先生是作家,作家都有丰富的情感,婚后生活一定富有诗情画意。然而,婚后的实际生活使他们都很失望,每星期晚上除了在医院度过外,每天晚上方女士都是一人先上床,不是与电视为伴,就是在百无聊赖中永久地等待……。特别是让方女士无法容忍的是,好不容易进入梦乡,仍沉浸在写作激情中的路先生一进房间,就把房内灯全部打开,并滔滔不绝地讲述写作进程或人物情节的设计以及今天创作中新的构思,絮絮叨叨,没完没了,等到方女士睡意全无时,路先生早已鼾声大起。
就在夫妻关系危机四伏时,路先生竟然一头扎进了一部反映当代人婚姻问题的长篇小说和联系出书事宜中,方女士先后三次相约,丈夫每次只有两个字:“没空!”10多个月后,当路先生喜滋滋地捧回家散发着油墨香味的《离婚》长篇小说时,方女士送给他的是一张协议离婚书和无可奈何的愁容。路先生急了:“你需要什么?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我给你买。”方女士说:“我现在什么都不需要了。”“那,好好的,为何还要分手呢?”“古人不是说过:‘书中自有黄金屋和颜如玉吗?’那是你们男人的世界。”
在协议离婚时,路先生慷慨地说:好在我们夫妻一场,家中东西尽管拿,我有我的小说就足够了。方女士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道: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我的鹃儿,她是我的肉。路先生再三问,难道没有一点挽回的可能?方女士十分坚定的点点头。于是路先生十分理智地在协议上签了字,就这样他们便和平分手了。
方女士在法庭上反复对女法官说:我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种下“瓜”,反而偏偏得到“豆”呢?
她们为何休夫?她们到底需要什么?聪明的丈夫应该从中汲取什么样的教训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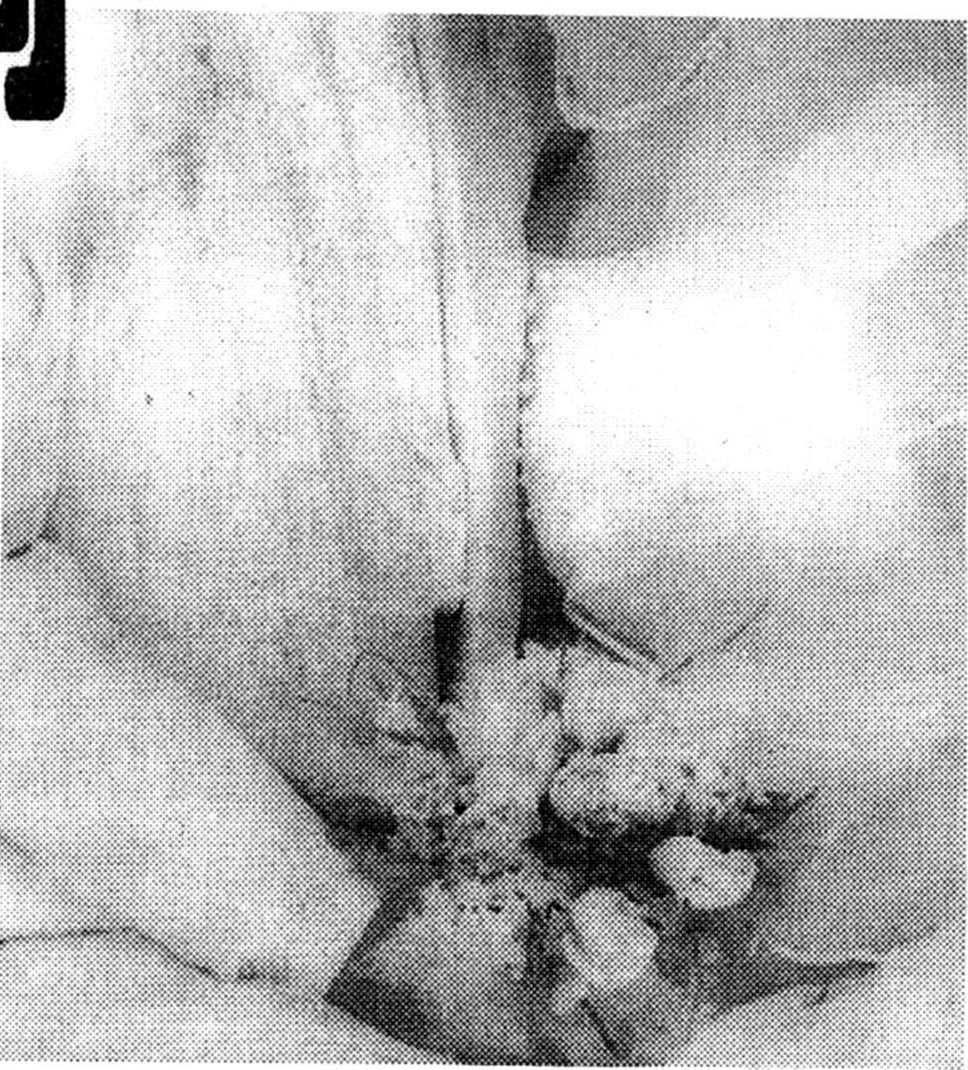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