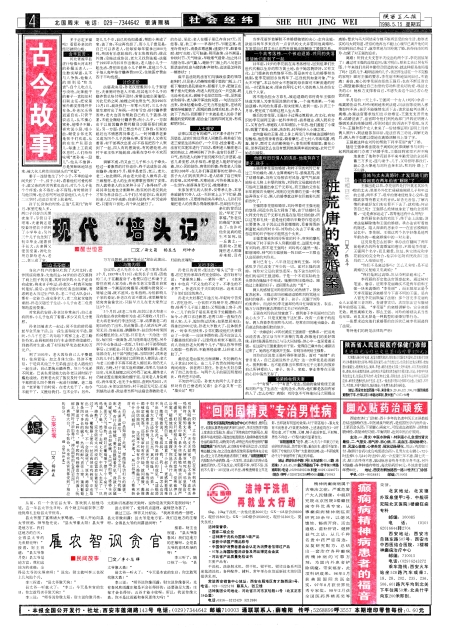现代“墙头记”
文/靳文菊 杨显忠 刘坤赤
多子必定多福吗?看看孙老汉的经历就明白啦。
含辛茹苦
河北省滦平县虎什哈镇大河北村的孙佩玉老人,一生憨实厚道,从不与人争执,他做人的原则是“和为贵”,自个儿吃点儿亏没啥。泼辣能干的妻子一直担任村妇联主任,把家里家外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孙老汉乐得逍遥自在,只管干农活儿,从不操心家务。他嗓子不错,喜欢说小段、唱小曲,颇受乡邻尤其是孩子们欢迎。从前在生产队那会儿,每逢上工前或休息时,人们纷纷吆喝“老孙来一段儿”,他从不推辞,总是笑眯眯地站出来,被大伙儿称作田间地头的“笑星”。
妻子一连给他生了5个小子,不幸的是中间夭折了一个。孩子小时,看着他们可爱的样子,做父亲的再苦再累也高兴,对几个儿子他个个疼爱,舍不得打,舍不得骂。有时候孩子与他顶嘴,他总乐呵呵地原谅他们。大儿子十二三岁时,他还总在背上驮着呢。
孩子长身体的时候,正值“瓜菜代”的年月,家里吃粮人多,两口子只好白天黑夜地干,尽管日子艰难,夫妻俩还是咬着牙把长子供到了小学毕业,另外三个儿子也念到了初中毕业。随着孩子长大,夫妻俩又受苦受累,省吃俭用总算给老大、老二、老三成了家。
众子不睦
当包产到户的春风吹到了大河北村,老伴因疾病缠身,先他而去,64岁的孙老汉感到了肩上担子的沉重。其时20岁的小儿子还没有成家,将来日子咋过,孙老汉一时真不知如何是好。最后,由家族中的长者出面调解。考虑到老大当过生产队长、老二干过大队会计,都有一定能力,遂安排老大、老二负起家庭的重担,孙老汉随长子生活,小儿子由老二负责帮助盖房娶妻。
对家族的安排,孙老汉非常高兴,自己老有所养,小儿子也有了着落,多少又有几分宽慰。
孙老汉随老大一起过,闲不住的他仍是起早贪黑地干活。这一段生活得较为平稳。期间,小儿子在老二的帮助下成家立业,老三勤俭持家,由最初的骑自行车走街串巷收破烂,到搞药材生意,成了村里较早发达起来的万元户。
到了1995年,老大因给自己儿子娶媳妇,住房紧张,加之身体欠佳,经济不宽裕,于是向其他三个兄弟提出让老人随他们一起生活,自己愿掏点赡养费。但三个兄弟不同意,已丧失劳动能力的孙老汉顿时陷于尴尬境地。后来老大找了族长及村干部,村干部把哥儿四个聚到一起进行调解。老二提出“老爹能干的时侯,在老大处干了,如今不能干了,又推给我们,这不公平;另外,哥儿几个中,自己的负担最重,帮助小弟成了家,盖了房,不应再负担了。”而小儿子意见是,自己可以养老人,但每家每年要拿出800元钱。终因有乐意轮班的,有主张拨钱的,彼此纠缠,没能达成协议。老大又找到法庭,法庭于1995年9月25日作出裁决:老人随小儿子一起生活,责任田也由小儿子耕种,其他三个儿子每人每年给付赡养费500元,住院医疗费由四子平均负担。
讨价还价
法庭裁决后,孙老汉便搬到小儿子家居住,夫妻俩对待老人不错,但其他三个儿子的赡养费总给付得不及时,常需法庭出面催促,为此兄弟之间、妯娌之间也常生气。到1996年10月1日,裁决执行一年零六天时,三儿子在做生意时出了车祸,一时有亏空,给付赡养费困难;老大也因为帮助自己的儿子盖房,钱紧,不能全额给付赡养费;而小儿子,一方面由于以前因赡养费问题没少跟哥哥们闹意见,另一方面,自己想出外打工挣钱,在家的媳妇也不情愿再侍奉老人。一时间赡养老爹又成为四个儿子的挠头事。看到老人又将无着落,村干部再次出面,好不容易把四个人聚到了一起。四人有的愿掏钱,有的愿轮班,而村干部主张不能轮班,结果在争吵中不欢而散。
调解不成,后又由三儿子和小儿子牵头,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终于达成协议:轮班赡养,每家3个月,顺序是老四、老三、老大、老二,如此循环。并由老大给老人做寿衣,老三做棺材,老人的生养死葬事宜得到了安排。四人就将老人的玉米种子分了,各得86斤,并将其承包地也分割耕种。憨实的孙老汉到此才知为养活自己,儿子们已另定协议,而此时的老人已79岁高龄,自感风烛残年,听凭安排吧,只要有口饭吃,有个趴处就行了。
万万没想到,新的“墙头记”却由此演出。
与猪为邻
协议后,老人先在小儿子、老三家各生活3个月。1997年4月10日,轮到长子当班,因他的二儿子在翻盖房子,他便以自己和妻子正借住在别人家为由,将亲生老父安置在自家猪圈旁一个潮湿的窝棚里,窝棚与猪窝仅一矮墙之隔,既不遮风,也难挡雨。为怕影响儿子家的稳定,孙老汉有话不敢说,夜里蜷缩在猪窝旁偷偷饮泣,只盼早点儿在老大家熬过这3个月。
3个月后,该老二当班,但其以老大和老三没有做出寿衣和棺材为由,拒不接收,7月2日,老大将老爹的行李送到老二家,结果被老二的媳妇给扔了出来。见此情景,老人欲诉无声,欲哭无泪,伤痛至极,蹒跚移步,独自到本村果园的窝棚里居住。6天里,只有老大一天给送一回饭,每回仅一碗面条,饥与饱都是这些啦,另外两个孙女各送过一次饭。7月8日,村干部得知此事后,立刻赶去,只见老人在窝棚里躺着,连炕席都没有。村干部气愤已极,当即回村,找来老汉的儿子们,要求他们立即将老人接回去,老大与老三的妻子不得不将老人接回来,但仍无人接收。当晚,村干部又组织调解,结果几句话没说完,兄弟及妯娌之间又吵骂了起来。最终老人仍被安置在猪窝旁的棚子里。后来老人身染痢疾,病体难支,也无子女接回。直到9月26日,天气已凉,乡邻议论纷纷,村干部忍无可忍,汇报到镇政法委,政法委当即与法庭会商救助老人的办法。至此,老人在棚子里已存身167天,历经春、夏、秋三季——早春时节,乍暖还寒,夜里冷得发抖,清晨浓霜遮鬓;盛夏时节,酷暑难耐,蚊叮虫咬,无可躲避,阴雨连绵,分外潮湿;仲秋时节,天气转凉,早晚寒气浸骨,加之终日与猪为邻,浊气薰人,蜷卧于门板上的八旬老汉那悲凉的叹息与猪的鼾声相和,这该是怎样的一幅惨状?!
滦平县法院的法官们与镇政法委的领导赶到时,只见老人仍蜷缩在棚子里的门板上,门板下堆放的是乱柴杂木,距棚子几步,肥猪正在槽子里大吃粥食,而老人的枕边仅一只空碗,既无汤来也无水,破被子也似烂垃圾一样。见到法官和领导,老人睁开浑浊的双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身体枯瘦如柴,已无力再坐起来。在场的镇领导被激怒了,围观的群众咂舌叹息,许多人流下了热泪,而距棚子十米就是老人的孙子新翻盖的瓷砖贴面、铝合金门窗的四间瓦房,形成鲜明对比。
入土难安
法律以其应有的威严,对不孝子进行了严厉惩处。法官们在征得老人同意后,将其安置在老三家里生活和治疗。一个月后,挂念着老八的法官们又驱车进行了回访,看到老人躺在老三家的热炕上,精神好转了许多,法官们长舒了一口气。然而老人的眸子里仍掩不住几许悲哀,法官几番安慰,执手相劝,希望老人能好好地活着。但心灵的创伤、病体的折磨,终使老人没能走到1998年,在儿孙们喜迎新春的忙碌中,在孩子大人们的欢笑声中,老人结束了自己残年的苦难。北风呼啸,天寒地冻,可怜孙佩玉老人一生劳作,却落得身无片瓦,晚境凄凉!
来参加丧礼的人很多,仅带孝儿孙、本家亲戚就有70多人,这一天孙家上上下下忙碌,既要赶制棺木,又要接待前来吊孝的人。儿孙们尽量把老人的丧事办得像模像样,但却挡不住乡亲们的背后议论:“早死了早享福。”孙老汉的确是“享福”去了,也许对他来说真的是生不如死。但一丘黄土,一座新坟,怎能掩住老人那凄苦难耐、没有归宿的灵魂呢?
父行子效
孙老汉的离世,使这出“墙头记”告一段落,但它在孙家却没有完全收场,老百姓有句话:“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老来难》中也有“不义生的不义子,不孝生的不孝男”。孙老汉长子夫妇的归宿,近来又成了乡邻们议论的焦点。
孙老大夫妇都已年逾五旬,年轻时辛苦劳作,省吃俭用,一分钱恨不得掰开花,攒钱积物,给两个儿子说上媳妇,又帮助盖上房子,其中,二儿子的房子是在其老房子处翻建的,而如今,小两口喜迁新居,老两口却一直租住在别人家,儿子、媳妇传过话来:如果想回来住,得拿出2000元钱。孙老大岁数大了,且体弱多病,一时拿不出钱来,乡邻们数说他们夫妻错走了一步棋——应该多攒些钱,而不应该让儿子翻盖他们的房子,以致现在有家不能回。也有人劝说孙老大的两个儿子:“得从你爷爷那儿吸取一些教训,不能再经法律、让孙家人丢脸了。”
最后还是由族长出面调解:夫妇俩的大儿子拿出1500元,由二儿子负责在其院内盖两间南房,供老两口居住。孙老大夫妇总算有了自己的住处,与两个儿子的丽瓦明屋相比,终有些不协调。
不知20年以后,孙老大的两个儿子会怎样对待自己垂老的父亲?会不会又有一出“墙头记”呢?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