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起来创新业
文/董庚臣
我叫董庚臣,今年50岁,原是沈阳矿务局本溪职工大学的讲师和宣传部长,现任辽宁省本溪市宏达开发公司经理。几年来,我和下岗的60多名教职工们从课堂走向社会,不等不靠,自强自立,闯出了一条组织起来再就业,共求生存和发展的希望之路。
1994年4月8日,我所在的原沈阳矿务局本溪职工大学因煤炭行业不景气,导致生源不足和教学经费严重短缺,被迫宣布解体。
宣布解体的第三天,几辆大卡车开到学校,把教学实验仪器、设备、桌椅、图书,都一车车地拉走了。就连教室里的日光灯管、镇流器、食堂里的大锅、菜刀等值点钱的东西也都被拉走了。眼巴巴地看着辛辛苦苦几十年积攒下来的价值100多万元的10多万册图书全被装上车,精心制作的图书检索卡片扔得满地都是,几名图书管理员,捶胸顿足,放声痛哭。一位教师一气之下把写字台的玻璃从窗户摔到楼下。原教务处主任一时想不开,连气带急,得了一场大病,住院11天就去世了。一种近乎绝望的情绪笼罩在大家心头。
在组织的帮助下,一些年轻力壮的、学历较高的都走了。剩下了65名被人挑来拣去,谁也不愿要,只好集体下岗。这65人中,女同志占了50多个,近80%年过50岁,最小的也有42岁。看到这种情况,上级就有意让我组织大家搞生产自救。许多下岗教师也找我,让我领着大家干。面对当时的条件,我心里非常为难。可是,当我望着65双期盼和信任的目光,一种责任感和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觉悟,促使我放弃局矿工报编辑的新工作,担起了组织大家再就业的重任。在这个破大院里,挂上了本溪市宏达开发公司的牌子。
人,虽然组织起来了,可是大家的心还没有拢到一起。我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分析面临的形势和处境。我对大家讲,改革要深化,下岗分流这步非走不可。对下岗职工,政府不是不管,但我们光靠政府不行。特别是煤炭行业属于特困行业,下岗职工那么多,都靠政府怎么能安排过来?大家只要面对现实,同心协力,自己救自己,就一定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最后一丝幻想被打破了,大家一致表示愿意跟我干。
我们需要有一个好的项目和产品。开始时,我们曾想与别人联办中成药厂,还曾想搞个汽车配件供应和维修中心,但都因为没有资金而一一告吹。后来看到我们学校一名教师下岗后,办了一个家庭数学辅导班,挣了不少钱。手无分文是我们的劣势,但我们有一支经验丰富的师资队伍,这就是优势。我们四处调查,并分析了我公司所在的彩屯地区教学形势,决定发挥教学管理、校舍和师资三大优势,办个私立中学。大家全体出动,跑遍了彩屯地区的各个学校动员学苗。为了招揽学生,没钱打广告,老师们就自己写、自己印,天黑后拎着小浆糊桶上街去张贴。没有资金,就大家集资8000元,购置了100套新桌椅,修复了150套旧桌凳。经过几个月筹备,1994年9月份,我们的“树人学校”开学了。
带着初涉商海成功的喜悦,我们决定前院办学,后院办厂。有人介绍南方一个老板委托加工菱镁浴盆项目,我与他们签定了加工合同,花5万元购买了他提供的凝固剂。再修厂房、制模具,男女教师60多人,没白没黑地苦干两个月,生产出420多只浴盆。可是到了付款提货的日期,却迟迟不见那个老板。经调查,原来对方竟是一个骗子,所谓加工定货是假,高价销售他的凝固剂才是真,钱一到手,早夹包溜走了。我们又赶紧跑到安徽另一家原定要我们浴盆的公司,一去才知道,对方也是个皮包公司,根本付不起货钱。凝结着大家几个月血汗的浴盆成了无销路的废品,办学挣的8万元一下子就赔了5万元。那是我们大家的救命钱啊!我怎么向教职工们交待啊!我病倒了,在旅店里昏睡了整整一天一夜。醒来回到家,我的体重下降了10多斤。
以后,经多方市场考察,我们从400多个项目中筛选出生产“菱镁复合门”这个项目。选这个项目一是因为我们剩下不少菱镁粉原料可利用,还有生产菱镁浴盆的经验;二是这个项目有一定科技含量,市场需求量大。菱镁门是一个技术性较强的产品,很多厂家都因生产出的产品门质发脆、门体沉重而纷纷破产。为掌握技术,我们选派人买回了两樘门,拆开来研究。又想方设法买来基础配方,请人指导。经过上百次实践,终于掌握了这项技术。上这个项目,一套设备少说也得30万元,我们上哪弄这么多钱啊!只好土法上马。好在厂房是现成的。我们又派教机械设计的教师到生产这种门的厂家,借买门之机,看人家的生产设备是什么样的,回到旅店里就凭印象画设备草图,回来后进行试制。制造中需几十米工字钢,我们几乎跑遍了市内所有废品收购站,花了不到400元,就解决了问题。工作台需要特厚木扳,上市场买每立方米得1400元。听说本钢有大型进口设备的包装箱要处理,我们跑到本钢,只花1000元买回4立方米大厚木板。成型车间需要专用搅拌机,买台新的得花一万元。我们把食堂废弃多年的和面机修复改造来替代。不到一个月,没用上3万元,生产线就建成投产,产品质量经过有关部门鉴定,完全合格,当年实现产值30万元。去年,我们又由此拓展开发了配套项目:塑钢窗,建了一个塑钢窗厂,全年完成产值360万元,盈利25万元。这样便形成了我们公司适销对路的主导产品,使公司进入了一个健康发展的轨道。
既要靠合适的项目、产品,也要靠适应市场经济的机制和管理。8000元集资办学,是我们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的开端。上塑钢窗生产线,我们又集资20万元,这是我们连股连心,搞股份合作的雏型。在分配上,我们向一线倾斜。一线人员平均工资800多元,最高月收入可达1700元。我们还给全体职工上了保险,交养老基金和住房基金,解决了大家的后顾之忧。
这种利益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大家的生产积极性和对集体的关切度。为了搞好生产,不用督促,几乎天天从早6点干到晚6点,有时干到深夜。有一次,一个教师把料下错了,为了不影响下一道工序,他一连好几个晚上领着老婆孩子全家来加班,弥补了下错料造成的损失。一名女教师,在施工中见一箱两吨重的玻璃倾斜,冲上去用自己的双腿将箱子顶住,避免了两万多元的损失,而自己的双腿却受了伤。
学校两座大楼维修费用每年近15万元,为节约经费,从上房串瓦,到钻地沟修地下管道,掏马葫芦,我们都自己干。为压缩水电开支,三九天全体职工齐出动,改线路、换水表,使水电费下降了40%。茶炉工有煤舍不得烧,整天烧菱镁门厂的碎木屑,一年就节约一万多元的燃料费。生产用的玻璃纤维,需要从沈阳买回来,为了省钱,一位讲师一次次坐长途客车往回背,每次都是八、九十斤,细细的纤维直往衣服里钻,扎得他浑身起满疙瘩。人到中年,学技术不容易,为此大家付出不少代价。记得我们有一个老师,为学木工技术,在使用电锯时,被割下了一截手指,大家赶紧帮他到处找,才在锯末子堆里找到了粘满木屑的那半截手指,到医院把它接上。上塑钢窗进了好几车玻璃,要卸车,每箱玻璃2吨重。一开始我们花每人20元雇了4个小工,可卸了一车后,他们说这活太累了,就是给50元,也说什么都不干了。雇吊车来卸吧,每天需付450元,雇不起,没办法,只好我们自己磕磕绊绊的一车车往下卸。
创业的艰辛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去年为矿工房改造工程生产3000多樘门、1.5万平方米塑钢窗,仅玻璃就用去了五个半火车皮的。为了抢工期,全体职工白天黑夜连轴转。在往工地楼上送塑钢窗时,为了省钱,我们自己背。女工们一次都背两扇。那是80多斤啊,要扛到7楼去,中间很想歇歇脚,又怕身子一歪磕坏了玻璃,只好硬挺着,一气儿背到楼上。有一回,一个女工累得腿发软,被楼梯绊了一下,膝盖跪在楼梯上,磕破的大口子鲜血直流。就是这样,她也没有把窗户扔下,直到咬着牙扛上楼。工期紧,任务重,可我们硬是把这个活拿了下来,而且被工程指挥部评为唯一的配合优胜单位。
由于长期过度的劳累,我患了糖尿病。尿糖四个“十”号,并伴有严重的尿蛋白,只得住进了医院。老伴因为着急上火,一下得了脑出血。经抢救虽然保住了性命,但落下了后遗症,至今半身不遂。这对于我的家庭和刚刚起步的事业,无疑是个沉重打击。我家里条件不好,上有八十岁老母靠我赡养,妻子没有工作,儿子在外地念大学,我和老伴有病的事一直瞒着他,怕他分心。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把实情告诉了外地归来的孩子。看着消瘦的我,看着瘫痪的妈妈,孩子难过极了,一家三口抱头痛哭。
那一段时间,我实在太累了,真想歇一歇。但想想自己肩上的担子,看看职工们期待的目光,我怎么能歇得下?只好一边打针吃药,一边侍候老伴,一边坚持工作。为了尽快打开产品销路,常常不得不撇下老伴联系业务,经常是早上做一顿饭她吃一天。一次去外地签合同,临走时怕老伴腿凉着,灌了热水瓶子放在她腿边,半夜才赶回来,结果老伴被取暖的暖水瓶烫了一腿大泡,三个月还没好。每想起这事,我心里就很内疚。现在,我每天还要打两次胰岛素,老伴也离不开照顾,但我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岗位。
经过不到4年时间的艰苦创业,我们公司取得了初步成功。公司办的“树人学校”在市内创出名气,已有15个班,在校学生达800人,年总收入超百万元;公司兴办的两个工厂,年产值由95年30万元增加到97年410万元,利润由5万元增加到35万元,企业实物积累50多万元;安置待岗职工70多人,职工月平均工资达800元。
说实在的,谁也没想到我们这些拿粉笔头出身的人能干出今天这样一番事业来。回顾我们四年来所走过的组织起来再就业的路程,我体会最深的,一是党和政府的关心与支持是我们组织起来再就业的靠山。二是下岗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勇气去面对新生活的挑战,不等不靠,自强自立,才能开辟出一片生存发展的新天地。三是散兵游勇、单枪匹马,很难创大业,下岗职工只有自己组织起来,集体参与市场竞争,就一定会创造出新的业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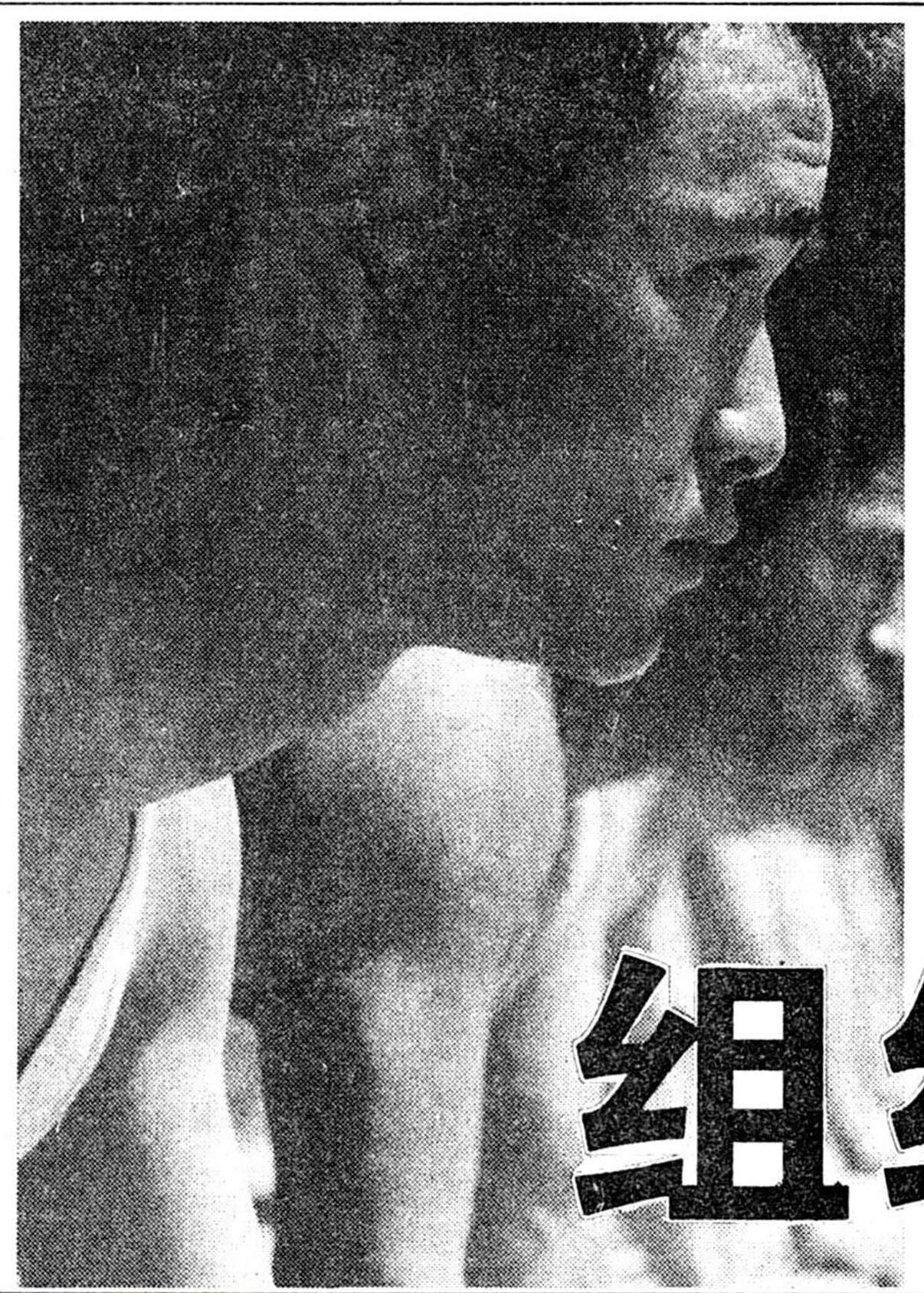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